 教研
教研  语文建设 2015年第7期
ID: 359153
语文建设 2015年第7期
ID: 359153
基于语用观的语文能力评价
◇ 荣维东
评价在我国原指“对事物的价值做出估量”。英语中有两个词与其对应:一是“evaluation”,二是“assessment”,它们都含有凭借一定标准,对事物进行价值判断的含义。可见,在评价活动中,“价值观”以及由此产生的“评价标准”甚为关键。
我国语文教育之所以存在这么多问题(包括历年公众对高考作文的吐槽),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语文教育的价值观以及核心语文能力评价标准出现了混乱。
鉴于语文教育评价过于复杂,本文拟从当代语言学“语用转向”,分析我国语文核心能力评价存在的问题,并探讨基于语用观的语文评价体系的构想。
一、作为语文素养核心的语用能力
1.语用学以及语用能力
当代语言学,尤其是语用学的发展使得我们对传统语言能力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简单地说,人的语言能力不仅是指对语言符号的感知与记忆,更应该是指人们在复杂的语言环境中灵活得体地运用语言,并科学或艺术地达成交际意图的能力。这种认识的学理依据是语用学。
语用学是专门研究具体语境中理解与运用语言的学科。自从20世纪30年代C.W.莫里斯提出语言有“语符、语义、语用”三维,开启了语用学研究的新视角。60年代乔姆斯基区分了“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两个概念:前者指内化了的语言规则体系,后者指人对语言的使用。20世纪70年代,D.H.海姆斯提出语言“交际能力”的概念,认为:一个人的语言能力不仅指能说出合乎语法的句子,还包括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恰当使用语言的能力,即在不同的场合、地点对不同的人进行成功的交际的能力。这些观点对语文教育有着重要影响。
2.从语言能力到语用能力
当代语言学经历了从结构语言学向语用语言学的转变,由内部语言要素(形态、句法、语义)转为外部语用(语境、交际、功能、语体、语篇)研究。这种转变集中体现在语言能力与语用能力两个概念上。
这两个概念存在着内涵、语言观和语言教学观的不同:前者指概括的、抽象的语言能力,后者指具体情境下、真实生活中的语言运用;前者属于静态语言观,后者属于交往语言观;前者偏重语符、语义教学,后者注重语境、语言功能教学。两者的区别就像汽车和学会开车一样,有所关联,但不是一码事。区分这两个概念对认识语言能力本质,开发语言课程教学体系,实施科学有效的语文评价体系具有重要作用。
语文教育的核心是什么?是语言学习还是语言运用?是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还是培养他们的语用能力?这是语文教育和课程建设必须澄清的理论基点问题。
语文教育的本质是语用。正像叶圣陶先生所说:“学语文为的是用,就是所谓学以致用。”“语言文字的学习,出发点在‘知’,而终极点在‘行’,能够达到‘行’的地步,才算具有这种生活的能力。”这里的“用”和“行”,都是指日常生活、工作、学习中的语言运用能力。这种语言语用能力的形成虽然离不开语言知识,但关键是要能够运用语言文字去思考、表达、读写与做事。这就是说语文不仅要教学生掌握语言知识和语法规则,更要培养学生真实有效地运用语言的能力(即语用能力)。
3.语用能力的核心是言语交际
澄清语文课程的“语用本质”后,还要进一步澄清“语用的核心是什么”。现代语言教学的一个很大特点是:较多地从社会的角度来对待语言,并且重视语言在不同社会环境中的交际功能问题。基于此,我们认为语用的核心是交际。
传统语文教育主要基于结构语言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把语言看作语言符号简单机械的刺激与反应,属于信息的“发出或者接收”,在教学实践中表现为简单机械的读写听说技能训练。这种训练所形成的是低水平、单向度、非交往性语言能力。传统语文教学因其简单、机械,故难以适应真实生活的需要。这种语言教学容易走向简单机械的“假语文”能力训练。
真实高效的语文能力应该是一种语用型的语文能力,其实质是一种灵活应付不同情境中语言交际任务的能力。它包括对言语交际的不同对象、目的、场合、功能、效果等的熟练精准把握,运用语言时需要具有对象意识、目的意识、语体意识、语境意识等。语用型语文教育因其知识来源、教学内容和过程最大程度上模拟并使用真实的语言环境,“所学即所用”“学而能应用”,更接近于真实情景中的语言运用与交流,因而语用型语文教学才是真语文能力教学。
然而,由于我国现行语文教育理论比较陈旧僵化,主流语文教育界还没有树立起语文教育的语用观,导致我国语文教育中语用知识严重缺失。这种缺失直接造成了“假语文”教育的泛滥。
二、我国语文教育评价标准存在的问题
王旭明先生认为我国语文教育的最大问题是“假”。这个“假”主要是指语文教育中无所不在的虚情假意的做派,如“泛人文”的道德说教、脱离真实运用的“贴标签”式阅读、“文艺范”作文教学等。假语文的实质是什么?我们认为是一种“不接地气”“虚假无用”的语文教育观,即用一种伪道学的话语方式,训练学生掌握那种脱离现实需要的应试语文能力,而不是真实生活中的听说读写技能和素养。
口语交际不是教学生说真实生活场景中应该说的话,而是一种生硬、简单、僵化得令人可笑的语句。阅读教学不是教学生真实地获取信息能力或文学鉴赏能力,而是用一套“语文”名词去生搬硬套。学生写作文,不是真实生活需要的实用写作或文学写作,而是如何完成一篇“小文人语篇”模样的“考场作文”。高考作文命题之所以每年都遭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批判,原因正是那些冬烘先生们自鸣得意的“玄虚化”“微言大义”与“文艺范”作文题。
更为严重的是,我们评价语文的标准已经出现严重偏差,几乎到了好坏不分、是非不辨的地步。让我们来看看一些被称道的“优秀作文”的“精彩语段”吧:
1.母爱是早晨妈妈端来的一杯牛奶;母爱是出门时妈妈一次又一次的叮嘱;母爱是下雨天妈妈送来的一把雨伞;母爱是妈妈没完没了的唠叨;母爱是考试成绩不好时妈妈的一声叹息……
2.快乐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奉献;快乐是“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的牵挂;快乐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祝福;快乐是“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的圣洁;快乐是“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的回忆;快乐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快乐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气节。
3.语文是鲁迅救国救民的呐喊,语文是文天祥宁死不屈的正气,语文是岳飞驰骋疆场的足音,语文是李白、杜甫、白居易高歌低吟所抒发的情怀……
这些语段好吗?自然在某些教师看来,学生能运用排比,写出的句子整齐排列、汩汩滔滔、铺排华丽,显得很有声势……这样的语言当然是好的。然而,须知这样的句子或语段是要有一定的场景和特定用途的。如果文章的确需要用重复来引起读者注意、说明某种道理、强化某种情感,这当然无可非议。可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情形是学生不论文体、目的、用途,都是这一个路子的话语表达。这种表达方式的特点为:机关枪似的强词夺理和不节制的渲染铺排。这种语言表达手法其实很简单,就是用一个句型模子去机械复制语言。这种简单机械的句式操练是不需要投入真实情感的,训练多了而又缺乏语境需求会逐渐破坏学生的天然语感、语言趣味,弱化他们的表达能力。
试想一下,同样是表达挚爱亲情,为什么朱自清在《背影》里运用那些平淡质朴的大白话能直击我们内心呢?“进去吧,里边没人”,“到了那里,给我来信”,(买完了橘子)“扑扑身上的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这些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语言为什么会唤起我们真切的亲情体验?就是因为这是一种真实情境中自然的语言。语言的功效与用不用排比、比喻、拟人等修辞格没多大关系。尽管朱自清在《春》中也运用了大量的比喻、排比、拟人,但那是在赞美春天、讴歌生命这样的文章主题和目的下,在散文诗这样的文体下,语言表达手法的正确选择。因为赞美诗和抒情散文需要这样文辞华丽、铺排话语风格。我们教修辞的时候,已经忘掉修辞的本质和真实功能、目的,导致为修辞而修辞。古人讲“修辞立其诚”,修辞是为准确、得体、艺术地表达服务的,而不是掩盖虚假的工具。
余秋雨在全球华人少年美文大赛现场对记者说:“从报纸上、出版书籍中,我们能看到一部分青少年写作走入了误区。大段的形容词、成语、排比句形成一股滔滔话语急流,裹卷着我们可爱的生命。”“朴素记叙的能力正在一些孩子身上慢慢丢失,华丽的辞藻、繁复的内容掩盖了最真实的某些东西,造成了许多青少年作品的千篇一律。”“学生作文中滋长着一种阴柔之风、空泛之风、浮躁之风、骈俪之风。”“缺乏观察体验,不下功夫学习语言,用时尚的概念和形式掩盖思想的贫瘠,写作成了矫情工具和文字游戏。”余先生的看法十分透彻。我们不是教学生回到内心、回到生活、回到情境中寻找一种真实质朴自然的表达,而是在教学生用一种铺张扬厉的“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方式,去掩盖他们思想的苍白和情感的虚假。
其实,学生也有某种尴尬与苦衷。他们并不是生来就对简单质朴的话语缺乏感觉,也不是生来就审美感觉麻木迟钝,而是我们的语文教师在用一种非正常的机械化复制训练,把他们本来自然的良好的语感给硬生生地破坏了,把他们原本自然、质朴、真实的语感给毁掉了。
我们的语文教育开始这种“排比+比喻”粗放式语言生产,很可能就是因为错误的、恶劣的、扭曲的语文评价标准的盛行。当真实朴素自然的语言受到放逐,机械铺张华丽滥情受到表扬,形式化机械化复制受到嘉奖,语文教育中语言不再是自然语言,话语不再是正常话语。
我国的语文教育为什么充斥着这么多虚假无用的东西,而不去培养学生真实有用的语言能力呢?第一,中国传统社会对人的语言交际能力要求不高。这一点与古希腊罗马重视人的“演讲”“论辩”能力形成鲜明对比。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小农经济造就了中国人对经典语言的膜拜和对应用语言的忽视。这种传统的一个致命缺陷是:忽视语言的交际本质,不重视人的语用技能,人的交际意识和交际能力不强。第二,百年来的现代语文课程知识开发走的是抽取结构语言学、现代语法、文章学等所谓新知识路子。这套知识目前看来有的是假的、错的、不实用且脱离真实语言实际的。第三,我国语文教育有“泛文学”“泛道德”情结,总以为语文教育要承担道德教育、灵魂塑造的任务,而对更广泛的实用语文教育重视不够,还以为它们很简单,根本不用去学。
当今社会对人的交际能力和复杂情境中的语言运用能力要求越来越高,学会交流和沟通已经成为人的基本素养。我们每天的生活中都面临着不同的语言交际任务,这些交际任务对象不同、目的不同(叙述、说明、娱乐、抒情、辩论、感动、审美、号召行动),就造成各种语体、文体、语言功能效果上的不同。过去那种只要听瞳、说出、简单读写就能应付生活的语言能力,需要向能应付复杂社会文化情境的语用能力转变。
目前我们的语文教育总体上来说只是简单地读懂、说出或者写出来,至于对谁说写,为什么说写,说的、写的得体不得体,合适不合适,效果好不好,这些问题是不大考虑的。对于语言应用中的读者意识、目的意识、语境意识,我们还缺乏一种理论上的自觉。
回到上面那些作文“精彩片段”,“排比+比喻”的话语方式在一般的心灵鸡汤式的小散文里也许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在一些议论文甚至说明文中,有些散文诗似的表达就显得不伦不类。就像当年叶圣陶先生嘲讽的有些老师本来是写信向他请教语文教学上的问题,本来应该把问题陈述清楚就可以了,可非得来一套“北风呼啸、乌云密布”之类的抒情不可。这是我国语文教育语用、语境知识缺失造成的。
三、树立基于语用观的语文评价体系
目前来看只有借助语用学、社会语言学、传播学理论,才能引导语文教育回归其语用本质,才能矫正我国混乱不堪的语文课程目标体系,重建语文课程新的知识体系,重构当代社会需要的公民语言能力要素和指标体系。运用语用学的思想与理论改造我国现有的语文教育理论和知识体系是一项艰苦细致的理论重建工作,需要方方面面切实行动和努力。
1.国外语文教育对语用能力的重视
语用学及语用能力的提出对欧美语言课程标准有着重要影响。
英国2007年新修订的《语言艺术标准》中指出:“在英语学习中,学生将发展听、说、读、写等各种参与社会和就业所需要的技能。学生将学会富有创造性和想象力地表达自己,并与他人自信地和有效地沟通交流。”
美国1996年颁布的《国家语言艺术标准》提出:“学生能够针对不同的对象和目的,运用多种不同的策略和恰当的要素进行交流。”美国南卡罗莱纳州2007年颁布的《语言艺术标准》强调,学生要“为读者而写”,“为了写好,学生必须经常写并为不同的目的写”。其中渗透着交流意识、读者意识和目的意识。
加拿大阿尔伯特省《中小学英语语言艺术课程标准》的目标是:“使每个学生理解和欣赏语言,在各种针对交际、个人发展和学习情境中,自信、自如地运用语言。”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英语课程标准》中“情境性理解”一项,包括如下内容:“识别自己和他人的写作目的”,“说明自己和他人的写作目的和对象”,“为特定的目的和对象选择恰当的文体类型来写作”,“针对各种情境、目的、读者选择恰当的文本类型写作”,“根据情境、目的和对象调整写作”。
上述国外语文课程标准和要求,都比较重视语言文字的实际运用,强调听说读写要看对象、有目的,从而突出真实的语言交际应用能力。与国外母语课程标准中对语用交际重视不同,我国的语文教学长期以来缺乏读者意识、目的意识、文体意识、语境语用意识。
2.构建语用型的语文素养评价体系
运用语用学知识构建新的语文能力素养体系,是一项艰苦细致的知识开发工作,需要我们以“语用能力”为总纲,在口语交际、阅读、写作等各个教学领域分别进行基于语用的语文知识开发和理论体系重建工作。
比如评价一篇文章的好坏优劣,过去主要依照的是文章学的四指标,即“中心突出、内容充实、结构完整、语言通顺”。这些指标其实质都是关于一篇好文章的文本标准,并没有涉及这个文本的语用因素。比如这篇文章:写给谁的?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意图是什么?基于这个对象和目的选取什么样的材料合适?采用何种结构、文体和语言表达风格?这个语用环境才是衡量好坏优劣以及为什么好坏优劣的真正依据。
欧美著名的“6+1”文章评价标准就渗透着丰富的语用观和语用意识,在衡量一篇文章时要质询的问题有:文章的题目合适吗?
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什么?
我要表达的重点信息是什么?
对这个话题,我了解足够多的细节吗?
我能否让读者一读起来就不想放下?
我的开头吸引读者吗?
我这篇文章的顺序是什么?
文章的细节有没有更好的呈现方式?
我的文章易于浏览吗?
文章的主要信息是否与主题有关?
文章的结尾如何,是否完整并让人回味?
这篇文章像我在说话吗?
文章是在说我最想说的话吗?
文章适合我的读者并吸引他们吗?
香港谢锡金曾提出写作中的“传意能力”并指出学生应掌握的传意能力包括:
能了解作者的身份,立场和写作动机;
能了解读者的身份,价值和期望;
能清楚知道写作的目标,写作契约和发表媒介;
能弄清文章的讯息;
能适当运用人称,选择文章格式配合各种场合;
能书写各种传意文章,例如:书信,公函,便条,启事,声明,新闻稿,投诉信,会议记录,应征信,各种政府表格等;
能适当运用传意策略。
上述语用型语文知识来源于真实的语用情境并应用于真实的语用活动之中,这是真的、活的、有用的语文知识。运用这样的知识去教学,语文教学才会找回本真,才能练成真实的语文能力。
我们目前的语文教育还缺乏这样基于语用的语言教育理论视野,缺乏基于语用的语文知识体系,更缺乏基于语用的语文教育评价指标体系。这是我国语文学科教育走向专业化、科学化、实用化,实现真语文教育的最大制约。
参考文献
[1]叶圣陶.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2—3.
[2][英]S.皮特·科德.应用语言学导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3:28.
[3]全球华人少年美文写作大赛扬州擂响决赛战鼓[DB/OL],http://www.xiancn.com/gb/news/2007—08/04/content_1271604.htm
[4]QCA.The National Curriculum for English[EB/OL]http://currieulum.qca.org.uk
[5] NCTE and IRA.Standards fnr the English Language Arts[DB/OL],http://www.reading.org/downloads,publications/books/bk889.pdf.
[6]洪宗礼,柳士镇,倪文锦主编,母语教材研究:第六卷[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7:303,
[7]丛立新,澳大利亚课程标准[c].章燕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9-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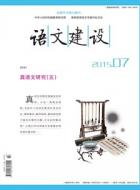
- 卷首语 / 佚名
- 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立德树人系列活动 / 佚名
- 基于语用观的语文能力评价 / 荣维东
- 语用学视野下的语文教学改造 / 徐默凡
- 立足语用构建语文教师专业素养 / 朱雨时 靳彤
- 语用观下的语文教材编写策略 / 魏小娜
- 文体感:写作行为的目标预期 / 潘苇杭 潘新和
- 学生主体真伪辨析 / 张承明
- 诗词欣赏教学与想象活动的组织 / 单学文
- 视角转换,激活语言 / 唐缨
- 文本解读应该尊重的四个标准 / 杨帆
- 古典诗歌欣赏的基础范畴(三):意脉 / 孙绍振
- 再读范仲淹《渔家傲》 / 王金伟
- “侧坐莓苔草映身”新解 / 成晓东
- 意象叙事:《红楼梦》中的风筝描写 / 王人恩
- 高考作文:最欠缺的是思维 / 冯渊
- 高考语文江苏卷之我见 / 谢嗣极
- 抗战特种国文读本述略 / 赵新华 贺朝霞
- 民国高级中学语文读本《词选》刍议 / 陆有富 崔微微
- 语文教学须“挖井见水” / 张清华
- 赤子情怀与人性光辉 / 邹诗鹏
- 一本让人“受用”的好书 / 赵志伟
- 《美国语文》教材编写启示 / 陶静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