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建设 2015年第7期
ID: 359172
语文建设 2015年第7期
ID: 359172
民国高级中学语文读本《词选》刍议
◇ 陆有富 崔微微
胡适《词选》自1927年由商务印书馆刊行后,就被列为民国高级中学国语专用读本,此后八十余年,风行海内,影响至今。龙榆生在他的《论贺方回词质胡适之先生》一文中曾说道:“自胡适之先生《词选》出,中等学校学生始稍稍注意于词,学校之教授词学者,亦几全奉此为圭臬,其权威之大,殆驾任何词选而上之。”龙氏对于《词选》之态度我们暂且不论,但从他的话语之中可以窥见胡适这部《词选》在当时传播之广,影响之大,并被广泛接受的事实。其实,从词体发生和演变的角度来看,这部《词选》固有许多令人不尽满意之处,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者对此多有论及,但如果从教科书的角度来看,它确实在当时白话文运动的背景下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
一、新体诗歌的范本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1月)的发表吹响了白话文运动的号角,为新文学革命确定了基调。此后,白话文体的创作、白话书报的流播、白话教科书的推广日渐盛行,这种现象的出现无疑响应和充实了胡适的白话文理论,也激发了白话文体本身的活力。胡适也深知浅显易懂的白话文的普及毕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梁启超在1899年所提倡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也未能促使文坛上自觉形成以白话代替文言的变革。毕竟文言传统的庞大根系一时难以连根掘起,那些固守传统文化的保守者受儒家思想浸染甚深,进而造成他们对传统文化过分留恋,不愿意抛却中国固有的传统。有鉴于此,胡适在经过认真思考之后,决定从传统文体的白话词选本入手,进一步说明白话词的创作古已有之,白话文体的创作并非是“放离传统”,“摈不复道”。
其实,这部《词选》的编纂早在胡适1915至1916年留学美国期间就开始酝酿了。胡适在1916年所写的《谈活文学》中就已经将李煜《长相思》(云一緺)等七首词作视为活文学的范本了,并认为“吾辈有志文学者,当从此处下手”。此后,胡适深信选本“都应该表现选家个人的见解”,都体现着个人的审美趣味、个人目的以及选者在编选过程中的种种判断和扬弃。可是胡适为何不以其他文体作为选本实践他的白话文理论呢?我们知道,胡适是新体诗的倡导者,而词这种长短不齐的文体样式也最接近新诗,此时国人所接受的西方诗歌也是长短不齐的形式,因此他选择借用这些白话词作为新体诗歌创作的范本,进而指导新诗创作。其实胡适早在1910年就开始模仿词体的形式创作白话词,虽然有些作品的格律与词谱不甚吻合,但业已看出白话词与新体诗逐渐合流的信息。另外,晚清的诗界革命中词这种传统文体最难撼动,胡适希望对词体的革新有一个大胆的尝试,希望借这部《词选》实践他的白话文理论,进而使得他所提倡的白话文运动找到传统的依靠和庇护。
作为高级中学语文读本的《词选》所选作品注解寥寥,十分易读,对于高级中学的学生来说非常容易入门。难怪龙榆生评价说:“自胡适之先生《词选》出,中等学校学生始稍稍注意于词”,“近人胡适辑《词选》独标白话……其在现代文学界中,影响颇大”。这部《词选》在民国时期中等学校的影响可见一斑,实现了胡适希望利用这部传统的“活的语言”选本来树立一个标杆的意图。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说道:“自从《三百篇》到于今,中国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其余的都是没有生气的古董,都是博物院中的陈列品。”又说:“真正有功效有势力的教科书,便是国语文学。”由此可见,胡适希望将浅显易懂的白话文借助词这种文体样式得以普及推广,进而达到启蒙民智的目的。
胡适在选词时也关注词作的审美趣味,注重词体的美感特质,关注词体演变发展的规律,致使这部《词选》具有可读易教的特性,因此在提倡白话文运动的背景下更容易被广大的青年学生所接受,进而达到胡适创造国语文学的目的。他认为“有了国语的文学,自然有国语”,因此他以理论指导、实践创作、选本示范的形式导夫先路,那种“为大中华,造新文学”的迫切心情以及对白话文体所寄予的热切希望昭然可见。
二、人格精神的垂范
《词选》选入唐宋词作共351首,其中入选率较高的有辛弃疾(46首)、朱敦儒(30首)、陆游(21首)、苏轼(20首),占到总数的三分之一,这足以看出胡适对这类词人的偏爱。究其原因,一方面胡适评价这些词人是从词史流变的角度进行的,他在苏轼的小传中说:“词至东坡而范围始放大,至朱敦儒、辛弃疾、陆游,这一派遂成为一大宗派。”胡适所言之“范围始放大”,是就东坡以诗为词和不拘泥于音律两个方面而言的,而朱敦儒、辛弃疾、陆游则继承了苏轼的创作理念又广而大之。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就是这四位词人的人格魅力。胡适指出:“真有内容的文学,真有人格的诗人,我们不妨给他们几分宽假。”可见胡适选词时不仅顾及词作者在词史的地位流变,还考虑到词的社会功能即词人品格、襟抱的垂范。
作为教材的《词选》持这样的选本观念,无疑对当时中等学校的学生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和教育意义。苏轼因其独有人格魅力而成为后代文人敬仰的典范,他进退自如,宠辱不惊,当遭遇坎坷之时,可以通向既坚持操守又全生养性的人生境界。《词选》中选录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卜算子》(缺月挂疏桐)等篇目所传达的内容就表现出苏轼在荣辱沉浮面前所特有的冷静、旷达的态度。朱敦儒志行高洁,天资旷逸,时有出尘之想。中年适逢世变,颇多家国感慨和身世悲凉之叹;晚年词作婉丽清畅,汪叔耕评价其为“虽杂以微尘,而其清气自不可没”。我们读其词亦可想见其人,他耿介疏狂的人格已经完全脱化到词作当中了。《词选》中“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懒慢带疏狂”(《鹧鸪天》)、“闲来自觉有精神,心海风恬浪静”(《西江月》)、“解散缰绳休系绊,把从前一笔勾断”(《鼓笛令》)等词句,正是词人那种洒脱无碍、闲适旷达心态的真实写照,显然是受到了苏轼的影响。
辛弃疾和陆游所具有的炽烈爱国热情几乎都是通过他们的词作表现出来的。他们不忍看到山河破碎、遗民泪尽,内心充满了建功立业、统一中原的理想。这种执着的意志和理念始终贯穿在他们心中,进而体现于词作。胡适对辛弃疾钦慕有加,说稼轩是“词中第一大家”,又说他“才气纵横,见解超脱,情感浓挚,无论作长调或小令,都是他人格的涌现”。不难看出,胡适选词对于人格精神的关注和阐扬。《菩萨蛮》(郁孤台下清江水)、《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水龙吟》(举头西北浮云)等词作中那种欲怒不怒、反复缠绵的特征,正是词人有志难申、悲慨难言的内在表现,从中正可看出稼轩心中一以贯之的执着意志和刚毅品格。陆游早年词作悲壮激烈,主要内容是书写爱国情怀,抒发壮志未酬的幽愤,与辛弃疾为近;晚年词作自有一种闲适飘逸的境界,刘克庄曾评价说“其激昂感慨者,稼轩不能过;飘逸高妙者,与陈简斋、朱希真(敦儒)相颉颃”,这正可看出他对于辛弃疾、朱敦儒二人风格的继承和发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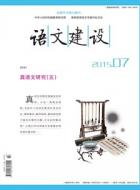
- 卷首语 / 佚名
- 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立德树人系列活动 / 佚名
- 基于语用观的语文能力评价 / 荣维东
- 语用学视野下的语文教学改造 / 徐默凡
- 立足语用构建语文教师专业素养 / 朱雨时 靳彤
- 语用观下的语文教材编写策略 / 魏小娜
- 文体感:写作行为的目标预期 / 潘苇杭 潘新和
- 学生主体真伪辨析 / 张承明
- 诗词欣赏教学与想象活动的组织 / 单学文
- 视角转换,激活语言 / 唐缨
- 文本解读应该尊重的四个标准 / 杨帆
- 古典诗歌欣赏的基础范畴(三):意脉 / 孙绍振
- 再读范仲淹《渔家傲》 / 王金伟
- “侧坐莓苔草映身”新解 / 成晓东
- 意象叙事:《红楼梦》中的风筝描写 / 王人恩
- 高考作文:最欠缺的是思维 / 冯渊
- 高考语文江苏卷之我见 / 谢嗣极
- 抗战特种国文读本述略 / 赵新华 贺朝霞
- 民国高级中学语文读本《词选》刍议 / 陆有富 崔微微
- 语文教学须“挖井见水” / 张清华
- 赤子情怀与人性光辉 / 邹诗鹏
- 一本让人“受用”的好书 / 赵志伟
- 《美国语文》教材编写启示 / 陶静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