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建设 2015年第7期
ID: 359166
语文建设 2015年第7期
ID: 359166
再读范仲淹《渔家傲》
◇ 王金伟
范仲淹的《渔家傲》词被冠以“秋思”之题,全词如下: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以往的研究对该词所表达的情感及其成因分析不足,故本文在剖析范仲淹心路历程并宏观把握时代背景的基础上,尝试进行新的认识。
一、评论与辨析
对这首词,宋代魏泰《东轩笔录》录其本事:“范文正公守边日,作《渔家傲》乐歌数阙,皆以‘塞下秋来’为首句,颇述边镇之劳苦。欧阳公尝呼为‘穷塞主之词’。及王尚书素出守平凉,文忠亦作《渔家傲》一词以送之,其断章曰:‘战胜归来飞捷奏,倾贺酒,玉阶遥献南山寿。’顾谓王曰:‘此真元帅之事也。’”。
这就是著名的“穷塞主之词”说。
事实上,范仲淹作为朝廷任命坐镇西北的帅臣,抵御外敌是卓有成效的,西夏人敬畏他“腹中有数万甲兵”。他自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三月以天章阁待制出知永兴军始,后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经略安抚招讨使等,战功卓著,威震敌军,时人传言“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他的作为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及赞扬,并因之而擢枢密副使、拜参知政事。因此范仲淹非但不是“穷塞主”,而恰是“真元帅”。
那么现实中的“真元帅”何以写出了“穷塞主”之词?我们认为这是词中抒发的情感造成的。远戍边疆,故园万里归不得,借酒浇愁并诉诸诗词,乃人之常情,词中“家万里”“归无计”即明确表明该词抒发了深切的思乡之情。这种感情的流露却与特定情况下的客观需求存在某种程度的违和感。
一方面,伤感忧郁的抒情和悲观内敛的情绪,在实际功用上可能会对士气产生消极影响。因为将士镇守边关是军事行动,需要张扬和强调的是爱国热情和报国壮志。本词情感的落脚点却专注于“家”,而非“国”。因“燕然未勒”故“归无计”,表现爱国报国的“勒石燕然”甚至成了归家的障碍,这与强调勇于牺牲、忘却小我的主导思想大相径庭。所谓“男儿有泪不轻弹”,更何况胸有甲兵万千的边疆将帅!而且,思乡情绪若超出合理的尺度,蔓延于军队之中则容易产生“四面楚歌”的效果,这势必会影响士气。明代瞿佑指出本词“句语虽工,而意殊衰飒。以总帅而所言若此,宜乎士气之不振,所以卒无成功也”,并认为这是欧阳修称之为“穷塞主”的原因,是有见识的。词中渗透的悲观内敛情绪,也确乎与“战胜归来飞捷奏”的乐观自信迥异。
另一方面,词作品(尤其是下片)呈现出偏于阴柔的审美格调,与“边塞雄风”有悖。塞上粗犷峥嵘的环境形成了边塞文学特有的品质,如钟嵘《诗品·序》中所言“负戈外戍,杀气雄边”,是雄浑豪壮的。而这首《渔家傲》却倾吐无奈,抒发悲苦,表现夜不能寐、愁肠百转,柔弱和缺乏信心的意思很明显。全词以“泪”收尾,更使审美上的柔性特征鲜明化。这属于审美范畴中的“优美”,与边塞文学通常呈现的“崇高”是迥异的。因为偏离了边塞题材通常表现出来的面貌,该词在一定程度上显出了困蹇窘迫的面貌——这亦是“穷塞主”之论的评判理由。
那么,如此豪词中渗透伤感的微妙情感是如何产生的?这要考察作者的人生经历及其心路历程,并紧密联系时代背景进行分析。
二、成因及背景
从个人主观思想上看,范仲淹有向专任儒臣回归的愿望,这并未因其立功边疆而改变。范仲淹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从出身上看是典型的文臣。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主张“弦歌始能治”(《上汉谣》)、“以理定区中,文经天下”(《铸剑戟为农器赋》),认为“儒者报国,以言为先”(《让观察使第一表》),并非诉诸武力。他在《用天下心为心赋》《尧舜帅天下以仁赋》《政治在顺民心赋》等作品中都对这种思想有所阐述。他入仕后积极参政议政,并几次不惜被贬而直言进谏,这其实是秉承了“文死谏”的传统。然而时势弄人,范仲淹没有在文臣的职位上实现政治理想,却在边疆危急时被任命为经略西北的将帅。客观条件造成了他报效朝廷的方式变为“武死战”,这与范仲淹的初衷是南辕北辙的。对范氏而言,这种危难之际奔赴边疆的行为,于国家是义不容辞,于其个人则可谓一时权宜。那么,坚决拒绝以文资换武阶则是完全出自他本愿了。庆历二年(1042)四月,朝廷诏命范仲淹、韩琦等四路帅为观察使。观察使是武阶,而且依宋制一旦以文易武则很难再换回。因此范仲淹连上三表,详细阐述了多条理由,坚辞任命。他又致信宰相吕夷简表明坚决的态度。即使身为边帅,他也非常看重自己“龙图老子”的身份,谨守“得带内朝职名节制边事”(《让观察使第二表》)的“履职模式”。由此可见,《渔家傲》词中“归无计”之“归”,实非单纯意义上的回家乡,也暗含了重回朝廷,同时回归文臣“岗位”的意思。范仲淹思想中的念家与爱国情怀统一于用文臣报国的理想途径上。
范仲淹如此思想倾向的形成,是由宋朝文人政治的特色体制造成的。“崇文抑武”“以文驭武”格局在宋初形成,文人士大夫待遇优厚、受到重用,如蔡襄在《国论要目·任材》中言:“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虽有武臣,盖仅有之。”而武官却一直备受猜忌防范,故北宋有狄青,南渡后有宗泽、岳飞等,虽战功赫赫却均以悲剧收场。文武有别,以文易武者往往仕途坎坷,如柳开主动换武而仕途坎坷;张亢几度变换文武身份故终不得志。文尊武卑,轻视武官在当时非常普遍。仁宗初年李维以文阶易武职,受到文官嘲讽抨击;真宗陈尧咨因射术非凡被朝廷改为武职,即使许以节度使的隆高头衔,其母竞也以“不务行仁化而专一夫之伎”为由杖之并“碎其金鱼”,宋朝甚至堪称“武士的悲哀”时代。这正是范仲淹不愿改任武阶、坚持文臣身份的客观原因。
而推敲《渔家傲》词中的情感,更要仔细考察范仲淹的个人际遇。专任文臣时范仲淹因“死谏”而屡遭贬黜;身为边帅时他唯“死战”报效,本已远离朝中斗争,却也遭遇了凶险的政治处境。庆历元年(1041)范仲淹焚毁了夏主元昊送来的有辱宋廷的书信,此事遭到朝臣弹劾:“大臣以为不当辄通书,又不当辄焚之,宋庠请斩仲淹”。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是常识,镇守边关的将帅本有便宜行事的权力,但军权极可能转化成为君权的威胁,因此对于臣子来说也成了双刃剑,助其建功的同时也带来了风险。赵宋王朝自来有不杀文士的传统,但对手掌兵权者却缺乏信任。范仲淹作为文臣几次直言顶撞皇帝、太后和宰相,都只是被贬出京;但当其镇守边疆,手握兵权时,竞出现了上述危机。范仲淹深谙个中道理,因此他一面不愿意从武,一面又不得不如履薄冰地尽职尽责做好一名边帅。范仲淹“以儒者奉武事”的个人际遇及其心境,正是形成他词中豪迈又夹杂柔弱的风格的内因。
沈际飞在评论时指出《渔家傲》词类比地以例说明:“昔宋儒有自翰林左迁,至任谒当辖,退而叹日:‘今日廷参,始觉身是县令。’盖不左迁,不知县令之苦。”。人生经历影响了作品表达的情感。欧阳修也偶写边塞诗词,但他没有驻守边关的经历,最多只是作为使臣过境边塞,故终究无法理解一位镇守边疆的文臣在特殊军事体制下,苦心孤诣抵御外敌、维系国家安全的心情,也难以感受到范仲淹那样交织着个^理想与现实矛盾的复杂感情。刘永济指出二者写作动机的差异:“范词乃自抒己情,欧词乃送人出征,用意自然不同也。”人是“真元帅”无疑,而词有“穷塞主”的意味,正是这首《渔家傲》词的独特之处。
三、意义与启示
本文尝试将范仲淹《渔家傲》词作为典型个案,进行深入细致分析,从学术研究层面向两方面进行努力。一是由典型选题扩展到类型研究。本词是宋代边塞词的代表作之一,其中表现的作者深受时代政治体制影响,纠结于文臣、武将身份之间的矛盾心情,是很有代表性的。唐代士人“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枞军行》),讲求“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岑参《银山碛西馆》),表现在边塞诗歌中多是寻求从武而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而至于宋代,世殊时异,“勒石燕然”退化成为保境安民的“防守型”要求;士风丕变,边塞诗歌中则多是“功名早晚就,裴度亦书生”(范仲淹《依韵答梁坚运判见寄》)这样文人本位立场的话语。宋代诗词,即使是边塞题材,也少有“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岑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的气魄。在对比中深入认识边塞诗歌在唐、宋时代的不同面貌,由此也可对“唐音宋调”(即唐宋文学的差异)有更全面深入的认识,正是本题的扩展性意义。二是注重文本精读与背景分析结合的方法。文学研究中,文史互证、“知人论世”的方法是值得重申的。缺乏对于相关背景性内容的深刻发掘,就无法准确理解文学作品的内在意蕴。我们探究这首《渔家傲》词,因为注意到了作者范仲淹徘徊于文武之间的个人境遇,又进一步深挖其背后的时代原因,就更有助于一层层剥离表面,深入其实质。
另外,这首《渔家傲》是宋词和古代边塞文学中的名篇,也入选了多种当代的中学语文教材。因此,本文的探究对语文学科的教学也有一定的启示。教学中,对于特定类型作品主导风格的强调是必要的,但这样也很容易走向“贴标签”的歧途,如讲到杜甫就“沉郁顿挫”,讲到苏轼、辛弃疾就豪放,讲到李清照就婉约,这是不妥当的。解读《渔家傲·秋思》,若简单地从边塞诗词的一般特征来评价,强调词作表现戍边将士爱国之情和建功立业之心,就很难认识到其独特价值所在。如此不仅埋没名作的真正价值,还容易将文学鉴赏和品评带向程式化、机械化。因此要实现素质化语文能力的培养,就要鼓励发散性思维,扬弃“标准答案”,强调传统解读和权威性观点的“参考”价值。开放、大胆地思考问题,解读经典作品时“尽信书,不如无书”,不唯教参是从,这样经典才能常读常新,文学的魅力才不会减色。
参考文献
[1][宋]范仲淹.范仲淹全集[M].李勇先等校点.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734~735.
[2][宋]魏泰.东轩笔录[M].李裕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卷十一.
[3][宋]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卷七.
[4][清]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1251.
[5][梁]钟嵘.诗品·序[M].北京:中华书局,1991.
[6][宋]蔡襄.蔡襄全集[M].陈庆元等校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32.
[7][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卷九.
[8]陈峰,武士的悲哀:北宋崇文抑武现象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9][元]脱脱等编.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10271.
[10]张璋等编纂.历代词话[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524.
[11]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微睇室说词[M].北京:中华书局,2010:43.
【本文系江苏省2014年度普通高校及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北宋边塞诗研究”(编号:KYLX一0676)的部分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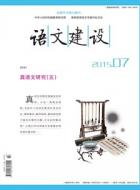
- 卷首语 / 佚名
- 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立德树人系列活动 / 佚名
- 基于语用观的语文能力评价 / 荣维东
- 语用学视野下的语文教学改造 / 徐默凡
- 立足语用构建语文教师专业素养 / 朱雨时 靳彤
- 语用观下的语文教材编写策略 / 魏小娜
- 文体感:写作行为的目标预期 / 潘苇杭 潘新和
- 学生主体真伪辨析 / 张承明
- 诗词欣赏教学与想象活动的组织 / 单学文
- 视角转换,激活语言 / 唐缨
- 文本解读应该尊重的四个标准 / 杨帆
- 古典诗歌欣赏的基础范畴(三):意脉 / 孙绍振
- 再读范仲淹《渔家傲》 / 王金伟
- “侧坐莓苔草映身”新解 / 成晓东
- 意象叙事:《红楼梦》中的风筝描写 / 王人恩
- 高考作文:最欠缺的是思维 / 冯渊
- 高考语文江苏卷之我见 / 谢嗣极
- 抗战特种国文读本述略 / 赵新华 贺朝霞
- 民国高级中学语文读本《词选》刍议 / 陆有富 崔微微
- 语文教学须“挖井见水” / 张清华
- 赤子情怀与人性光辉 / 邹诗鹏
- 一本让人“受用”的好书 / 赵志伟
- 《美国语文》教材编写启示 / 陶静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