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9年第10期
ID: 135966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9年第10期
ID: 135966
语文教学中训练之探究
◇ 王友君
训练在我国传统语文教育中的地位不容忽视。张志公先生曾经把我国传统语文教育的主要特征概括为“四线并进,分线合击”,也就是识字、写字、读书、作文四条线各有自己的训练体系,最终融合起来形成一个人的语文能力。识字从“三百千”开始,写字从“上大人”开始,读书从韵文到骈散的吟咏背诵,作文从对对子到八股,都是有很强的训练成分的。国外的母语教育也普遍重视通过训练形成学生的语文能力。法国1995年的语文教学大纲指出:“学生应该将语言训练和课文学习结合起来,必须具有语文训练、精神陶冶及艺术欣赏之价值”。新加坡、加拿大等国的语文教学大纲也有类似的表述。
一、训练之现状
在新课改的今天,翻遍《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在众多新名词、新概念的缝隙中找不到“训练”二字。再翻看《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在“教学建议”第四条中看到了这样一句话:“语文教学要注重语言的积累、感悟和运用,注重基本技能的训练,给学生打下扎实的语文基础”。通篇仅此一处提到“训练”,而且还是捎带提及的。可以说不是新课标研制组的专家们刻意回避“训练”,便是“训练”根本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
毫不夸张地说,矫枉过正,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似乎可以说成是潜藏在绝大多数国人灵魂深处的思维规律。人们的思维在权威性的导向下也似乎一夜间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课堂教学的价值取向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人们纷纷将目光瞄向游离于训练之外的所谓的提升学生能力,致力于培养学生人文素养等之上,“训练”一下子成了千古罪人,直接导致的是“训练”被打入了冷宫。表现在实际语文教学中,便是凌空蹈虚式的语文课越来越多,所谓“双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早已置之不顾,在一些公开课上这种倾向尤其明显,日常的语文课由于还有考试这道关紧紧“卡”着,才使老师们不敢太荒腔走板了。
为什么“训练”在语文课程改革的今天会跌落到如此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境地?原因也许很多,但主要原因是人们对“训练”的理解有误。比如有人认为“训练”就是习题演练,完全是应试教育的产物,与素质教育背道而驰;有人即使不排斥“训练”,但也感到只有在要求学生掌握某些最进步的技能的时候才需要训练,高层次的能力如“感悟”“创新”是训练不出来的,尤其在“人文性”被抬到了超越一切的高度的当下,“训练”往往被当作“人文性”的对立面而受到“谨慎对待”。
二、训练之释义
其实“训练”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我们来看训练的释义。小篆“训”,从言川声,本义作“说解”解(见许慎《说文解字》),乃以名言嘉言教导人之意,故从言;又因“川”本作“贯穿通流水”解,为河渠之通称,又疏导水流使通意,“说教”乃导人通于义理,故“训”从川声。小篆“练”,从糸,柬声,本义作“煮缣而熟之”解(见《急就篇》颜师古注),乃煮丝使熟之义,故从糸;又以柬本作“分别择之”解,煮丝使熟,须分别择之,以防其过熟或不熟,故“练”从柬声。“贯穿通流水”,“煮缣而熟之”实为训练之要义:使融会贯通,犹流水之贯穿,具穿透与通透之精神;并使臻于纯熟,熟则巩固,不熟则择之使熟。
《现代汉语词典》说,训练,有计划有步骤地使更具有某种特长或技能。
叶圣陶老先生在《阅读是写作的基础》一文中说过:“什么叫训练呢?为使学的东西变成他们自己的东西”。在这里,叶老虽然没有揭示“训练”的内涵,但却道出了“学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必须通过训练的基本观点。
上海特级教师钱梦龙谈到训练,从构词的角度看,“训”和“练”其实各有所指,“训”指教师的指导、辅导,是教师一方的行为;“练”指学生的实践、操作,是学生一方的行为。从教学过程中师生的关系看,学生是学习、发展的主体,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学生又是不成熟的学习者,还离不开教师必要的指导和帮助,于是形成了教学中教师“导”,学生“学”这样一个师生互动的过程,就是“训练”①。
笔者认为钱老师的解释更为实用,可见,训练不是什么习题演练,也不是语文课上那种刻板烦琐的字、词、句操练,与“题海”“应试”更是完全不搭界。语文课只要有师生互动,就必定呈现训练的形态。取消训练,等于取消师生互动,这样的语文课还怎么上?
三、训练之必要性
训练乃是语文教学的基本形态。叶圣陶老先生生前与语文教师谈语文教学,常常强调训练的重要性,他的很多话对我们理解训练的要义很有启发。例如他说:“学生须能读书,须能作文,故特设语文课以训练之。其最终目的为:自能读书,不待老师讲;自能作文,不待老师改。训练必须做到此两点,乃为教育之成功”②。朴朴素素的语言,却道出了“训练”的真谛,学校之所以设置语文课程,就是为了训练学生使之达到“自能读书”“自能作文”的最终目的。换言之,学生要学会阅读,学会写作,就要靠实实在在的阅读训练,实实在在的作文训练,舍此而外,别无他途。
新课标指出:“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因而语文教育既包括工具教育,又包括人文教育,这一点在当前的语文界已取得了广泛的共识。但却偏偏有人死盯着人文性不放,过分夸大人文教育在整个语文教育中的地位。并且他们以此为据振振有词:学生的人文品格应通过浸润渐染,积累感悟的方式来培养,而不是训练,语文教学应该淡化甚至摒弃训练。其实,这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论调,只要稍加分析,便知道是站不住脚的。
语文是一个整体,工具性和人文性是经脉互连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二者发展的角度来看,它们是水涨船高的关系,工具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发展,人文教育也会相应地取得一定进步。而我们知道,要掌握语文这门工具,必须进行严格的训练,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所以说,语文训练不仅不同语文的人文性相悖,而且它还是推动人文教育的一个间接手段。并且,在语文新课标中对“两性”的表述中,将“工具性”置于“人文性”之前,笔者认为不是一种任意的排序,因为“工具性”毕竟是语文课程的基本属性。“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同样需要在训练过程中实现。通过训练,学生掌握了语文这门工具,就获得了一个自我发展的能力,从而就为他将来的成功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不正是对教育者最大的人文关怀吗?
总而言之,“训练”还不该退出历史的舞台。相反,语文教学中合理的训练是应该有的,这是语文教学的生命本色。训练是提升学生能力的重要手段,它是基石,只有基石坚固,搭建在其之上的能力大厦才能安稳;训练是拓宽学生视野的重要方式,要想开阔学生的视野,首先必须以学习和运用为前提,再以多种内容和方法的灵活运用为途径,说穿了,学习和运用,内容和方法,实则也指的是“训练”;训练是培养学生人文素养的重要载体,语文教学中的“训练”是第一性的,“人文素养”是第二性的,训练是人文素养的基础,是人文素养的载体,人文素养蕴涵于科学合理的训练之中,没有科学合理的训练,也就不可能有人文素养的积淀和厚重③。
谈了这么多,皆是因为训练并非可有可无,并非就该退出历史舞台。训练是一种有效的方法,教学生习字,教学生读书,教学生作文,是训练其习字、读书、作文的方法。所谓授之以鱼,不若授之以渔,正是这个道理。训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同课程是过程,教学是过程一样,训练也是伴随学习始终的一个过程,训练是学习主体间的多元互动。
四、训练之合理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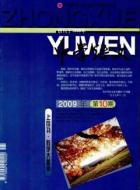
- 具有独创意味的王松泉论著“结构示意图” / 张文秀
- 王松泉写作教学思想试论 / 纪 勇
- 叙事作品中的“交代”例说 / 倪丽霞
- 文学定篇组合的关系模式(三) / 胡根林
- “场”思维在高中作文教学中的有效迁移 / 甘玲珑 余宗波
- 野芳虽晚不须嗟 / 李祖贵
- 议论文写作训练尝试 / 刘名桂
- 网络环境下的语文课教学构想 / 刘 祥
- 反思历史,寻找进步的真理 / 吕 品 武玉鹏
- 《逍遥游》:放飞心灵的自由(下) / 何永生
- 李商隐《锦瑟》诗旨为“陈情说”探析(下) / 曹兴戈
- 文言文学习要注重句的把握 / 李 政
- 失意中的精神贵族 / 陈 秉 章国华
- 实施“三还”教学,促进高中语文课程改革 / 江艳桃
- 读图时代:语文教育应关注学生的视觉素养培养 / 张青民
- 不愿说再见 / 李爱梅
- “越国以鄙远”的“鄙”是意动用法吗? / 吴林方
- 朱熹语文教育思想的当代解读与启示 / 何 宇
- 孔子的教育之道(九) / 韦志成
- 《秋声赋》“一气之余烈”注商 / 林忠港
- 语文课堂就是要让学生读、悟、说 / 赵精忠
- 让生存之“思”走进语文教育 / 马 进
- 苏教版语言瑕疵正误 / 郭祥圣
- 关于高效课堂的冷思考 / 刘海燕
- 语文教学中训练之探究 / 王友君
- 中美语文教科书课后练习设计的个案比较 / 刘 敏
- 怎样把握长文短教短文长教中的“度” / 张朝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