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9年第10期
ID: 135952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9年第10期
ID: 135952
李商隐《锦瑟》诗旨为“陈情说”探析(下)
◇ 曹兴戈
尾联是直抒胸臆。不过“当时”二字又不易确解。许多人只是在此联与上文的结构关系上争论不已。笔者以为,厘清“此情”与“当时”的含义,对于确解诗旨至关重要。“此情”句,论者多解释为“此种哀伤之情直到现在也不堪追忆”。“当时”二字也有人释为“现在”,如汪师韩的《诗学纂文》。笔者以为,“此情”固然是从上四句来的,但解释不能纷乱,当与“迷”、“春心”、“珠有泪”和“玉生烟”联系起来,表达对令狐氏真诚的感恩之心,最后点明“陈情”的目的。该诗与作者众多的《无题》诗类似,以香草美人作比,希望世人尤其是令狐绹能省察他沉痛婉款的内心。尾联诗意概括起来便是:这种真诚的感恩,这种追悔歉疚,何须等到今天成为追忆,即便在当初也已惭愧到觉得无以报答,现在你却因疑见疏,这种痛惜、怅惘叫我怎能承受呢?对于这种心情,《酬别令狐补阙》中“锦段(缎)知无报,青萍肯见疑”两句可为参证。而“惘然”至少是其陈情、剖白的余绪。“锦段”句典出张衡《四愁诗》:“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青萍”句典出陈琳《东阿王笺》:“君侯体高俗之材,秉青萍干将(均为宝剑名)之器。”刘、余释为“谓令狐厚谊,已虽无所报答,然实心念旧恩,古人于我,岂有按剑之疑哉?”①李商隐一生之反复陈情,既是向令狐绹表白自己“实心念旧恩”, 又是想要在世人面前洗刷“背恩”的冤名,这一点笔者前文已经揭明。
总起来说,这首诗以“锦瑟”起兴,以“思华年”为倾诉的由头,以“迷”辩解,以“托”示诚,以“珠有泪”说感恩,以“玉生烟”引共鸣,最后归结到“此情”何堪承受,诗意自然流淌,婉转曲折而又沉痛深切地袒露了心曲。深谙李商隐诗风的令狐绹,自然不难破解其流珠泻玉的“语码”。
四、李商隐的“令狐情结”和“陈情心态”是解读《锦瑟》的唯一钥匙
可以这么说,在牛、李党争的阴影里,李商隐有着横亘一生的“令狐情结”和挣脱不得的“陈情心态”。这与其诗歌的寄托性和迷离幻美的意境特点以及它的深情婉约、用典工切的风格有内在的联系。他之所以热心于“楚雨含情俱有托”的手法和风格,与其说是艺术趣味所致,毋宁说是出身、境遇、心态和性格使然。
李商隐是晋凉武昭王李暠的后裔,唐高祖李渊是李暠的第七代孙,一度家世显赫。对此诗人也常沾沾自喜。但至其祖、父辈已门庭衰落,其父李嗣仅担任过获嘉县令。商隐十岁时父亲去世,境况十分狼狈。他在《祭裴氏妹文》中述及当时情境是“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他在十二岁时靠替人抄写文书和出卖劳力谋生,生活十分辛苦。十八岁时到洛阳以文干令狐楚,楚时任天平军节度使,招其为幕僚,辟署巡官,不仅教他习吏习文,还“岁给资装,令随计上都”。开成二年(837年)因有令狐父子作奥援,商隐得中进士。当时高锴知贡举,“令狐绹雅善锴,奖誉甚力,故擢进士第”(《新唐书·文艺传》)。后来商隐至徐州幕“复干绹,乃补太学博士”(《新唐书·文艺传》)。因此,李商隐对令狐氏心存感恩。这种感恩之情在他的诗文里有充分的表达。如《上令狐相公状》:“自幼从岁贡,求试春官,前达开怀,后来慕义,不有所自,安得及兹。”《奠相国令狐公文》:“将军身旁,一人白衣。”对此冯浩评曰:“楚爵高望重,义山受之最深。”李商隐《撰彭阳公志文毕有感》写道:“百生终莫报,九死谅难追!”见出感恩情结之深重。及至绹主动疏远,他还“屡启陈情”,在《酬别令狐补阙》中,仍然将绹当作最可托付的朋友:“弹冠如不问,又到扫门时。”以至纪昀批这两句诗“太无骨格”。
那么,如何看待令狐绹及世人对李商隐“背恩”(或“忘家恩”)、“放利偷合,诡薄无行”的评价呢?这些指斥,当然是因为他入王元茂幕府娶王氏之女以及其后入郑亚幕府并受其辟署和推荐为官——这两位在党争的派系中都属“李党”。对此,大多论家予以理解。的确,那是境遇所迫,乃“择木之智,涣丘之公”,相反还见出令狐绹不伸援手的“谿刻”。这样的评价大致是公允的。但是,在当时社会价值体系中,李商隐的选择却与奉师交友及尚义的道德准则相悖。从表面上看,让商隐背上“背恩”、“薄行”的黑锅也不是没来由的。这便是李商隐产生焦虑心理的根由,也是他“屡启陈情”的主要原因。而还原批评以知人论世,则是我们评价历史人物时应有的尺度。
再说李商隐对待牛李党人的态度。对王茂元、郑亚,他除了感恩戴德外,还颇引为知己,这无疑是出自真情和道德归依。即便是对李德裕,其在为郑亚代作的《会昌一品集序》里也极力推崇其事功;同样,对牛僧孺,他在《樊南乙集序》中也写道:“是岁葬牛太尉,天下设祭者百数。他日尹言:‘吾太尉之薨,有杜司勋之志与子之奠文,二事为不朽。’”他给牛的祭文受到京兆尹的夸赞,说明他对牛也是极力赞美的。上述材料能说明什么呢?其一说明他并无党派之见;其二也能说明他的为文,或珍重所托,或出自真情,或出自对大人物德望的仰慕,总之有一种对自己的文字万分珍惜的态度。随之而来的便是另一个问题:李商隐确是无意于党争的,但能不能说他与党争无涉呢?——他的经历和境遇已经作出了否定的回答。也正因为如此,令狐绹对其日渐疏远,世人目之以“放利偷合”、“诡薄无行”。回到当时的社会风尚和道德氛围,应该还是有其“合理”性的——请注意,我这里并非要对诗人进行道德评判,而是说无论是出于干谒、释疑,还是出于辩诬或情绪的释放,诗人都有其充分的理由去“屡启陈情”并且“喋喋不休”的。无论是出于“功名”的汲汲以求,还是出于对“内美”的重重修炼;无论是缘于脆弱的性格,还是源于纤细的情感;无论是悬于世道中的“立身为人”,还是为摆脱内心道德感的煎熬,诗人都有充足的理由对着明确的或假想的读者去屡陈“此情”的。而“此情”的内涵又十分丰富和复杂:感恩、追悔、怨望、期盼甚至愤激,他于悲痛惨怛中才不得不发而为有所寄托——借类似屈宋的香草美人比君子的手法来表达隐微的心曲。于是十五首《无题》和类似于《无题》的《锦瑟》成了他的最佳选择;甚至也无怪乎他的诗形成秾艳绮丽、深情婉约和用典工切的风格。
而再进一步说,如果我们认同冯浩之观点——《锦瑟》写成是在东川时期的大中七年(853年),那么李商隐对令狐氏的“感恩”与“陈情”,是否有可考的事实或存在的合理性呢?答曰:有。李商隐在写于大中五年(851年)的《上兵部相公启》(答绹请他写碑之启)有句云:“思长感集,恪钝惭深,但恐涕洟,终斑琬琰。”他说两代人的恩德深长,自己为难以报答而惭愧。“涕洟”,周振甫评曰:“既有感恩之泪,又有自伤之泪。”商隐与绹的交往终于何时?吴乔以为:“至(商隐)流落藩府,终不加恩,乃发愤自绝”,“九日题诗于绹厅事,绹遂大恨,两世之好决然矣。”笔者以为,“终不加恩”是事实,但将《九日》题于绹厅事,“两世之好决然矣”,显属主观武断。《玉溪生诗集》中有《留赠畏之三首》,冯浩考第一首为诗人“东川归后作”,认为“东川府罢,义山必由京而至郑州,时畏之(李商隐的同科进士和连襟)方得意,故溯及第之年而荣枯不齐也”。“东川府罢”为宣宗大中十年(856年),时商隐四十五岁。冯还以为后二首实为令狐绹而作,说的是夜里去看绹,绹喝醉了,一早又忙着去上朝。第三首说他夜里等绹,盼望绹到来。清何焯批曰:“难于明言,而托于狎昵之词”,亦陈情之作。这观点为周振甫所肯定②。由此可证,至东川府罢,李商隐不仅还去令狐绹家里,而且继续在向他写诗陈情。见出“两世之好决然矣”的说法过于粗率。至于是否有《九日》题诗于绹厅事,周振甫有较为合乎情理的分析。先看《九日》这首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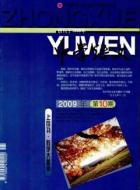
- 具有独创意味的王松泉论著“结构示意图” / 张文秀
- 王松泉写作教学思想试论 / 纪 勇
- 叙事作品中的“交代”例说 / 倪丽霞
- 文学定篇组合的关系模式(三) / 胡根林
- “场”思维在高中作文教学中的有效迁移 / 甘玲珑 余宗波
- 野芳虽晚不须嗟 / 李祖贵
- 议论文写作训练尝试 / 刘名桂
- 网络环境下的语文课教学构想 / 刘 祥
- 反思历史,寻找进步的真理 / 吕 品 武玉鹏
- 《逍遥游》:放飞心灵的自由(下) / 何永生
- 李商隐《锦瑟》诗旨为“陈情说”探析(下) / 曹兴戈
- 文言文学习要注重句的把握 / 李 政
- 失意中的精神贵族 / 陈 秉 章国华
- 实施“三还”教学,促进高中语文课程改革 / 江艳桃
- 读图时代:语文教育应关注学生的视觉素养培养 / 张青民
- 不愿说再见 / 李爱梅
- “越国以鄙远”的“鄙”是意动用法吗? / 吴林方
- 朱熹语文教育思想的当代解读与启示 / 何 宇
- 孔子的教育之道(九) / 韦志成
- 《秋声赋》“一气之余烈”注商 / 林忠港
- 语文课堂就是要让学生读、悟、说 / 赵精忠
- 让生存之“思”走进语文教育 / 马 进
- 苏教版语言瑕疵正误 / 郭祥圣
- 关于高效课堂的冷思考 / 刘海燕
- 语文教学中训练之探究 / 王友君
- 中美语文教科书课后练习设计的个案比较 / 刘 敏
- 怎样把握长文短教短文长教中的“度” / 张朝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