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大语文论坛 2012年第6期
ID: 134125
中学语文·大语文论坛 2012年第6期
ID: 134125
时政性与思想性结合的典范
◇ 侯笑一
【摘 要】在鲁迅散文的阅读和教学过程中,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其文章的思想性受到了教师和学生高度的赞扬和重视,而其文章的时政性却少有人发现和挖掘,作为鲁迅散文的一体两面,不了解时政性就必然无法理解鲁迅文章深刻的思想,随着时代的推移,这个问题也会表现得越来越突出,进而成为困扰我们语文教学的一个瓶颈。本文通过《记念刘和珍君》这篇课文,结合相关材料,透过时政性分析思想性,点明了二者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提醒我们在鲁迅散文的教学过程中,要把二者结合起来不可顾此失彼。
【关键词】鲁迅散文 背景知识 时政行 思想性
《记念刘和珍君》是鲁迅散文中的名篇,也是中学语文教材的传统课文。深邃的内涵、澎湃的激情、高度的正义感,使本文具有了永恒的价值和长久的魅力,可是对于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中学生来说,文章的语言精辟却难懂,思想厚重却不易把握。究其原因与读者的阅历固然有关,时代差异导致的代沟却不容忽视,我们只有把握住文章时政性的特点,才能认识到北洋政府的腐朽专制,才能理解那个时代青年人的社会责任感,才能体味到鲁迅先生的愤怒与哀痛。所以解读本文我们需要了解以下几方面的背景知识:
一、中华民国
文章开篇作者便写到“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对中国近代史缺乏了解的人很容易把这个“中华民国”理解为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其实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中国的时间是1927年至1949年。而本文写作的时间是1926年南京国民政府还没有成立,那么这个“民国”指的是哪个“民国”呢?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辛亥革命说起,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可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辛亥革命的果实被掌握清王朝精锐部队——“北洋新军”的袁世凯窃取了。1912年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1916年他又因复辟帝制在全国上下的一片讨伐声中下台。袁世凯死后无人具有足够能力统领整个北洋军队及政权,各领导人以省割据导致分裂,以军队为主要力量在各省建立势力范围。在名义上仍接受北京政府的支配。对外仍称“中华民国”,但北京政权实际上由不同时期的军阀所控制,故而在北洋军阀时期北京政府又有北洋军阀政府(简称北洋政府)的称呼。鲁迅作品,大多数都注明了写作时间,但是他几乎从不像其他民国时人一样,在作品或信件后注上“中华民国某年某月”,要么只注月和日,要么用公历纪年。这是什么原因呢?鲁迅1933年在其《自选集》序言中说:他“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了”。这是对他自己之所以参加文学革命的一个回顾。就是因为鲁迅对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产生了怀疑,他才会从沉默中爆发,拿起笔做刀枪,向愚昧不堪的国民性挑战,向统治者的权威挑战。中华民国,在他的眼里,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辞藻,不仅没有意义,有时还被人用来做掩饰罪恶勾当的遮羞布,冠冕堂皇,让人以为改朝换代、天下太平了。因此,他是不轻易在作品中注明“中华民国”的字样的,因为他理解的“中国民国”在现实中并不存在。1925年2月12日,他提起笔来,“忽然想到”:
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
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很像在德法等国里的犹太人,他们的意中别有一个国度。
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
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
退一万步说罢,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因为我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虽然还只有十四年!
而在《记念刘和珍君》那篇文章开首就写上中华民国,正有他的深意。这篇文章是愤怒声讨军阀刽子手将屠刀砍向爱国青年的,他已经“出离愤怒”了,写上“中华民国”正是在愤怒悲哀中发出的讽刺之声,让人感到,在屠刀和鲜血面前,这几个字显得那样的苍白和无力。
二、三一八惨案
1926年3月,奉系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进兵关内,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党军队同奉军作战,这本是内战,然而日本帝国主义公开援助奉军,干涉中国内政,派军舰驶入大沽口,并炮击国民军,守军死伤十余名。严重伤害了中国的主权,国民军开炮自卫还击,将日本军舰逐出大沽口。事后,日本认为国民军破坏了《辛丑合约》,与英、美、法、意、荷、比、西等8国公使,于16日向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等种种无理的要求,并限令48小时内答复,否则以武力解决。同时各国派军舰云集大沽口,用武力威胁北洋政府。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一致愤慨,1926年3月18日,北京总工会、北京学生联合会、北京反帝大联盟、广州代表团等60多个团体、80余所学校约计5000余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大会议决:通电全国一致反对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军舰;电告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战。会后,群众结队前往段祺瑞执政府请愿,要求段政府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立即驳复八国通牒。段祺瑞担心局势失控,命令执政府内的预伏军警以武力驱散游行队伍,结果造成当场死亡47人,伤200多人的惨剧。事后执政府又用嫁祸卸责的手法,反诬学生等人假借“共产学说”谋乱。
外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中国人民当然有权利要求政府作出强硬的姿态,这符合国家民族的利益,也是政府应尽的责任,可是段政府不但没有顺应民意,反而用最为粗暴的方式来压制民意,用御用文人的笔来强奸民意,妄图用武的和文的两手来使民众“沉默”!“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段政府迎来的不是民众的“沉默”而是沉默中的“爆发”。因为,对于一个政府来说,一旦向徒手的青年学生与平民百姓开了枪,不仅践踏了为政之德的底线,也越过了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界限。正如周作人在《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书》中所言:屠杀学生和平民的政府,“同情、信用与期望之损失是无可估量,也无法挽救的”。所以,在屠杀发生后不到一个月,段祺瑞政府就在遍布全国上下的抗议声中于1926年4月倒台。
“三一八”事件是一个永恒的历史事件,影响了包括鲁迅在内的整整一代知识分子,为什么“三一八”惨案会在这一代人的心中留下如此刻骨铭心、须臾不忘的记忆?周作人在一篇论及“五四与三一八”的短文里这样写道:“正如五四是代表了知识阶级对于北京之政府进攻的成功,三一八乃是代表北京政府对于知识阶级以及人民的反攻的开始,而这反攻却比当初进攻更为猛烈”,“在三一八那年之前,学生和教授在社会上似乎保有一种权威和地位,虽然政府讨厌他们,但不敢轻易动手”,“及至三一八那时,执政府卫队公然对学生群众开枪,这情形就不同了。对知识阶级的恐怖时代可以说就此开始了”。
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此次惨案的发生鲁迅是没有思想准备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因为在此之前政府开枪镇压学生是没有先例的,所以当消息传来的时候,他的反应是“竟至于颇为怀疑”,他不曾料到执政府竟“下劣凶残到这等地步”。请愿反对的是八国联军,政府竟枪杀学生,公然为侵略者张目,让亲者痛,仇者快!面对着“中国军人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惩创学生的武功”,鲁迅觉得自己所住的地方毫无公平正义可言,正如“非人间”的地狱。在地狱中居住的人当然是“哀痛”的,但是他们并不怨天尤人,而是面对着血淋淋屠刀挺起胸膛,勇敢地承担起时代赋予的责任,他们是当之无愧的“猛士”。牺牲固然是“哀痛”的,而为了大多数人的光明而牺牲的人也是“幸福”的,因为他们活得有理想、有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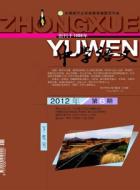
- 古诗文教学中弘扬传统文化的策略研究 / 杨建平
- 语文课堂改革与语文素质教育之我见 / 谭地文
- 构建三美,让语文课堂“嗨”起来 / 冯艳丛
- 和谐课堂 / 张云杰
- 奏响课堂和谐的旋律 / 史梅香
- 高中语文教学的反思切入点 / 蒋维明
- 浅谈新课改课堂教学讨论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 于晓颖
- 唱好语文课堂开场戏 / 薛文琰
- 探究式学习 / 谢允有
- 古典诗歌诵读教学例说 / 唐玉琳
- 百花齐放春满园 / 闫子强 宁改换
- 试谈中学古典诗歌教学的有效策略 / 牙韩国
- 在阅读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 / 颜金花
- 《沁园春.长沙》标点商兑 / 李万程
- 运用对话策略建设高效阅读课堂 / 陈承标
- 浅谈高中语文课堂有效教学的实施 / 吴亚红
- 高中语文教学中的灵魂对话 / 李莹
- 浅析古诗词鉴赏中“衬托”与“烘托” / 黄钱娥
- 互动式作文训练浅谈 / 吴森茂
- 走出小说教学的误区 / 唐上等
- 浅谈对“模式作文”的几点思考 / 王晓慧
- 结构技巧 / 刘学飞
- 浅谈高中语文阅读教学 / 陈怀
- 刍议陆游诗歌的“悲”与“愤” / 周新顺
- 让传统文化点亮高考作文 / 闫庆
- 寻常巷陌雪梅香,平仄人生叹炎凉 / 张吟湄
- 关于培养学生议论文写作中的思辨能力的思考 / 刘碧芳
- 如何用事实论据让论证更充分 / 杨孝茜
- 让思辨为你的作文提档升级 / 邢延
- 《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爱》教学设计 / 刘明娟
- 作文教学之要务 / 杨乐勤
- 议论文用例论证的有效提升 / 叶永松
- 创新是作文教学之魂 / 王东梅
- “三读”“六导”赏析千古美文《陈情表》 / 郭连友 李小玲
- 直面生活 观照自身 巧写作文 / 赵顺宏
- “有心”与“无意”之间 / 贺江湖 徐地仁
- 关于写作有效教学策略的一点思考 / 庄海玲
- 让学生作文的语言灵动起来 / 刘志勇
- 作文拟题之“五讲”“四美” / 姜全德
- 现代观念观照下的渔父形象再解读 / 龚丽丽
- 了解语文,学习语文 / 郭凤敏
- 与其“扬汤止沸” 莫如“釜底抽薪” / 石爱国
- 作文创新立意与动态思维 / 周淑粉
- 培养审美情趣 提升人生境界 / 谢伯雄
- 作文批改要注重方式与实效 / 梁健灵
- 用学生的亮点点亮学生 / 王静
- 如何使自主、合作、探究式课堂学习更加高效 / 张燕
- 为理想而献身 / 王静
- 语文老师,别荒了“黑土地” / 王荣清
-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 焦曼
- 初中生文言文语感培养的教学策略 / 邵晶
- 情境式教学方法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应用 / 孙春玲
- “省”字作“曾经”解? / 贺烨
- 除了教材,我还讲些什么 / 杨杰
- 从句式上引导学生理解语句的内涵 / 谢友明
- 从“断发”说开去 / 刘杰
- 诵读三法在古诗词教学中的运用 / 周兆青
- 文学教育的反思及对策 / 吴武明
- 文言文教学的“三味课堂” / 徐蕾蕾
- 文言文有效教学的尝试 / 胡永生
- 关于语文课“学生投入—走上讲台”教学模式的思考 / 郑瑞娟
- 高中语文方法论漫谈 / 徐柏兴
- 曲尽表达的“孤独”情愫 / 陈培
- 用“月份咏物诗歌”激扬人生豪情 / 范徽生
- 全才张衡之“三心” / 彭俊生
- 高三语文阅读复习之我见 / 吴国爱
- 时政性与思想性结合的典范 / 侯笑一
- 深度嫁接阅读经验 精彩呈现阅读境界 / 钱珏
- 语文教师应该超脱一些 / 张良会
- 刍议诗歌阅读鉴赏类探究性试题 / 邹虹 赖庚祥
- 做一个开启学生心灵的语文教育工作者 / 张鸿文
- 得胜高考现代文阅读 / 舒俊华
- 漫谈语文教师的语文素养 / 张军红
- 考场作文应做到“八化” / 王平
- 例谈成语题的“陷阱”和解题步骤 / 施映宏 涂春蓉
- 选择问句中问号到底应该怎么用? / 汪明爽 王志文
- 压缩语段十种常用题型例解 / 周耀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