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07年第10期
ID: 92927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07年第10期
ID: 92927
散文真情艺术美谫论
◇ 滕永文
一
文学不是无情物,情感是文学艺术的精魂,没有情感的文学就没有生命的活气和灵性。所以有人说:“艺术就是感情”(罗丹),也有人讲文学就是情学,文学的本质是始于感情而终于感情的。古人曾认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毛诗序》)古人在这所强调的“情”对于诗具有重要作用,其实,它对于所有的文学文体也具有同样的意义。
在文学创作中,情感“不但是一种推动力、组合力,而且是一种发现力和创造力,发现生活美和创造艺术的美的力量。”[1]创作者通过驾驭情感来建构作品中的形象体系,用饱含情感的内容来产生尽可能大的感染力量。创作者写诗作文,无非是教人、喻人、冶人、育人。要能达到教、喻、冶、育的目的,其作品必须饱和深沉浓郁的情感。因为,“没有感情这个品质,任何笔调都不可能打动人心。”(狄德罗语)[2]感情之于作品,犹如血液之于人身。对于“情种的艺术”——散文来说,它对情感的要求更为浓郁、更为强烈。它作为一种文学样式,“是一种充满了主观意识的文体,在描摹社会人寰和自然环境的时候,总是侧重于诉说自己对于这客观世界的印象、体验和感悟,这样就十分容易打开自己心灵的窗户,跟许多读者朋友进行诚恳与亲切的对话,因此也必然会洋溢出真挚、灼热、浓郁和深沉的感情来。”(林非语)[3]散文是创作主体面对接受主体抒发情怀、感叹人生、、诉说忧乐的最真实、最诚挚的艺术。在对“情”的表达中,最为自然、最为真实、最为痴情者,莫过于散文之情。当你浏览散文佳作时,那一篇篇散文犹如创作者打开的心灵之窗,在向你表白,在向你诉说,在向你倾吐那感人的肺腑之言,那么纯真,那么朴素自然。学界泰斗、著名作家季羡林先生在多年的创作生涯中,遍尝了个中的酸甜苦辣,对于散文写作,也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独特见解,他认为散文的精髓在于“真情”二字,“真”就是真实,“情”就是要有抒情的成分。创作主体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是散文美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
散文真情艺术美这种特质首先要求创作主体要真诚。
庄子曾经说过:“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渔父》)[4]“情感贵在真诚”这一思想体现着中国式的精神超越路径,也使后人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精神自由。真正的艺术家应该是真诚的,应该忠实于内在世界的客观性和感官感觉(包括幻觉)的真实性,以成熟的技巧精确地描绘自己构造的理想世界。
真实是艺术的生命,更是散文的生命。
在文学创作的园地里,散文以它可贵的品质——“真”而独树一帜。无论是散文名家还是散文爱好者,他们在创作或品评散文作品时,在对散文的真、善、美作艺术鉴赏时,无不把“真”放在首位。真人、真情、真心、真语,离开了“真”,散文就失去了生命。散文是“文学的测谎器”,“在一切文学的类别中,最难作假、最逃不过读者明眼的,该是散文。”[5]作假、编造、矫情、虚饰等是散文的大敌。
长期担任《散文》月刊执行主编的贾宝泉先生在谈到自己的创作体会时曾经说过:“何谓好散文?或谓好散文应该是怎样的?这自然可以作出多种回答。我的看法是:好散文是写作者以典型的个人笔致表现的他本人在特定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所能达到的最高智慧和最真纯的情感。”[6]即是说,好散文最能真实地折射出散文创作主体的人品、性格和创作态度,能直接展示创作主体的思想情绪和人格面貌,更能凸现其创作个性。散文的“真实”之感,首先来源于散文创作主体的真诚之心。“真诚”指的是创作主体对客观现实的态度,对接受主体读者、观众、听众的态度,自然也是他对自己的态度。就是说,要敢于正视现实,直面人生,好就是好,坏就是坏,不粉饰,不美化,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嘴说自己心里的话,说自己想说的话,说自己思考过的、自己相信的话。诚实的人格,要求创作者不仅仅是在散文中能淋漓尽致地写出自我的喜好或厌恶,而且要充分表现出自我的道德观念或思想情操。卢梭曾经坦言,他的写作是率真的,既不隐瞒坏事,也不添加好事,只是率真地吐露自己的真实胸襟与言行,如果写作中出现与真实有偏差,那也只是记忆上的问题,而不是有意为之。在《忏悔录》这部自传里,卢梭以一种惊世骇俗的大胆,真实地展示了“一个资产阶级个性的‘我’有时像天空一样纯净高远,有时却像阴沟一般肮脏污浊的全部内心生活。”[7]卢梭这种直面人生、正视自我的勇气,曾给中国的文人很大的影响。被称为“中国的卢梭”的郁达夫,为了辞绝虚伪的罪恶,在《达夫日记》等作品中,坦诚地、赤裸裸地写出了自己的心境,记录了自己情感的变迁,心理的伤痛,爱情的波折,乃至行为的颓放,在当时的文坛,无疑像一声惊雷,惊得一些假道学家、假才子们狂怒。瞿秋白在狱中写下的《多余的话》等作品,也对自己的灵魂、自身的矛盾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他无情地剖析自己对政治兴趣的淡薄,工作能力的不强,特别是卷入无法摆脱的最大矛盾——政治家和文人的矛盾。其在自我解剖、自我否定方面并不亚于卢梭。他们这种自我暴露、自我解剖,既可以让读者体会他们襟怀坦白的胸襟、敢于直面灵魂的勇气,也使他们的散文个性淋漓尽致地突现出来。巴金晚年创作的那部“说真话的大书”——《随想录》之所以蜚声海内外,也是与他那颗创作的真诚之心分不开的。他在《〈病中集〉后记》说:“我不靠驾驭文字的本领,因为我没有本领,我靠的是感情。对人对事我有真诚的感情,我把它们倾注在我的文章里面,读者们看得出来我在讲真话还是撒谎。”“我的座右铭便是:‘绝不舞文弄墨、盗名欺世。’”“我只想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全部爱憎消耗干净,然后问心无愧地离开人世。这对我是莫大的幸福,我称它为‘生命的开花’。”“我必须用最后的言行证明我不是一个盗名欺世的骗子。”(《〈无题集〉后记》)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到,巴金晚年的这部大书,实在是他不可抑制的感情催逼的结果,正如他说的:“我有一肚皮的话,也有一肚皮的火,还有在油锅里反复煎了十年的一身骨头。”(《〈无题集〉后记》)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同时是一部需要“把笔当作手术刀一下一下地割自己的心”、让他“感到剧痛”的作品。——我们可以想见,在这样的创作过程中,作家的人格力量、艺术家的良心——也就是巴金所说的“真诚的心”、“真诚的感情”,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散文女作家王英琦在《我能这样地生活》一文中曾深有感触地写道:“散文太需要真诚了,真诚即是散文的灵魂。”钱谷融先生也说:“本来,一切文学作品都是要显示作者的性情和品格的,但在诗歌、小说和戏剧作品中,作者常常用韵律节奏、故事情节等把自己装裹起来,使读者不容易一下子看清他们本人的庐山真面目。散文则不然,作者毫无装扮,甚至不衫不履,径自走了出来。凡有所说,都是直抒胸臆,不假雕饰。他仿佛只是在喁喁独语,自吐心曲;或如面对久别的故人,正在快倾积愫。读者读过他的作品,一下子就看到了作者本人,看到了他的本色本相。所以散文是最见性情之作,既是最容易写的,也是最难写的。一切没有真性情的人,或者不是真有话要说的人,最好不要来写散文。”[8]“我对散文,要求的是真诚、自由、散淡。能够成为一个散淡的人,真诚地写作,就可以达到自由的境界,写出真正令人爱读的散文来。”[9]可以这么认为:没有哪一种文体像散文这样最坦诚地面对读者,与读者进行着真诚的对话,或旧事重提回忆童年生活,或轻声慢语述说家长里短,或胸怀挚情抒发内心感受,或思绪深沉追问人生价值。散文家总是毫不遮掩地展示着自己的喜、怒、哀、乐、爱、恶、惧,让读者清楚地看到了他们的赤诚之心,看到了不同性格的真实的创作者的自我再现。读巴金的《随想录》,我们看到了一位世纪老人的自责自省与那颗“燃烧着的心”;读鲁迅的《朝花夕拾》,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位文化伟人对随韶光而去的美好的童心、天性、爱和人情的吊唁与缅怀;读《赋得永久的悔》(季羡林)、《母亲》(曾卓)、《我与地坛》(史铁生)、《背影》(朱自清)、《多年父子成兄弟》(汪曾祺),我们体会到的是那种不管岁月的长河如何流逝,永远也不会消失的人类最普通也最珍贵的感情——父母之情;读《藤野先生》(鲁迅)、《回忆鲁迅先生》(萧红)、《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季羡林)等散文,我们感受到的是他们对恩师的崇敬之心和感激、怀念之情;读《给亡妇》(朱自清)、《亡人逸事》(孙犁)、《怀念萧珊》(巴金),我们可以深深地感受到那种刻骨铭心、难以忘却的思念亡妻之情;读《碗花糕》(王充闾)、《我的嫂子》(李辉英),我们能体会到那股浓浓的叔嫂之情……
[##]
散文创作主体的真诚,不仅仅是能在散文中再现出真实的自我,而且要做到说真话、言真情、展真性、道真趣,以达到从审美层次上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引起读者的共鸣,发挥散文陶冶性情的美感作用。散文创作主体只有以真实的自我与接受主体进行感情的交流,以真实的自我与他们进行心灵上的碰撞,才能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撼动人心的感人效果,才能让读者永不忘记,流传久远。
三
从审美的过程来看散文,创作主体的真诚是创造美和传达美的前提,但还不是艺术美的本身。要创造美、传达美,使作品具有审美品质,还必须有一系列“中介”环节,情感就是这个中介环节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散文作为抒情艺术,它抒发的是创作主体对一定客观事物的主观态度和情感体验,正如黑格尔在《美学》中所说:“它所特有的内容就是心灵本身,单纯的主体性格,重点不在当前的对象而在发生情感的灵魂”。因此,人们把散文当作创作主体的一种抒发“自我情怀”或“心灵独白”的文本。
散文创作主体在创作过程中非常看重情感这一文学创作的动力性因素,因为,他们知道,情之所动,才有文学,文学是情感动态的形象化表现。凡优秀的文学作品,都应看作是创作主体生命的艺术形态,是生命苦乐等复杂体验所导致的情感波动。正是有了充沛的情感作为一种动力性因素,文学作品才有了强大的生命力,如果抽掉了情感因素,那么,许多文学将不是文学。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就是创作主体情感流程的实现。散文作为一种最直接、最具个性、最具真情的文体,它可以通过创作主体在多种多样的作品中所表现和流露出来的鲜明的爱憎、蒸腾的情绪、点滴的感受、具体的细节及有滋味的情调来传递这种真情,来传递这种来自创作者的深切体验和感受。散文正是通过“写自我的真实体验、真实经历、真实言行、真实心境”来凸现其真情艺术美的。
周作人曾于1922年写过一篇千字短文《初恋》,在文中他把情窦初开的少年隐秘心理酣畅淋漓地表现出来,他写道:
我不曾和她谈过一句话,也不曾仔细的看过她的面貌与姿态。大约我在那时已经很是近视,但是还有一层缘故,虽然非意识的对于她很是感到亲近,一面却似乎为她的光辉所掩,开不起眼来去端详她了。在此刻回想起来,仿佛是一个尖面庞,乌眼睛,瘦小身材,而且有尖小的脚的少女,并没有什么殊胜的地方,但是在我的性的生活里总是第一个人,使我于自己以外感到对于别人的爱着,引起我没有明了的性之概念的,对于异性的恋慕的第一个人了。
我在那时候当然是“丑小鸭”,自己也是知道的,但是终不以此而减灭我的热情。每逢她抱着猫来看我写字,我便不自觉的振作起来,用了平常所无的努力去映写,感着一种无所希求的迷?的喜乐。并不问她是否爱我,或者也还不知道自己是爱着她,总之对于她的存在感到亲近喜悦,并且愿为她有所尽力,这是当时实在的心情,也是她所给我的赐物了。在她是怎样不能知道,自己的情绪大约只是淡淡的一种恋慕,始终没有想到男女关系的问题。[10]
这里,“我”的朦朦胧胧的初恋的喜悦情怀,“我”的自然属性的“本我”的性意识的端倪,“我”第一次对于异性的爱慕等内容都在这些美妙动人、撩人情怀的文字中流露出来,非常真实、自然、贴切而又传神,那种初恋的陶醉,初恋的幸福,初恋的深情,初恋的自作多情都在“我”的笔端真实地流淌。作家周作人没有粉饰,没有做作,只是如实地捕捉“我”的情态、“我"的心境。
作为世界性的文化名人和具有崭新思想的大学教授,朱自清最初的婚姻却是百分之百的中国旧式的,即完全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法则主宰的。这从他的早期散文《择偶记》和《给亡妇》中,可以看到事情的全部过程。另外,如果说中国旧式婚姻制度也可以产生“美满家庭”的话,朱自清也可称得上是一个典型例子。1916年寒假,19岁的朱自清奉父母之命在扬州与武钟谦女士结婚。婚后夫妻感情甚好,但武氏身体病弱,且操劳过度,终于1929年冬病逝,终年仅32岁,遗下三子三女。1932年10月,朱自清用他固有的至情妙笔,写下他的名文《给亡妇》,寄托他对前人的未忘之情。在该文中,作者追忆了亡妻武钟谦生前的种种往事,与其说作者在为死者哭泣,不如说是生者在向死者致歉。妻子的辛劳、克己、无私以及对孩子、丈夫的挚爱,在作者的笔下一一展露出来。普列汉诺夫说过:“最大的美在于真和朴素,而真实性和自然性构成艺术创作的必要条件。”[11]《给亡妇》就写出了作者的亲身经历、切身体验,作者在对现实生活的叙写中,充满了对亡妻的真挚的思念之情、内疚之情。全文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美丽的修饰,没有技法的炫耀,而是朴素、实在的追思,就像作者在与亡妻对话,至痛的思念,没有裹挟泪水;至痛的倾诉,没有哭泣的哀嚎。那明白如话的叙述,那通俗易懂的语言,就像一泓秋水,缓缓地流进读者心田,那实情实景,却让人刻骨铭心,实难忘怀。
海明威曾说:“你别美化,坚持写出实际的状况,如果你想美化,你不但做不了好事,也写不出实际情形来。”这里,海明威强调的是写实,写生活中的实人、实事、实景、实物,进而写出作者的真实情感来。散文这种讲究真实性的文体,其所蕴含的情感理应是真实的,但真实而缺少真挚性的情感则很难打动读者。真挚,应该是一种强度和深度的要求,情感仅仅停留在一般的真实上是不够的,否则很难产生动力性效应。也就是说,散文创作中所强调的真情,不能仅仅满足于一般的真实,理应以“典型的个人笔致”把真实的情感写得情真意切,达到强烈感人的程度,要能找到“真挚”之点,只停留在一般真实的程度上是意义不大的。像巴金的《怀念萧珊》、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王充闾的《碗花糕》、宗璞的《哭小弟》等作品之所以能深深地打动读者,是因为它们都是充满了真挚情感的好散文。
四
梁启超在《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一文中,曾这样论及情感及情感教育:“情感的作用固然是神圣,但他的本质不能说他都是善的都是美的。他也有很恶的方面,他也有很丑的方面。他是盲目的,到处乱碰乱迸,好起来好得可爱,坏起来也坏得可怕,所以古来大宗教家大教育家,都最注意情感的陶养。老实说,是把情感教育放在第一位。情感教育的目的,不外将情感善的美的方面尽量发挥,把那恶的丑的方面渐渐压伏淘汰下去。这种工夫做得一分,便是人类一分的进步。”[12]他认为情感教育的最大的利器,就是艺术。“音乐、美术、文学这三件法宝,把‘情感秘密’的钥匙都掌住了。……所以艺术家的责任很重,为功为罪,间不容发。艺术家认清楚自己的地位,就该知道,最要紧的工夫,是要修养自己的情感,极力往高洁纯挚的方面,向上提?,向里体验。自己腔子里那一团优美的情感养足了,再用美妙的技术把他表现出来,这才不辱没了艺术的价值。”[13]著名教育家、美学家蔡元培先生也曾说过;“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14]散文作为一种富于主观抒情性的融汇了作家真诚个性及深层人生意蕴的文学体裁样式,也是陶情冶性、给人以审美享受、实施美育的一种必不可少的重要方式。因此,创作主体在创作过程中就应该注意“情感的陶养”,既要注意情感的深沉、真挚,又要注意抒情的“度”,不矫情,也不滥情,同时,还要使表达出来的情感合乎健康的审美情趣,不应媚俗、低俗。这也是散文真情艺术美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散文的写作中,不管创作主体采用“一泻无余的‘奔进的表情法’”(即用“喷”的方式,直陈心曲,直接剖白内情,直接抒发自己激越、奔突、翻涌、腾跃、燃烧的情感,它常常以独白式或宣告式的形态出现,作者的情感活动呈透明状,同时也可以映照出作者率直的个性),还是采用“含蓄蕴藉的表情法”(此抒情方式常常借助外在形象的描绘或叙写,隐曲吐露作家的衷肠,或情隐话中,或情隐景物),[15]都应该抒写出创作者真挚的张扬着个性的闪烁着人性光芒的情感来。
[##]
而反观时下的散文创作,有几个明显的不良倾向需要注意:一是一头钻进故纸堆里,专拿名著屁股说事儿,玩味词语、把玩器物的散文太多;二是跟风现象严重。刘亮程的乡土散文火了,一下子就冒出来一大群乡村散文作家;三是释放个人情绪,在花花草草、风霜雨雪、河流山脉之间转来转去,小发现小感觉的散文太多;四是打扮青春、编造浪漫、罗织感人故事的散文泛滥;五是翻检历史碎片、类似地方志写作的散文太多;六是专搞书评、时事评论和思想文化名著解读的散文太多。这些散文作品虽说也张扬着个人的性情、洋溢着感官体验,但同时也暴露出脱离生活、内容空洞、个人趣味的浅薄虚伪(如在相当多的散文中流露出浓郁的“官本位意识”和功利意识)、缺少底层的、生命的和灵魂的直接触动和真切体验,这些“伪情绪”泛滥的作品读多了,就会败坏胃口和食欲,最后引发出病症来。这种写作无论多么华丽,最终都只能为读者所摒弃。
结语
散文作为一种自由宽松的文体,它无须虚构,也无须造作,只需用自己的人生体验与生命情感真诚地与读者展开交流,只要说真话、抒真情,像巴金那样“要掏出自己燃烧的心,要讲自己心里的话”,就能感染、打动读者。
真情,不仅是散文的魅力所在,更体现着散文的品格。
参考文献:
[1]童庆炳.文学审美特征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37.
[2]西方古典作家谈文艺创作[C].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105.
[3]林非、李晓虹、王兆胜选编.百年中国经典散文:挚爱卷[M].呼伦贝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6:1.
[4]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上)[A].北京:中华书局,1985:40.
[5]余光中散文·自序[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1.
[6]贾宝泉.散文镜花词[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253.
[7]柳鸣九.<忏悔录>译本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20.
[8][9]钱谷融.真诚、自由、散淡——散文漫谈[A].毛时安主编.海上名家文丛·长夜属于你[Z].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6:34,37.
[10]周作人.雨中的人生[M].李文选编.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45-46.
[11]形象思维资料汇编[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37.
[12][13]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下)[A].北京:中华书局,1985:417-418.
[14]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下)[A].北京:中华书局,1985:460.
[15]董小玉.各体文学审美之旅[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71-276.
滕永文,南京三江学院中文系讲师,阅读学与写作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职博士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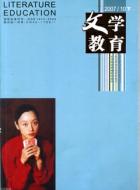
- 南国的风 / 黎林果
- 自由的声音 / 周永清
- 短文两篇 / 牟 茜
- 随笔两则 / 方 成
- 仰望东坡 / 阮 晓
- 寻找回家的路 / 周 霁
- 307的可爱男生 / 徐宏寿
- 逝去的经典 / 黄荣婕
- 中职生及其说话能力训练 / 曾淑梅
- 学生评教是建设和谐校园的平衡点 / 孙翠琴
- 语文教学应加强学生口语训练 / 魏少良
- 教师要学会跟学生解围 / 朱忠金
- 要科学合理引导学生爱美 / 薛 忠
- 语文教师的望闻问切 / 刘加洪
- 把课堂还给学生 / 陈 英
- 多媒体在语文教学中的作用 / 沈心华
- 语感实践训练方法谈 / 段水清
- 让学生尽情享受课堂教学 / 谢继合
- 多媒体使语文教学更有魅力 / 李素艳
- 做一个风情万种的语文教师 / 顾 明
- 散谈小学阶段的古诗文教学 / 刁太祥
- 用创新的教法使学生乐学 / 卢 艳
- 语文课堂教学与想象力开发 / 张志远
- 散文艺术的虚与实例析 / 卢红英
- 培养良好习惯是素质教育的归宿 / 王凌红
- 母语教育的重要性 / 杜晓平
- 也说全民阅读的重要性 / 曾松林
- 对师生交流中教师语言的深层思考 / 罗修武
- 初中语文教师应具备的素质与能力 / 李志勇
- 回头再看教育上的经典语录 / 王业贞
- 口头作文的特点及训练方法 / 王保升
- 校园启事的写作亟需规范化 / 张兆华
- 短篇小说创作技巧例说 / 徐继雄
- 优化写作教学策略琐议 / 袁和平 袁娇萍
- 获得作文高分的几种技法 / 宗永臣
- 如何让作文闪耀出奇异的光彩 / 余建琼 余 澜
- 文章拟题的几个技巧 / 吕 兵
- 下水作文的操作要领 / 杲先旺
- 高考作文如何审题 / 余逊云
- 作文创新思维四法 / 汪群英
- 写作教学要注重的几个环节 / 文联霞
- 论新课程背景下小学生活作文教学 / 顾三川
- 写作前应拟定假想读者 / 崔铁梅
- 作文写作应重视三个积累 / 孙承先
- 如何激发学生写作的自主意识 / 张桂芳
- 作文评语要体现出三性 / 李爱华
- 自读课文阅读方法谈 / 彭治顺
- 课外阅读的指导艺术 / 娄新强
- 阅读教学要回归文本 / 黄 莺 朱 洁
- 阅读教学切忌盲人摸象 / 张振芳 张春梅
- 语文阅读教学的两面性 / 薛锦东
- 运用自主性阅读策略教好文言文 / 汪远忠
- 关于阅读教学的实践分析 / 睢瑞丹
- 阅读教学要切实运用探究性学习 / 李文洲
- 新课程视野下的阅读对话 / 翁进迁
- 关于阅读教学的优化问题 / 付友艳
- 《祝福》里“我”的作用 / 赵永刚
- 《沁园春·长沙》所体现出的革命情怀 / 伍运凤
- 解读鲁迅名作《明天》 / 高志明
- 《子夜》中主人公吴荪甫的两面性 / 毛三红
- 阮海彪《死是容易的》的生命意识 / 杨红祥 蒋代炳
- 《孔乙己》思想意蕴探析 / 蔡兴明
- 《日出》女主人公人物形象分析 / 张 杨
- 评梁实秋《雅舍小品》 / 檀 辉
- 《许三观卖血记》的音乐之声 / 祁雪婷
- 解读《百年孤独》的魔幻密码 / 耿红岩
- 在设疑解疑中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 周超勇 尹 琴
- 语文课堂教学中的探究性学习 / 刘泽红
- 语文自主教学可操作性探讨 / 汤小梅
- 文学审美鉴赏下的语文教学 / 檀华武 王章材
- 语言教学中的学习者因素探析 / 黄 惠 夏 楠
- 以《诗经》为视角看中学生的气质培养 / 赵向玲
- 语文综合性学习的实践与体会 / 樊雅娟
- 古汉语教学中的认知能力与创新精神培养 / 张桂梅
- 大学生的语文教育与人文教育 / 刘维娅
- 用爱与知识搭建和谐的教学桥梁 / 徐向莉
- 语文教学更应注重师生交往的民主性 / 江玲燕
- 文学课堂中如何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 / 许开松
- 语文课堂教学中的三美 / 李 娜
- 《羚羊木雕》教学实录 / 徐敏红
- 《大自然的启示》教学设计简案及实录 / 陈雨佳
- 说明文教学应多作些逻辑分析 / 孙国璋
- 在交流语境中有效实施话题教学 / 吴箫箫
- 汉语中女性称谓歧视现象分析 / 朱礼金
-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 / 毛素文
- 古希腊与罗马神话之比较 / 王昆仑 彭小梅
- 论《长恨歌》的主题思想 / 周国强
- 《红楼梦》五十八至六十一回的艺术特色 / 焦福生
- 博尔赫斯与残雪创作方法比较 / 姚莹?
- 李煜后期词的感伤色彩 / 赵晶晶
- 古代文人的秋愁情结 / 沈 鸿
- 沈从文的人文关怀及其对当下的影响 / 崔宗超
- 从纯文本角度看《三国演义》中鲁肃形象 / 王 伟
- 散文真情艺术美谫论 / 滕永文
- 论晓苏面对“底层”的两副面孔 / 李 勇
- 男色如花 / 吴珍艳
- 无非图个闲闲的散步 / 方英文
- 贪嘴 / 薛尔康
- 鲁迅是个有魅力的人 / 吴 俊
- 艺术:使人成为人 / 乔东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