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07年第10期
ID: 92926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07年第10期
ID: 92926
从纯文本角度看《三国演义》中鲁肃形象
◇ 王 伟
所谓历史演义是指“用通俗的语言,将争战兴废、朝代更替等为基干的历史题材,组织、敷衍成完整的故事,并以此表明了一定的政治思想、道德观念和美学理想”。[1]历史演义是小说,其本质是文学,不是历史,历史故事是它的题材。如果研究作品的创作可以在必要时考查史实,而于其他方面对已经形成独立文本的历史演义来说史料是没有意义的。无论作者创作初衷如何,读者接受和欣赏的对象都是小说文本,没有必要为此去读遍相关史料。读者阅读属于审美和消遣的范畴,而不是为了了解历史,否则就应该直接去研读史书。同样,文本研究也不能依赖史料。假如这些题材不是历史,而完全是由作者虚构出来的,那么作品的文学价值会消失或下降吗?当然不会。所以对于历史演义,如果不是研究其创作,就应该从纯文学角度探讨,而不宜参照史料去做毫无意义的“校对”。这是对其文学价值的认可。历史演义既然可以被看作一个虚构文本,那么就可以把它看成作者创造的一个新的世界的总和。这个世界中的一切,“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文本中的“存在”虽为作者所提供,却时常有着作者意想不到的妙用。这时作者创作阶段已经过去,文本脱离了作者的实际控制,并因其内部存在而展现出独特的文本文化,即特定历史语境中的历史内容。历史演义审美的一个关键正是对其文本文化的认可和尊重。如阅读《封神演义》就必须承认神仙法术,不能说那是封建迷信,小说不是政治教材。读《三国演义》对诸葛亮“多智而近妖”也应正确看待,在特定的文本文化和特定的历史语境[2]中“缩地”和“禳星”都是合理的,文本中诸葛亮不过是个与三国蜀相名字相同、事迹相类的一个能驱六丁六甲的神人而已。同样,其中的黄巾军也不是历史上的起义军,是文本社会中的反贼。李宗吾曾于《三国演义》中悟出一套“厚黑学”,把人际的种种权谋形象的概括为“脸厚”与“心黑”,这是作者始料不及的,作者的贡献恐怕只是制造了一个创作的“巧合”。然而,读者面对的只是文本,不是作者,阅读的目的也不在于重复作者的思考或追索作者的意图,更何况读者阅读乃是文本意义的再创造[3]。
关于《三国演义》(以下简称《演义》)鲁肃这一形象近年来研究者关注日多。鲁肃一直被认为是孙吴集团的主要人物,以前多定位为“忠厚长者”,而如今翻案渐兴,又有了夸大的倾向。其实没有必要去刻意挖掘文中机窍,鲁肃也是一个人,是个政治家,他具备战略家的品质,他有聪慧也有不足。鲁肃即将出场时作者借周瑜之口为之简单介绍:“姓鲁,名肃,字子敬,临淮东川人也。此人胸怀韬略,腹隐机谋。早年丧父,侍母至孝。其家极富,尝散财以济贫乏……”(《演义》第二十九回)“孝”是其文化背景中有德者的标志,诸葛瑾也“侍母至孝”,徐庶更为一“孝”终生不展其才。仗义疏财也是富人的一个德行,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资助刘、关、张征黄巾军的中山大商张世平、苏双和资助曹操讨董卓的孝廉卫弘。这两点只能说明鲁肃有德,所以关键在于“胸怀韬略,腹隐机谋”八字,尤其一个“隐”直接暗示了他大智若愚的特点。鲁肃“愚”于小事,全局上则是一流战略家。他为孙权分析天下大势:“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无法“为桓、文之事”;又“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今乘北方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而据守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同上)鲁肃说了两点:一是曹氏强大,刘氏衰微,孙权不可中兴汉室,只能自称帝王;二是如今形势俨然鼎足三分,即曹操、孙权、刘表,其余皆不足虑,且三家中刘表较弱,所以孙权应该趁此时曹操无暇南顾吞并刘表,与之南北对峙,建号称孤,再图天下。这使孙吴战略第一个目标便锁定了荆州。荆州位当冲要,乃用武之地,其主刘表却是一庸才。再看江左,东濒大海,南接荒蛮,北邻先为袁术后是曹操,皆兵多粮足而不可争锋,惟有西取荆襄,否则只能蜗居一角不得展足。于是经过两年准备,于建安七年孙权打败黄祖;至建安八年再次出兵,消灭黄祖,一度占领江夏。
刘表毕竟实力雄厚,孙权虽然一鼓作气攻克江夏却能取而不能守,又退回江东再作计议。此时荆州内部刘备支持的刘琦和蔡瑁支持的刘琮矛盾日益激化,待刘表病逝,内讧顿起,结果荆襄九郡竟落入曹操之手。倘若强大的曹操于汉上立稳脚跟,孙权再想获取荆州就几乎没有可能了。而且如今曹操正在封死孙权陆上的一切门户,形势十分严峻。于是,鲁肃在大方针不变的情况下为孙权谋划:“荆州与国接邻,江山险固,士民殷富。吾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今刘表新亡,刘备新败,肃请奉命往江夏吊丧,因说刘备使抚刘表众将,同心一意,攻破曹操;备若喜而从命,大事可定矣。”(《演义》第四十二回)鲁肃要替孙权招降刘备,进而收服荆州诸将,再趁势从曹操手里抢下荆州。这时诸葛亮也在替刘备算计江东:“今操引百万之众,虎踞汉上,江东安得不使人来探听虚实?若有人到此,亮借一帆风,直至江东,凭三寸不烂之舌,说南北两军互相吞并。若南军胜,共诛曹操以取荆州之地;若北军胜,则我趁势以取江南可也。”(同上)双方针锋相对。然而,一会面鲁肃就“敢问操军约有几何”,急躁之情溢于言表,外交上已落下风。当他听诸葛亮诈言欲投吴巨,竟又“坚请”其共赴江左。于此,毛宗冈批道“孔明劝玄德结孙权为援,鲁肃一劝孙权结玄德为援,所见略同。而孔明巧处,不用我求人,骗使人来求我”。“妙在孔明并不挑拨鲁肃,鲁肃先来勾搭孔明,又孔明之巧也。”[4]第一次交锋,孙吴外交优势严重丧失。鲁肃虽有战略眼光,但在具体操作中也的确是个“忠厚长者”。过江后,诸葛亮对孙权说,“操军破,必北还,则荆吴之势强,而鼎足之形成矣”。(《演义》第四十三回)对孙吴的招纳刘备集团并不就范,而是要攻破曹操,然后自领荆州,分庭抗礼。孙权非但没有异议,却早言:“孤不能以全吴之地受制于人。吾即绝矣。非刘豫州莫与当曹操者;然豫州新败之后,安能抗此难乎?”(同上)“是孔明激怒孙权而使孙权求助于玄德也。”[5]前者是鲁肃求诸葛亮,此时是孙权求刘备。第二回合的失利使孙权外交优势丧失殆尽,与既定方针也有所偏离。第三回合是诸葛亮与周瑜对荆州的政治争夺,即所谓的“智激周瑜”(见《演义》第四十四回)周瑜原想以“降者易安”为幌子,迫使刘备求他抗曹,届时即成为孙权解救刘备,刘备依附孙权,刘备也就没法苦争荆州了。哪知诸葛亮居然“支持”他,又大讲曹操之能,说降曹可“保妻子”、“全富贵”,巧妙的给周瑜安上了“懦弱”和“卖主求荣”两条罪名。但这只能使鲁肃“大怒”,周瑜却不动声色。诸葛亮还又说,曹操南下乃是觊觎二乔,并引曹植《铜雀台赋》为证。小乔是周瑜之妻,大乔是周瑜的义嫂和内姊,更是江东“国母”。若为苟且偷生把她们献出或是降后被强占过去,何等耻辱?“保妻子”已不可能,“全富贵”更不见得,周瑜的戏再也演不下去了。其实周瑜何尝不知是诸葛亮借此挤兑他:曹操出身宦官家庭,由洛阳北部尉作到当朝宰相,其志其能,岂止于佳人美姬?再看《铜雀台赋》,共计二十二句,“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是第七句。那么周瑜为什么要等孔明诵毕整篇才知“老贼欺吾太甚”呢?他性情极烈,往往触怒即发,今天何以如此反常?一定是在思忖对策,但最后依然不得不按诸葛亮的指引去“勃然大怒”。所谓“适来所言,故相试耳”不过是周瑜牵强附会的为自己打圆场。他刚刚表现得对江东六郡八十一州的得失浑不在意,此时又因“揽‘二乔’”而与曹操“势不两立”,岂不自损形象?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鲁肃在这场斗争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文本开篇曾说“鲁肃与周瑜最厚”,这“厚”字自然包括政治上的相契。周瑜方至,鲁肃便向周瑜“将前项事细述一番”,周瑜说“子敬休忧”——是赞成抗曹——又道,“瑜自有主张”——有些莫名其妙——并要“速请孔明来相见”。周瑜尚未见到孙权、张昭诸江左高层,就急着找诸葛亮这个外人,似乎不通。鲁肃却不带任何疑问的“上马去了”。瑜亮一会面,鲁肃就问:“今曹操驱众南侵,和与战二策,主公不能决,一听于将军。将军之意若何?”他们不是谈过了吗?是想得到周瑜明确答复吗?但为什么要当着外人的面问呢?很明显,是要挑起话题,也是在告诉诸葛亮东吴战与和“一听于将军”。当周瑜说“战则必败,降则易安”,诸葛亮并无反应,鲁肃却“愕然”的与周瑜争辩。诸葛亮说曹操“善用兵”、“莫敢当”,还说降曹可“保妻子”、“全富贵”,周瑜浑不在意,居然又是鲁肃“大怒”。看到周瑜被“激”的大呼“吾与老贼势不两立!”,鲁肃竟又不见应有的惊喜。他对周瑜所言的“瑜自有主张”、“今可速请孔明来相见”乃是心领神会的,他的“愕然”、“大怒”不过是在演戏。他积极促成瑜亮交锋,并与周瑜大演“双簧”,可惜较诸葛亮仍技逊一筹。三场外交斗争皆是刘备集团胜利,至此孙权、鲁肃承认了刘备的平等地位,并与之建立了联盟关系。
[##]
孙刘正式结盟后,周瑜为绝后患屡屡设计,欲除去诸葛亮甚至刘备。对此,鲁肃的立场则有些摇摆不定。杀诸葛,灭刘备,孙权无力独抗强曹。可刘备属刘表部将,又声称以叔辅侄,日后占领荆州绝非师出无名。从名爵上看,孙权为乌程侯,拜将军,兼领会稽太守,掌管江东六郡;刘备乃大汉皇叔、宜城亭侯,授左将军,除豫州牧,屯兵夏口,实是一大劲敌。倘若荆州当真落入刘备之手,那形势便又回到了先前局面——鼎足之势。刘备不比刘表,将寡兵微,半生羁旅,哪个诸侯愿意其强大起来并与自己平起平坐?何况与之有直接利益冲突的江东集团?更重要的是,刘表乃一庸才,且子嗣臣僚不睦,只要“北方多务”就可“竟长江所极而据守之”;刘备则世之枭雄,仁名播于海内,百姓拥护,上下一体,又有诸葛为之策划,更兼关、张、赵云皆勇烈之士,潜力颇大。后来曹操也曾叹曰,“刘备,人中之龙也,生平未尝得水。今得荆州是困龙入海矣”。(《演义》第五十六回)如果孙权北向“不可卒除”之曹操,西邻“困龙入海”之刘备,非但难图天下,即便江东大本营也将受到扼息之迫。刘备既不肯归顺,又值新败,正是吞并的大好时机。然而若无刘备之力,恐怕孙吴难度此劫。所以当周瑜对付诸葛亮时,鲁肃拿不定主意,几乎任凭周瑜措置。而惺惺相惜的意气心理又常占上风,往往能在关键时候帮诸葛亮一把,从而保证了联盟的持续。当然,鲁肃此时只是把联刘作为抗曹的权宜之计,其目的还是并刘。直到赤壁战后,刘备稳踞荆州,他才认识到,曹操虽败犹强于孙吴,且刘备已不易吞并,因而不得不把联刘确定为长远方针。但是这些想法得不到孙权尤其是踌躇满志又大权在握的周瑜的支持。于是,他三次奔波于孙刘之间,讨还荆州。诸葛亮未出草庐即为刘备制定了“先取荆州后取川”的战略,荆州怎能讨回?鲁肃讷于言辞,疏于诡计,又找不到合适的解决办法,只得去扮演着两面不讨好的角色,后来他讨荆州也有几分敷衍了。他往返周旋,旨在维护联盟,底线是孙刘不起刀兵,因为他已意识到了另一种危险:“方今与曹操相持,尚未分成败;主公现攻合淝不下。不争自家相互吞并,倘曹兵乘虚而来,其势危矣。况刘玄德旧曾与曹操相厚,若逼得紧急,献了城池,一同攻打东吴,如之奈何?”(《演义》第五十二回)随着矛盾的不断激化,讨荆州出现了高潮——“关云长单刀赴会”(见《演义》第六十六回),此时形势有了新的变化。孙权先后与曹军于合淝、濡须两次接战,总体未分高下,而于濡须战役中占到上风,这表明江东具备独立对北军作战的实力。再则,刘备已得西川,却拒还荆州,暗使关羽,对吴态度恶劣,孙权震怒,孙刘联盟名存实亡。关羽的因素也很重要,他直接否认“借”荆州:“荆州本大汉疆土,岂得妄以尺寸与人?”(同上)况且他武艺超群,深谙兵法,又夙恨孙吴,雄踞汉上,犹如猛虎,随时可能伤人,不若早除免为其害。此外,鲁肃因为亲口将荆州“借”与刘备,至今难以收回,自觉愧对孙权,总想给孙权一个交代。于是,他决定设宴赚关羽。但一时疏忽,还是让关羽走脱。这是鲁肃生前最后一次大的外交活动,在文本中他再也没有正面出场。鲁肃担任都督期间,从未领导过对外军事活动,其真正成绩在于保证孙刘之间的和平,为鼎足三分创造了必要条件。
鲁肃大智若愚,是孙吴集团战略方针的制定者,有人把他与诸葛亮、曹操、司马懿并列为四大战略家[6],这是比较客观的。与另外三人相比,鲁肃又有明显的不足。首先他缺少军事指挥才能,江东的诸多具体战斗他几乎都未亲身参加,即便是赤壁一战也只是与阚泽等文人守寨而已,“伏路把关饶子敬”不过是诸葛亮的一句戏言;政治上他更是徒具战略眼光,疏于战术,以致其方针在执行中往往因缺少行之有效的方法而陷入窘境;另外,他忠厚木讷,不比诸葛亮等人灵活机变、俐齿灵牙,外交上吃尽苦头。但是,鲁肃出色的完成了江东集团所赋予他的任务。这就涉及到了鲁肃的文本意义,主要有三点。第一,鲁肃形象使得曹、刘、孙三家在人才实力上保持平衡,这是三分的关键。曹操自不必说,堪称前后数十个军阀人才最盛者。刘备兼有“两人得一,可安天下”的卧龙、凤雏,关、张、赵、马、黄、魏皆乃世之名将。孙权集团周瑜、吕蒙堪当统帅,甘宁、太史慈可充勇士,但若与曹、刘争雄上尚需一个目光长远的战略家,那就是鲁肃。惟有如此,才不致为曹、刘所吞,又为适时称帝奠定了基础。第二,缔造和维护孙刘联盟。鲁肃不但是江东唯一能与诸葛亮主持联盟的人,还要应对孙权、周瑜、诸葛亮、关羽等人的种种有损联盟的行为,并独自解决由此产生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第三,鲁肃的活动客观上促成了天下三分。三分的关键在于荆州,刘备无家可归时他把荆州“借”与刘备,维护孙刘之间的和平,给刘备提供了积蓄力量的机会;鲁肃死后孙权才袭下荆州,但刘备已经稳坐东西二川。孙权也因适时得到荆州,保证了自己的实力。此时,三家实力接近均衡。也就是说,鲁肃去世的时间对三分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影响。然而,随着鲁肃的去世,孙刘联盟也正式结束。即便蜀建兴元年后孙刘第二次结盟,双方也只是停留在邻里和睦的限度上。在伐魏问题上,司马懿就曾一针见血的指出,“孔明尝思报?亭之仇,非不欲吞吴也,只恐中原乘虚击彼,故暂与东吴结盟。陆逊亦知其意,故假作兴兵之势以应之,实是坐观成败耳。(《演义》第九十八回)陆逊也说,“既与同盟,不得不从。今却虚作起兵之势,遥与西蜀为应。待孔明攻魏急,吾可乘虚取中原也”。(同上)而诸葛亮北伐,即“檄李严等守川口,以拒东吴”(《演义》第九十一回)。军阀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注 释:
[1]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版,24页。
[2]特定的历史语境不同于现实历史的语境,是指文本呈现出的时空语境。
[3]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修订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版,40页。
[4]唐风、冬梅编《胡适鲁迅等解读〈三国演义〉》,辽海出版社,2002年第1版,87页。
[5]同上。
[6]张锦池《中国四大古典小说论稿》,华艺出版社,1993年第2版,56页。
王伟,山东鲁东大学汉语言文学院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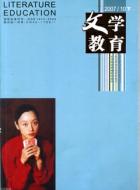
- 南国的风 / 黎林果
- 自由的声音 / 周永清
- 短文两篇 / 牟 茜
- 随笔两则 / 方 成
- 仰望东坡 / 阮 晓
- 寻找回家的路 / 周 霁
- 307的可爱男生 / 徐宏寿
- 逝去的经典 / 黄荣婕
- 中职生及其说话能力训练 / 曾淑梅
- 学生评教是建设和谐校园的平衡点 / 孙翠琴
- 语文教学应加强学生口语训练 / 魏少良
- 教师要学会跟学生解围 / 朱忠金
- 要科学合理引导学生爱美 / 薛 忠
- 语文教师的望闻问切 / 刘加洪
- 把课堂还给学生 / 陈 英
- 多媒体在语文教学中的作用 / 沈心华
- 语感实践训练方法谈 / 段水清
- 让学生尽情享受课堂教学 / 谢继合
- 多媒体使语文教学更有魅力 / 李素艳
- 做一个风情万种的语文教师 / 顾 明
- 散谈小学阶段的古诗文教学 / 刁太祥
- 用创新的教法使学生乐学 / 卢 艳
- 语文课堂教学与想象力开发 / 张志远
- 散文艺术的虚与实例析 / 卢红英
- 培养良好习惯是素质教育的归宿 / 王凌红
- 母语教育的重要性 / 杜晓平
- 也说全民阅读的重要性 / 曾松林
- 对师生交流中教师语言的深层思考 / 罗修武
- 初中语文教师应具备的素质与能力 / 李志勇
- 回头再看教育上的经典语录 / 王业贞
- 口头作文的特点及训练方法 / 王保升
- 校园启事的写作亟需规范化 / 张兆华
- 短篇小说创作技巧例说 / 徐继雄
- 优化写作教学策略琐议 / 袁和平 袁娇萍
- 获得作文高分的几种技法 / 宗永臣
- 如何让作文闪耀出奇异的光彩 / 余建琼 余 澜
- 文章拟题的几个技巧 / 吕 兵
- 下水作文的操作要领 / 杲先旺
- 高考作文如何审题 / 余逊云
- 作文创新思维四法 / 汪群英
- 写作教学要注重的几个环节 / 文联霞
- 论新课程背景下小学生活作文教学 / 顾三川
- 写作前应拟定假想读者 / 崔铁梅
- 作文写作应重视三个积累 / 孙承先
- 如何激发学生写作的自主意识 / 张桂芳
- 作文评语要体现出三性 / 李爱华
- 自读课文阅读方法谈 / 彭治顺
- 课外阅读的指导艺术 / 娄新强
- 阅读教学要回归文本 / 黄 莺 朱 洁
- 阅读教学切忌盲人摸象 / 张振芳 张春梅
- 语文阅读教学的两面性 / 薛锦东
- 运用自主性阅读策略教好文言文 / 汪远忠
- 关于阅读教学的实践分析 / 睢瑞丹
- 阅读教学要切实运用探究性学习 / 李文洲
- 新课程视野下的阅读对话 / 翁进迁
- 关于阅读教学的优化问题 / 付友艳
- 《祝福》里“我”的作用 / 赵永刚
- 《沁园春·长沙》所体现出的革命情怀 / 伍运凤
- 解读鲁迅名作《明天》 / 高志明
- 《子夜》中主人公吴荪甫的两面性 / 毛三红
- 阮海彪《死是容易的》的生命意识 / 杨红祥 蒋代炳
- 《孔乙己》思想意蕴探析 / 蔡兴明
- 《日出》女主人公人物形象分析 / 张 杨
- 评梁实秋《雅舍小品》 / 檀 辉
- 《许三观卖血记》的音乐之声 / 祁雪婷
- 解读《百年孤独》的魔幻密码 / 耿红岩
- 在设疑解疑中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 周超勇 尹 琴
- 语文课堂教学中的探究性学习 / 刘泽红
- 语文自主教学可操作性探讨 / 汤小梅
- 文学审美鉴赏下的语文教学 / 檀华武 王章材
- 语言教学中的学习者因素探析 / 黄 惠 夏 楠
- 以《诗经》为视角看中学生的气质培养 / 赵向玲
- 语文综合性学习的实践与体会 / 樊雅娟
- 古汉语教学中的认知能力与创新精神培养 / 张桂梅
- 大学生的语文教育与人文教育 / 刘维娅
- 用爱与知识搭建和谐的教学桥梁 / 徐向莉
- 语文教学更应注重师生交往的民主性 / 江玲燕
- 文学课堂中如何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 / 许开松
- 语文课堂教学中的三美 / 李 娜
- 《羚羊木雕》教学实录 / 徐敏红
- 《大自然的启示》教学设计简案及实录 / 陈雨佳
- 说明文教学应多作些逻辑分析 / 孙国璋
- 在交流语境中有效实施话题教学 / 吴箫箫
- 汉语中女性称谓歧视现象分析 / 朱礼金
-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 / 毛素文
- 古希腊与罗马神话之比较 / 王昆仑 彭小梅
- 论《长恨歌》的主题思想 / 周国强
- 《红楼梦》五十八至六十一回的艺术特色 / 焦福生
- 博尔赫斯与残雪创作方法比较 / 姚莹?
- 李煜后期词的感伤色彩 / 赵晶晶
- 古代文人的秋愁情结 / 沈 鸿
- 沈从文的人文关怀及其对当下的影响 / 崔宗超
- 从纯文本角度看《三国演义》中鲁肃形象 / 王 伟
- 散文真情艺术美谫论 / 滕永文
- 论晓苏面对“底层”的两副面孔 / 李 勇
- 男色如花 / 吴珍艳
- 无非图个闲闲的散步 / 方英文
- 贪嘴 / 薛尔康
- 鲁迅是个有魅力的人 / 吴 俊
- 艺术:使人成为人 / 乔东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