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07年第10期
ID: 92925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07年第10期
ID: 92925
沈从文的人文关怀及其对当下的影响
◇ 崔宗超
人类生存现状探悉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逐渐步入了信息社会,经济的多元发展和人们接受信息的多元化使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生活节奏逐渐加快,生存压力越来越大。从尼采的“上帝死了”到后现代主义的“人也已死了”无不揭示了当今人类的生存状态,海德格尔也警示我们“存在的被遗忘”已困扰着现代社会的每一个人。的确,现代人在宣称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奋斗的同时,却逐渐忽视了生活质量的真正提高。
也许是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给予我们越来越多的诱惑和压力,处于现代信息社会的人们时时刻刻都被一种紧迫感追逼着,好朋友相邀一块儿喝茶谈心,一家人坐下来吃顿团圆饭,都几乎成了一种奢侈。人们见面只是一个形式化的微笑或问候,左邻右舍之间冷若冰霜,防盗门一锁割断了所有沟通的机会。这些都市里的官员、商人、知识分子们每天想的做的多是如何工作、挣钱,金钱和名誉成了多数人生活的主宰。很多人在觥筹交错中变换着“友谊”,在歌舞摇摆中达成种种交易,他们总是想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人生价值”,来显示自身的过人之处,满足虚荣的成就感。即便是被沈从文讴歌的“乡下人”也少了原有的质朴和善良。“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灭了。”[1]
人越来越陷入生命的不自由、非本真状态,我们认为当今人们的生存状态是一种被异化的状态。人们的日常生活所展开的世界,是一个充满了欢乐与悲伤的“沉沦”世界,在这个“非本真”的世界里,人处于一种“非本真”的存在状态。
那么,什么是人的本真存在呢?人类精神的家园和自然健康的状态究竟是什么呢?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个美丽、自然、淳朴而又充满了人性美、人情美的湘西世界。
生命之真 人性之美
沈从文的作品处处洋溢着对生命的热忱和关怀,他曾不无悲凉地说:“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2]沈从文是孤独的、感伤的。然而这种孤独和感伤正体现了他对人性和生命的极大热情和挚爱,他以一个艺术家的眼光,通过对生命的思考和探索来叩问中国民族命运和民族品德的问题,力图用自己的笔,唤起人们对生命意义的明悟,探索社会前进的动力,使人们获得前进的信心和勇气。
生命的顽强和坚韧在他的作品中反复呈现,他对生命的关爱,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怀也通过他那优美细腻的语言,美丽迷人的风景,淳朴强悍的风俗民情呈现在我们面前。比如《长河》中为滕长顺守橘子园的水手满满,作为一个独身的老人,以其顽强的生命力量抗拒着外部世界袭来的苦难,展现着生命主体的坚韧,虽然这种抗拒收效甚微,但抗争本身就显示出了生命由自在状态上升到自为状态的努力。这种对生命的美的原生态的展示对当今信息社会人们毫无价值的忙碌和盲目的追求有很大启发。
人性是他创作的起点和归宿。正像他自己所说:“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漠上或水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做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种庙供奉的是‘人性’。”[3]
《边城》就是作者所营造的众多“希腊小庙”中最“精致、结实、匀称”的一座,他用人性描绘了一个瑰丽而温馨的“边城”世界,这里人性皆真、皆善、皆美,翠翠和二老之间朦胧而纯洁的爱,老船夫对孙女的爱,祖孙二人对所有渡船人的爱,杨马兵对翠翠母亲的爱……在这片神奇、静谧的土地上演绎得和谐而美好。当今社会人们欲望的多元膨胀,人性逐渐脱离自然的状态而开始扭曲发展,因而精神的疗救就显得尤为重要。沈从文在写完《边城》时曾说:“《边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热情,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了,应当还保留些本质在年轻人的血里和梦里,相宜的环境中即可重新燃起年轻人的自尊和自信心。”[4]作者希望“乡下人”这些美好品行能够被重视并保存下来,组合到现代的精神内核中,以实现民族的振兴。随着沈从文作品接受群体的扩大及研究热潮的到来,其作品中的人文关怀和精神内核对当今社会人们被异化的生存状态起着越来越大的矫正作用,读者在细心品味时便可感受到其向真、向善、向美的力量和充满温情的人文关怀。
悲悯情愫 终极关怀
笔者认为,悲悯情怀即个体对生命苦难的体察、博爱和疗救。对生命苦难的体察是悲悯情怀的感知基础,博爱是悲悯情怀的德性前提,疗救是悲悯情怀的本质追求。沈从文的作品在表现自然、和谐,体验温情、关怀的同时也通过一系列“残缺”和“死亡”来寄托他对人们的悲悯情愫和终极关怀。
在《边城》中,作者描绘了一个温暖的充满爱的理想“边城”世界,然而背后呈现的却是一个残缺的家庭以及一个又一个突如其来的死亡和逃离。翠翠的爹娘早已去世,留下她和祖父相依为命,接着天保和祖父相继死去,爱她的二老傩送也生死未卜。小说中翠翠的命运与母亲命运的相似构成了宿命的循环,作者对命运不可知的沉重情绪和人物的悲悯情怀强烈地表现了出来。
同样跟翠翠命运相似的少女三三,她们都纯洁、善良,但却难以逃脱心上人生死未卜或病死的结局,一个守着渡船,一个守着碾房,在河水流逝中,在碾盘的转动中,重演着她们的母亲的经历。然而不同的是,在屋前榆蜡树篱笆间,萧萧还抱了自己新生的毛毛,看大儿子娶童养媳,同十年前自己抱丈夫一个样子……一种宿命的循环与轮回让人颤抖!翠翠总爱胡思乱想:“我要坐船下桃源县过洞庭湖,让爷爷满城打锣支叫我,点了灯笼火把去找我。”[5]三三也是这样,“每次到溪边玩。听母亲喊:‘三三不回来了,三三永远也不回来了。’为什么不回来,不回来又到什么地方去落脚,三三并不曾认真打量过。”[6]简单、质朴的语言中所蕴藏的悲悯情绪实在让人感动。
“城市”与“乡村”两种文明对峙中的人文情思
沈从文始终以一个“乡下人”的姿态供奉着人性的“希腊小庙”,以原始朴素的人性美傲视都市“文明”下自私、虚伪、堕落的丑陋灵魂,他的许多作品都体现了城市与乡村两种文明对峙的人文情思,希冀在那充满原始意味的人性美与虚伪的现代文明的对照中,以尚未被熏染的原始民风,对上流社会道德风气进行对抗,用下层人民血液中保留的健康、纯朴、充满活力的道德元素拯救为历史压扁、扭曲了的人的灵魂。
《边城》和《绅士的太太》是这两种文明对峙的典型。《边城》如一首爱的田园牧歌,彰显着灵魂的纯洁无瑕,没有任何利益渣滓。翠翠和二老的爱情是真挚的,热烈而纯真的,他们为爱而爱,没有任何私欲。二老没有因为团总女儿有颇值钱的碾坊而倾心。翠翠在二老为她唱歌传情时,在梦中快乐的浮起来,“飞窜悬崖半腰”去摘那象征爱情的“虎耳草”,即便二老因大哥的死而离开了,翠翠也没有任何怨言,痴痴地等待爱人的归来。爷爷更是为了孙女的幸福,不顾自己受冷落和委屈。人性在这儿是那么的美丽动人。而在《绅士的太太》中,人性泯灭的昏天暗地,高贵的身份透露着十足的虚伪,华丽的衣着掩盖不住灵魂的肮脏,人们时刻想着欺人,防着被欺。即便是夫妻,也是同床异梦,各怀鬼胎,毫无真情可言。金钱成了生命的主宰,人性沦丧了,道德堕落了。
在两部作品的对照中,我们分明感到作家远离了都市的繁华与喧闹,在那永恒的生命长河边搭起自己人性的“希腊小庙”,独守着“边城”这一方净土,默默地耕耘,抵御着外来的污秽,用自己的至善至真感悟着庞杂的社会。这虽然不乏原始的陈旧,但它的质朴、纯洁,给人一种回归自然的温暖与安适。
[##]
沈从文总是有意识地描写城乡的差别,用乡村生活的平静优美自然,与都市生活的烦嚣丑恶异化进行比较,用乡下人的勇敢,诚实,映照城里“上等人”的怯懦、虚伪。
这种对照也集中体现于沈从文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刻画,大城市文明下她们身居都市,享受着豪华、舒适的物质生活,用打牌与看戏打发日子的同时,也倍受精神空虚的强烈折磨。于是,“绅士的太太”每天闲来无事,以打牌为业,后与一同僚的大公子生下一子;“或人的太太”不甘寂寞背着丈夫会情人,终心有愧坦白之,两人后合好如初。“我们在大城市里住,遇到的人有学问,有知识,有礼貌,有地位,不知怎么的,总好像这人缺少了成为一个人的东西。真正缺少了些什么又说不出。但看看这些人(水手)就明白城里人实实在在缺少了点人的味儿了。”[7]
沈从文笔下的都市女性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以太太们为代表,她们要么是娼妓出身,要么是做了太太,样子变成娼妓,每日过着空虚,堕落的生活;第二种是以女学生为代表的青年一代的女性,她们要么作白日梦,要么跑步、打球,做一些为普通人猜想不到的事情,壮大如水牛,争强好胜,追求功利,犹如男子,在社会中丢失了自己的本真,无怪乎作者在称赞阮陵的女人时,说:“女权运动者在中国二十年来的运动,到如今在社会上露面时,还是得用‘夫人’名义来号召,并不以为可羞,而且大家都集中在大都市,过着一种腐败的生活,比较起这种女劳动者把流汗和吃饭打成一片的情形,不由得我们不对这种人充满尊敬与同情。”[8]
而一系列农村少女形象贯串着民族品德的发现与重造,这充分体现了他以“乡下人”的身份在两种文明思考中的人文情思,他笔下的农村女孩子总是那样健康,那样纯真,那样聪明,寄托着他的人生感慨和审美理想,脱离不掉生命的“自然状态”。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沈从文的作品中处处体现着其对生命的信仰,对人性的探寻,对人类的博爱和关怀,这些因素对我们处于信息时代的读者无疑是一种浸染,一种熏陶。如果你在生活中迷失了自己,或是在日新月异的竞争面前力不从心、悲观失望,看看沈从文的作品,体味他对人生、对社会、对生活的思考和探寻,感受他的自然、温馨和关爱,你就会在淡泊、宁静的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发现自己的价值。如果你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已变得浮躁、轻飘、伪饰,那么如果能够进入沈从文的这种淳朴情境中静心平思,你就会收获一份踏实,一份坦然!沈从文作品中的生命之真、人性之美、独特的悲悯情怀、“人性”与“文明”的对抗、对“爱”、“美”、“回归自然”的理想“边城”世界的追求,完整地筑就了他的人文关怀意识。他的人文关怀温暖着一颗颗渴求自由平等的心灵,鼓舞着人们追求“合理”“合乎人性”的和谐社会。
沈从文具有诗人的气质,对事物极敏感,因此在乐观、热情中夹杂着些许忧伤,但又不同于悲观,他对人生、对民族从没有放弃希望。正如作者所说的:“横在我们面前许多事都使人痛苦,可是却不用悲观。骤然而来的风雨,说不定会把许多人的高尚理想,卷扫摧残,弄得无踪无迹。然而一个人对于人类前途的热忱,和工作的虔敬态度,是应当永远存在,且必然能给后来者以极大鼓励的!”这位与当代社会人生观、价值观相违背的作家及其作品所包含的人文关怀思想,已被遗忘成一小角隅,但他开启了创建和谐社会的金钥匙,他的人文关怀思想如夜里燃着的一盏孤灯,照亮我们前行的路,洋溢着无限温情。
参考文献:
[1]沈从文:《〈长河〉题记》,《沈从文小说选》(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38、340页
[2]《〈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与香港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44页
[3][4]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文集》第5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1、228页
[5]沈从文:《边城》,《沈从文小说选》(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261页
[6]沈从文:《三三》,《沈从文小说选》(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297页
[7]沈从文:《从文自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8]沈从文:《阮陵的人》,《沈从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
崔宗超,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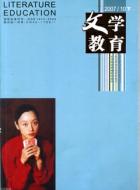
- 南国的风 / 黎林果
- 自由的声音 / 周永清
- 短文两篇 / 牟 茜
- 随笔两则 / 方 成
- 仰望东坡 / 阮 晓
- 寻找回家的路 / 周 霁
- 307的可爱男生 / 徐宏寿
- 逝去的经典 / 黄荣婕
- 中职生及其说话能力训练 / 曾淑梅
- 学生评教是建设和谐校园的平衡点 / 孙翠琴
- 语文教学应加强学生口语训练 / 魏少良
- 教师要学会跟学生解围 / 朱忠金
- 要科学合理引导学生爱美 / 薛 忠
- 语文教师的望闻问切 / 刘加洪
- 把课堂还给学生 / 陈 英
- 多媒体在语文教学中的作用 / 沈心华
- 语感实践训练方法谈 / 段水清
- 让学生尽情享受课堂教学 / 谢继合
- 多媒体使语文教学更有魅力 / 李素艳
- 做一个风情万种的语文教师 / 顾 明
- 散谈小学阶段的古诗文教学 / 刁太祥
- 用创新的教法使学生乐学 / 卢 艳
- 语文课堂教学与想象力开发 / 张志远
- 散文艺术的虚与实例析 / 卢红英
- 培养良好习惯是素质教育的归宿 / 王凌红
- 母语教育的重要性 / 杜晓平
- 也说全民阅读的重要性 / 曾松林
- 对师生交流中教师语言的深层思考 / 罗修武
- 初中语文教师应具备的素质与能力 / 李志勇
- 回头再看教育上的经典语录 / 王业贞
- 口头作文的特点及训练方法 / 王保升
- 校园启事的写作亟需规范化 / 张兆华
- 短篇小说创作技巧例说 / 徐继雄
- 优化写作教学策略琐议 / 袁和平 袁娇萍
- 获得作文高分的几种技法 / 宗永臣
- 如何让作文闪耀出奇异的光彩 / 余建琼 余 澜
- 文章拟题的几个技巧 / 吕 兵
- 下水作文的操作要领 / 杲先旺
- 高考作文如何审题 / 余逊云
- 作文创新思维四法 / 汪群英
- 写作教学要注重的几个环节 / 文联霞
- 论新课程背景下小学生活作文教学 / 顾三川
- 写作前应拟定假想读者 / 崔铁梅
- 作文写作应重视三个积累 / 孙承先
- 如何激发学生写作的自主意识 / 张桂芳
- 作文评语要体现出三性 / 李爱华
- 自读课文阅读方法谈 / 彭治顺
- 课外阅读的指导艺术 / 娄新强
- 阅读教学要回归文本 / 黄 莺 朱 洁
- 阅读教学切忌盲人摸象 / 张振芳 张春梅
- 语文阅读教学的两面性 / 薛锦东
- 运用自主性阅读策略教好文言文 / 汪远忠
- 关于阅读教学的实践分析 / 睢瑞丹
- 阅读教学要切实运用探究性学习 / 李文洲
- 新课程视野下的阅读对话 / 翁进迁
- 关于阅读教学的优化问题 / 付友艳
- 《祝福》里“我”的作用 / 赵永刚
- 《沁园春·长沙》所体现出的革命情怀 / 伍运凤
- 解读鲁迅名作《明天》 / 高志明
- 《子夜》中主人公吴荪甫的两面性 / 毛三红
- 阮海彪《死是容易的》的生命意识 / 杨红祥 蒋代炳
- 《孔乙己》思想意蕴探析 / 蔡兴明
- 《日出》女主人公人物形象分析 / 张 杨
- 评梁实秋《雅舍小品》 / 檀 辉
- 《许三观卖血记》的音乐之声 / 祁雪婷
- 解读《百年孤独》的魔幻密码 / 耿红岩
- 在设疑解疑中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 周超勇 尹 琴
- 语文课堂教学中的探究性学习 / 刘泽红
- 语文自主教学可操作性探讨 / 汤小梅
- 文学审美鉴赏下的语文教学 / 檀华武 王章材
- 语言教学中的学习者因素探析 / 黄 惠 夏 楠
- 以《诗经》为视角看中学生的气质培养 / 赵向玲
- 语文综合性学习的实践与体会 / 樊雅娟
- 古汉语教学中的认知能力与创新精神培养 / 张桂梅
- 大学生的语文教育与人文教育 / 刘维娅
- 用爱与知识搭建和谐的教学桥梁 / 徐向莉
- 语文教学更应注重师生交往的民主性 / 江玲燕
- 文学课堂中如何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 / 许开松
- 语文课堂教学中的三美 / 李 娜
- 《羚羊木雕》教学实录 / 徐敏红
- 《大自然的启示》教学设计简案及实录 / 陈雨佳
- 说明文教学应多作些逻辑分析 / 孙国璋
- 在交流语境中有效实施话题教学 / 吴箫箫
- 汉语中女性称谓歧视现象分析 / 朱礼金
-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 / 毛素文
- 古希腊与罗马神话之比较 / 王昆仑 彭小梅
- 论《长恨歌》的主题思想 / 周国强
- 《红楼梦》五十八至六十一回的艺术特色 / 焦福生
- 博尔赫斯与残雪创作方法比较 / 姚莹?
- 李煜后期词的感伤色彩 / 赵晶晶
- 古代文人的秋愁情结 / 沈 鸿
- 沈从文的人文关怀及其对当下的影响 / 崔宗超
- 从纯文本角度看《三国演义》中鲁肃形象 / 王 伟
- 散文真情艺术美谫论 / 滕永文
- 论晓苏面对“底层”的两副面孔 / 李 勇
- 男色如花 / 吴珍艳
- 无非图个闲闲的散步 / 方英文
- 贪嘴 / 薛尔康
- 鲁迅是个有魅力的人 / 吴 俊
- 艺术:使人成为人 / 乔东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