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建设 2015年第9期
语文建设 2015年第9期
ID: 359212
语文建设 2015年第9期
语文建设 2015年第9期
ID: 359212
当数字和爱恋发生冲突
◇ 杨大忠
伯尔的短篇小说《在桥边》的主题是什么?教参如是说:
小说的主题,在表面上看是爱情,表现爱情对于一个处境堪忧的小人物具有如何强大的精神力量,而深层则是对德国战后重建中偏重物质而缺乏精神关怀这一问题、以及小人物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的精神状态的思考。
这样的概括相当客观准确。我们现在围绕小说的具体内容来看看小说是如何对以上主题进行展开的,同时再探索一下伯尔这篇篇幅相当短小的小说又蕴含着什么其他深刻的社会意义。
一、对战后德国民众的批评
小说的主人公“我”显然是个二战中的伤兵。出于人道主义以及对伤兵的抚恤,政府给“我”安排了一份对于残疾人来说或许是个“美差”的工作:数一座新桥上每天通过的人数。这份工作对于“我”来说当然无比枯燥乏味,而且“我”也不认同自己的工作具有什么实际意义,将其看作“毫无意义的空洞的数目”。
那么,从当时德国政府重建家园的角度看,“我”的工作是否真的没有实际意义呢?先来看看教参的说法:
“新桥”这一意象,是德国战后重建的代表;而对“新桥”所通过的人员、车辆的种种统计、计算,则代表了一种十分不可靠、近乎痴妄和盲目的乐观。
将“新桥”看作德国战后重建的代表,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将通过“新桥”的人员、车辆的统计与计算看作“十分不可靠、近乎痴妄和盲目的乐观”,显然大有问题。
德国人向来以工作严谨、认真、细致和具有前瞻性著称。对一座重建的“新桥”每天通过的人员和车辆数目进行统计,以此为基础总结归纳出一段时间内数目的变化规律,将其看作今后制定发展规划的借鉴,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这正是政府给“我”安排这份工作的原因和初衷。教参则说“我”的工作“代表了一种十分不可靠、近乎痴妄和盲目的乐观”,是对小说中“我”的糊涂想法的推波助澜,明显荒谬不通。
但“我”只是个普通的德国人,是曾经的战士,不是懂经济的知识分子,因而对于自己工作的意义明显认识不足。在“我”看来,工作中统计出来的数目,空洞而无意义,因而采取了敷衍了事、虚假瞒报的态度:
我以此暗自高兴,有时故意少数几个人;当我发起怜悯来时,就送给他们几个。他们的幸福掌握在我的手中。当我恼火时,当我没有抽烟时,我只给一个平均数;当我心情舒畅、精神愉快时,我就用五位数字来表示我的慷慨。
可见从“我”手里出来的数字的多少,完全是由“我”的心情决定的。这里根本没有客观性可言。不仅如此,“我”还自作聪明地对察看统计数目的“他们”报以嘲讽的态度:
当我把我上班的结果报告他们时,他们的脸上放出光彩,数字愈大,他们愈加容光焕发。他们有理由心满意足地上床睡觉去了,因为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走过他们的新桥……
他们算出,今天每分钟有多少人过桥,十年后将有多少人过桥。他们喜欢这个未来完成式,未来完成式是他们的专长——可是,抱歉得很,这一切都是不准确的……
其实,“他们喜欢这个未来完成式,未来完成式是他们的专长”这句在“我”看来充满讽刺意味的话,正体现出德国人工作中的未雨绸缪、事先规划的长远观念与意识,而“我”对这一切却全然无知。
二战中德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被战火摧毁,战后重建家园,人们的热情非常高涨。不能忽视的一个事实是,虽然人们对于能够直接感受到的切切实实的重建成果抱有极高热情,但一些应当运用长远眼光来看、不能直接获得眼前利益的工作与建设,往往不能得到目光短视的人们的充分认识和理解。“我”对统计过桥数字的工作轻视、冷漠、不理解,正是这种社会心态的典型反映。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伯尔短小的《在桥边》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二、对精神关怀的呼唤
由于认识不到工作的意义,加上工作的单调乏味,“我”的生活基本上就是浑浑噩噩的,“我”在消耗着毫无意义的人生,没有信仰和精神寄托。就在苦恼烦躁的时候,冷饮店的姑娘就像一阵清新的风吹进了“我”的心田,她成了“我”在工作中的唯一寄托。
她每天要两次走过桥,一次一分钟。这短短的两分钟,成了“我”生活中最绚烂的亮色:
所有在这个时间内走过的人,我一个也没有数。这两分钟是属于我的,完全属于我一个人的,我不让他们侵占去。
女孩的出现严重干扰了“我”本来就马马虎虎从事的工作。当她出现时,“我”再也不能在她出现的这两分钟内清点过桥的数目了:
当她晚上又从冷饮店里走回来时——这期间我打听到,她在一家冷饮店里工作——,当她在人行道的那一边,在我的不出声音、但又必须数的嘴边走过时,我的心又停止了跳动;当不再看见她时,我才又开始数起来。所有一切有幸在这几分钟内在我朦胧的眼睛前面一列列走过的人,都不会进入统计中去而永垂不朽了,他们全是些男男女女的幽灵,不存在的东西,都不会在统计的未来完成式中一起过桥了。
这两分钟,是“我”追随姑娘的芳踪心随她动的美好时刻。世界在这一刻几乎都凝滞了,所有过桥的其他人都成了我思想中可怜的垂浮物,“我”把他们彻底忽略了,他们都是虚空的,再也不能进入“我”的统计中去。小说虽然没有直接说出“我”随着姑娘的倩影内心激烈地翻腾,但通过对过桥数目的忽略能间接看出“我”对姑娘的如醉如痴。是的,“我”已经不可自拔地爱上这个姑娘了:
这很清楚,我爱她。但是她什么也不知道,我也不愿意让她知道。她不该知道,她用何等可怕的方式把一切计算都推翻了,她应该无忧无虑地、天真无邪地带着她的长长的棕色头发和温柔的脚步走进冷饮店,她应该得到许多小费。我在爱她。这是很清楚的,我在爱她。
这段短短的话语,竟然连用了三个“我爱她”,并且两次强调“这很清楚”,可见爱得沉迷和痴狂;但“我”对这种单相思又是很清醒的,或许是考虑到自身残疾的缘故,“我”并没有付诸行动,可能是顾虑到一旦付诸行动连这珍贵的两分钟都会丧失。只要心爱的人能够无忧无虑、天真无邪地工作并且能得到许多小费,这就够了。
表面上看,伯尔在写爱情对人的影响,表现出爱情对人产生的无比强大的精神力量,教参中说这种精神力量“深层则是对德国战后重建中偏重物质而缺乏精神关怀这一问题、以及小人物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的精神状态的思考”,这自然可备一说;但笔者更愿意做出如下补充:一个战争中的伤兵,在战后重建的过程中,从事着在他看来毫无意义的工作,并且从没有受到爱情的激励转而热爱自己的工作。类似这样的社会现象,不也能引起人们足够的深思吗?
“我”对这位姑娘的迷恋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当饭碗受到了威胁,“他们”对“我”进行检查的时候,“我”不能不端正自己的态度,发疯似的数着桥上过往的人。即便如此,“我”仍旧没有把心爱的姑娘计入统计数字,这也是“我”只比主任统计员少算了一个人的原因。按照“我”的想法,“我一辈子也不会把这样漂亮的女孩子转换到未来完成式中去;我这个心爱的小姑娘不应该被乘、被除、变成空洞的百分比”。“我”对工作的厌倦程度就如同对这位姑娘的爱恋一样,也是无以复加。
由此,联系小说中“我”的身份,引发了我们对一种社会现象的反思:一个因二战而残疾的德国士兵,虽然在战后得到了较为妥善的安置,有了一个饭碗,但他的精神创伤有时却是无法用现实物质弥补的。由于战争造成的生理与体格上的缺陷,面对自己心爱的人,面对可能到来的爱情,他不能也不敢表达出内心炽热的情感,只能把情感深深地压抑在内心。由于对爱情毫不自信,对待工作也只能是应付,丝毫提不起任何兴趣。说到底,这仍旧是一种战后综合征的体现。
战后德国处于极度缺乏粮食、工作岗位和房子等物资的恶劣情况之下,更为可怕的是战争留给人们的心灵创伤,战争虽然结束了,但后续影响无处不在。“我”的经历和遭遇可谓典型。伯尔的《在桥边》描写人的心理活动时,虽然没有直接写出战争的受害者“我”对战争的憎恶之情,但通过叙述“我”对爱情的压抑以及对工作的懈怠,还是间接地表达出战争对德国社会仍旧有着剪不断的不良影响。以“我”为代表的德国民众需要的不仅是工作,还要有精神上的关怀。精神上的创伤得到了疗治,德国就不仅能够从废墟中崛起,而且其人文、思想以及文化也才能得到相应的恢复和繁盛。由此可见,伯尔的《在桥边》是德国民众对精神关怀的呼唤。
三、对社会进步的自信
小说的结尾对“我”来说可谓大欢喜:由于得到了主任统计员“忠实、可靠”的评价,“我”被调去数马车。这样一来,“我”就用不着整天待在桥边了,因为马车一天最多只有二十五辆,只需每半小时在脑中记一次数字就可以了;更令人欣喜的是,“四点到八点时根本不准马车过桥,我可以去散散步或者到冷饮店去走走,可以长久地看她一番,说不定她回家的时候还可以送她一段路呢,我那心爱的、没有计算进去的小姑娘……”。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其中蕴含着永不褪色的进步意义,寄托着作者的理想与期望;哪怕是悲剧,也要通过“花瓶的破碎”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促使人们反思造成悲剧的原因是什么,从而引起社会疗救的希望。伯尔的《在桥边》思想趣味并没有一味地沉沦下去,没有让“我”在生活中彻底失望,而是让“我”重获新生,从中寄托了作者的理想。
在故事的结尾,“我”幻想着“说不定她回家的时候还可以送她一段路呢”,联系之前即使深爱着她“我也不愿意让她知道”,“我”的思想更进了一步。相信有些善良的读者甚至都能联想到“我”与姑娘最终的大团圆的结局。可是教参中却不这样认为:“小说的结尾尽管皆大欢喜,故事却似乎并未因此终止。作品中埋下了的伏笔‘我爱她。但是她什么也不知道,我也不愿意让她知道’,预示着‘数马车’的好运对‘我’也是十分有限的,或许那将是永远的爱恋,或许还将伴随着更多的痛楚。”
以上两种看法都是猜测。笔者以为,伯尔在故事的结局中并没有说到“我”与姑娘最终的结局,这是非常明智的做法。如果安排“我”与姑娘终成眷属的结局,则不仅故事情节转换太快,而且从故事的发展线索与脉络来看,似乎又不太现实,甚至有一种严重失真的感觉;如果继续安排“我”与姑娘始终保持过去的状态——“我”只能远远地观望她,但她不知道——从情节的发展来看则又处于停滞,也就是说,无论“我”的身份、思想如何变化,姑娘始终是水月镜花,“我”和她之间始终处于之前的“原生态”,没有任何变化,这恐怕又是读者难以接受的。
那么,最折中、最完美的做法就是让“我”对姑娘的情感更进一步,由起初的“不愿意让她知道”发展到幻想“说不定她回家的时候还可以送她一段路呢”,但最终的结局是什么,伯尔没有交代,甚至连暗示都没有。读者只能根据自己的意愿做出相应的猜测。见仁见智的事,就交给读者按照各自合理的空间去揣摩吧。
但是,《在桥边》中的“我”毕竟不是单个的个体,而是二战后德国民众的缩影与典型,从“我”的生活状态与精神状态中,我们可以看出伯尔对战后德国社会的评判。伯尔在小说的结尾把“我”的思想境界推进了一步,“我”不再对姑娘保持远观,而是有所幻想。联系之前“我”对生活的无比失望,“我”的幻想不正是一种前进的动力吗?从“我”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出伯尔对整个德国社会寄予的乐观和自信,这正是德国社会不断进步的源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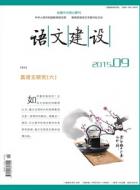
- 卷首 / 佚名
- 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立德树人系列活动 / 陆俭明
- 为什么要遵从汉语特点和规律教语文 / 吴格明
- 抓住汉语的音乐性特点教语文 / 尹逊才
- 从象形特点和构形规律看汉字教学策略 / 王鹏伟
- 基于语篇衔接理论的作文批改 / 荣维东 朱小燕
- 语文的基点 / 蔡建明
- 警惕散文教学千人一面倾向 / 贾龙弟
- 发挥语文独特的育人价值 / 童明辉
- 《春怨》不朽的原因:喜剧性的抒情 / 孙绍振
- 《窦娥冤》的文本缝隙及文学意义 / 田欣欣
- 孟浩然《春晓》诗旨探微 / 卫佳 杨和为
- 当数字和爱恋发生冲突 / 杨大忠
- 中考作文命题须务实 / 胡培兴
- 高考作文期待精彩的记叙文 / 姚赛男
- 穆济波的国文教学研究 / 赵志伟
- 曾国藩的语文教育思想 / 肖建云
- 赛课,不是赛车 / 肖培东
- 文言文教学改革探索 / 姚丹华
- 在历史长河中探寻语法规律 / 崔山佳
- 不会过时的导读法 / 徐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