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建设 2015年第9期
语文建设 2015年第9期
ID: 359203
语文建设 2015年第9期
语文建设 2015年第9期
ID: 359203
抓住汉语的音乐性特点教语文
◇ 尹逊才
语文的基础是语言,这毋庸置疑。《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对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的定义,就是在深刻认识语文和语言的关系基础上做出的正确判断。汉语言是有个性特点的,这也无须争论。语文课程标准强调,“语文课程应特别关注汉语言文字的特点对学生识字写字、阅读、写作、口语交际和思维发展等方面的影响”。课标对语文课程性质的界定及特点提倡,其实已经提出了当下语文课程建设的两大研究课题:汉语特点及其规律的研究,以及如何依据汉语特点和规律进行教学的研究。不过可以想见,这两个课题将是长期的、艰巨的、浩大的学术建设工程。笔者不揣鄙陋,试就汉语的特点之一——音乐性,结合语文教学实践,谈一谈自己的认识。
音乐性是汉语的一个突出特点,这与其独具特色的音节结构及声调系统有关。首先,汉语一字为一个音节,音节时长大体相等。音节一般由声母和韵母两部分组成,其韵母主要以元音为主,而元音是乐音,“因此现代汉语的音节比较别的语言,读起来最为响亮悦耳”[1]。其次,汉语每个音节都有一定的声调。现代汉语普通话有四个声调,即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这四个调类在韵文中则分为平声和仄声两大类,平声包括阴平和阳平,仄声包括上声和去声。这种独特的声调决定了汉语音节自身的平曲抑扬,使由此汇成的语流呈现音响高低变化的状貌。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汉语特别关注自身的语音层面,有时候为了语音上的美感,不惜破坏语法,扭曲词性词义”,“对音乐性的追求这一传统已经积淀为一种民族文化心理,以至在许多时候我们必须从形而上的角度去面对这一语言现象”。[2]因而,教师应当引领学生关注并利用汉语的音乐性特点,提升学生语言的感悟及运用能力。
一、关注平仄,追求唇谐
长期以来,汉语社会集团形成了讲究平仄的传统,好多熟语和习用的成句都是平仄和谐的。如大多数双音节的缩写词,像枚马(枚乘与司马相如)、元白(元稹与白居易)、韦柳(韦应物与柳宗元)等,词序主要考虑的是先平后仄的顺序,并非是按照两个词素所代表的人物的特征排列的;再如,在汉语四音节词中,符合平平仄仄顺序的词最多(占随机抽取的400例中的178例),符合仄平仄仄(最接近平平仄仄的语感)的词占第二位(400例中的77例)[3]。也因为如此,人们才说“张三李四”,不说“李四张三”,说“油盐酱醋”,不说“酱醋油盐”。当然,并列词语的词序排列也有其他的原因,如汉民族尊卑有序的民族心理等(如“父母”“大小”“干群”等),不过平仄关系显然是其主要考虑因素。此外,古典诗歌就更是追求平仄和谐的代表性文字了。这就使人们形成了一种语感,一种心理定式:平仄不协调,读起来拗口,听起来别扭;平仄有规律,读起来上口,听起来舒服熨帖。在语文教学中,教师要关注并充分利用这些内容,让学生多读多体会,从而形成这样的语感和心理定式。古人强调“读书百遍”,不仅仅是“其义自见”,还有确保识记于心、谐于唇吻、永不会误读的功用。
二、关注声韵。追求耳顺
汉语独特的音节结构及音节多义性使得其声韵组合的规律性很强,“构词中的双声、叠韵、叠音,还有词的重叠及押韵、反复、回文、顶针等辞格的运用,都可形成汉语音列上音色上异同相间回环往复的声韵美”[4]。如《再别康桥》,其艳美而凄惘情感,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声韵传递出的,“《再别康桥》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语言的音乐美”[5]。首先,此诗首节三处使用了叠词“轻轻”,末两节三处用了“悄悄”。“轻”和“悄”本身就有柔和的音乐感,加上重叠,就更显细腻缠绵。其次,整首诗大量使用双声叠韵,如艳影、榆荫、清泉、荡漾、青荇、招摇、斑斓、别离等,创造出纷至沓来的音乐效果,充分表现了作者的一腔柔情和不尽思念,渲染出全诗的情感基调。最后,这首诗每一节各自押韵。第一节押[al]韵,第二节押[ang]韵,第三节押[ao],第四节押[ong]韵,第五节押[e]韵,第六节押[lao]韵,第七节重复第一节[al]韵。每节首句不入韵,为次句换韵创造条件。节内隔句押韵,每一节诗内部韵律和谐,读来有音乐美感,而每节换韵又造成一种参差错落感,曲折地表达了诗人内心温馨而凄美、充实而失落的难以言传的复杂情感。第一节和最后一节在用韵上的回环复沓,营构了一种悠远、怅惘、醇厚的氛围,表现了依依惜别的深情,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
重声叠韵词在汉语中占有相当大的数量,声韵的和谐已经成为汉语构词的一条十分重要的规则。“由声韵律构成的内在和谐不仅是中国诗歌追求的效果,同时也已经渗透到了汉语散文的节奏甚至是日常口语的节奏当中。”[6]如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其描写月下荷塘景色的段落就堪称重声叠韵词运用的典范: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叶子底下是脉脉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
在这短短的二百多字中,作者一连使用了九个重声叠韵词(曲曲折折、田田、亭亭、层层、粒粒、星星、缕缕、密密、脉脉),三个重声词(袅娜、仿佛、渺茫),两个叠韵词(零星、宛然)。如此密集地使用重声叠韵词,不能不说是作者为追求音韵上的动听而刻意为之。此外,从这些词的声音上来看,多为齐齿呼、撮口呼的词,这也于声音上造成了一种静谧、欲吐又不能尽意的感觉。在语文教学中,碰到这样的美文,教师除了引领学生通过文字的意义领略作者构筑的物象世界美以外,还应多引领学生通过文字的音韵体味作者构筑的声音氛围美,否则学生只能是欣赏到一个“悄无声息的物象或内心世界”。
三、关注发音,追求意合
汉语的音乐性,不仅表现为悦耳动听,还在于它的发音、节奏与发音者的心情相契合。《文心雕龙》说:“夫音律所始,本于人声者也。声合宫商,肇自血气。”大致意思为,音律原本就是根据人的发声,人的发声符合五音,本于生理机构。也正因为此,“人情的喜怒哀乐,或奋或郁,为求宣情达意,在发音时,借着喉牙(鄂)舌齿唇诸官能姿势的辅助,造成发音气流的委直通塞,表现出清浊、高下、疾徐不齐的声音,赖此声音,以宣达其奋郁惊喜的情绪。所以在五音之中,不同的音质,自能表现不同的情感”[7]。这一点,古诗文中的例子比比皆是。如叶绍翁的《游园不值》,第一句“应怜屐齿印苍苔”,前五个字都属齐齿呼,读起来整句声音纤细,这正与园子静谧的环境氛围相契合;第二句“小扣柴扉久不开”,后面三个字中的“久”,发音时须先齐齿后撮口,颇为费力,后面又紧跟着一个撮口呼的“不”,两字连读就更加蹇阻,这也正是柴门长时间不开,作者寻找春天的迫切心情受阻的心态写照。
现代文学作品中,这种例子也不少,如上面提到的《再别康桥》《荷塘月色》。下面再从中学教材中撷取两个例子。如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句中最后四字,“蜗”“摸”韵母为“o”,“索”韵母含有“o”,按照《文心雕龙》的观点,这当属于“叠韵杂句而必睽”(意思是说两个叠韵字隔杂句中两处,念起来一定别扭),这种声音上的别扭造成的发音不畅,只有与祖国在“历史的隧洞里”艰难前行的意象结合起来,才能予以合理的解释。再如汪曾祺的《葡萄月令》,段落结尾的收字几乎很少用开口呼,而多用合口呼、撮口呼与齐齿呼,如雪、音、里、了、的、绿、住、着、肺、呢、片、须、粒、面、色、子、秃、土等,“这种语音上的安静,实际上正是作者对植物生长状态的自然传达”[8]。
声音与情意的这种契合关系,逐渐积淀就会形成心理定式和语感,比如人们往往觉得细弱的发音比较婉约,宏大的发音比较豪放,像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凄切》和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就是典型的代表。这一点,古人其实早有觉察:“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俞文豹《吹剑录》)[9]可惜后人多本末倒置,误以为这是在谈两位词人的风格差异,从而忽略了它们音响差异的事实。《雨霖铃》这首词,去掉标点共一百零三字,但其中有近四十字是由舌、齿、唇形成的气流较细弱发音的字,如蝉、凄、切、骤、雨、歇、绪、处、舟、催、执、竞、语、噎、去、楚、情、自、清、秋、节、今、酒、醒、此、经、是、辰、景、虚、设、与、说等。这样的语音,“音细而若,细声细调,用之来表现离别时的情形,仿佛听到了情人问的叮咛的声音,看到了离别之际的凄苦,离别后的寂寞与孤凄。齿音的运用在此处简直是再恰当不过了,诗声与诤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了”[10]。《念奴娇》则多用舌、鼻、喉形成的气流较强洪亮发音的字,如大、东、浪、淘、古、风、边、道、国、郎、乱、空、涛、拍、岸、江、山、画、豪、想、公、当、年、谈、故、多、华等。这样的语音,用来展现长江非凡的气象,英雄豪迈的气概,作者豁达的胸怀,亦非常贴切。
以上三点,基本都是笔者在中小学听课时的一些思考和感悟。总体上感觉,大多数教师极其欠缺汉语的音乐性特点相关的知识。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笔者认为不在于教师,主要在于语文课程的建设者。语文课标虽然呼吁“特别注意汉语言文字的特点”,但对其特点和规律却毫无阐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缺失。靠广大一线教师个体自觉地去捕捉汉语言文字的特点和规律,这显然是不应该的,也是不可能的。语文课程建设者理应承担起这一重担。这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不信请看我们的中小学语文教材,很多选文的语言文字并不典范,甚至是有问题的。随便举一例,某版本小学语文教材中有一篇课文叫《鱼游到了纸上》,其第一段第一句话,“我喜欢花港,更喜欢‘泉白如玉’的玉泉”,从音乐性的角度来说,显然不好:两个“玉”字读起来是多么的拗口。按照沈约的说法,这是典型的八病之中的“正纽”,即一句之中隔字同音。这种音韵的不协调,从全文来看,显然不是刻意为之,而是因为作者缺乏必要的汉语音乐性感觉。这样的文章,无论是教材编者还是广大一线教师,都还把它当作典范的文章让学生学习,可想而知我们对汉语音乐性的感觉已经迟钝到什么程度了。这一点,古代的蒙学教材要比我们做得好,如“三百千”,可称作利用汉语音乐性特点的典范。我们应该好好研究,好好学习才是。
最后声明一点:汉语的音乐性特点肯定不止本文谈的这些,但囿于笔者的学识只能谈到这个程度,其中还尚且存有不妥之处。如能引起应有的注意,那自当是不胜欣喜。
参考文献
[1]郑福田,汉语新诗的形式美与现代汉语的特点[J],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91(5)
[2][6]泓峻,汉语音乐性潜质及其在现代文学语言中的失落[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6(3)
[3]贺国伟,汉语词语的产生与定型[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219~227
[4]吴洁敏,论汉语节奏规律[M],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1)
[5]尤敏,读徐志摩的《再别康桥》[J],名作欣赏,1980(1)
[7]黄永武,中国诗学:设计篇[M],北京:新世纪出版社,2012:144
[8]汪政,何平,解放阅读——文学批评与语文教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1:174
[9]转引自唐圭璋等,唐宋词鉴赏辞典:唐、五代、北宋[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322
[10]吴果恒,“形式美”在高中古诗文教学中的效用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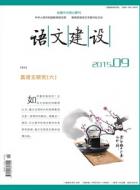
- 卷首 / 佚名
- 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立德树人系列活动 / 陆俭明
- 为什么要遵从汉语特点和规律教语文 / 吴格明
- 抓住汉语的音乐性特点教语文 / 尹逊才
- 从象形特点和构形规律看汉字教学策略 / 王鹏伟
- 基于语篇衔接理论的作文批改 / 荣维东 朱小燕
- 语文的基点 / 蔡建明
- 警惕散文教学千人一面倾向 / 贾龙弟
- 发挥语文独特的育人价值 / 童明辉
- 《春怨》不朽的原因:喜剧性的抒情 / 孙绍振
- 《窦娥冤》的文本缝隙及文学意义 / 田欣欣
- 孟浩然《春晓》诗旨探微 / 卫佳 杨和为
- 当数字和爱恋发生冲突 / 杨大忠
- 中考作文命题须务实 / 胡培兴
- 高考作文期待精彩的记叙文 / 姚赛男
- 穆济波的国文教学研究 / 赵志伟
- 曾国藩的语文教育思想 / 肖建云
- 赛课,不是赛车 / 肖培东
- 文言文教学改革探索 / 姚丹华
- 在历史长河中探寻语法规律 / 崔山佳
- 不会过时的导读法 / 徐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