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1年第12期
ID: 136762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1年第12期
ID: 136762
写《旧书》欲得高分:关键在于“有思想”
◇ 覃明才
2011年湖北省高考作文题目一“露脸”,就引起了比以往更广泛的反响。大都认为,“旧书”审题难度不大,考生都有话可说,不容易跑题,但有“限制”,获得高分很难。作家杨标称“‘旧书’是为有文学修养的学生准备的”,暗指得高分难。不少媒体纷纷推出“试水高考作文”,似乎也是想印证这种看法(不排除炒作)。6月8日,搜狐网问卷有38.11%的网友认为“难”;大楚网调查认为“比较难、太宽泛、难以下笔”的有54.41%;还有某网站调查有67.1%的考生觉得“偏难”。有专家分析,可能是“文体不限”、“考生求稳”等因素遏制了考生的发挥,也可能是考生平时不注重观察和积累所致。很多考生却认为,每天和书打交道,却忽略了读书入心。我倒是觉得,写《旧书》要想取得高分,关键还是在于“有思想”。
一、究竟怎样才叫做“有思想”
武汉作者高池在点评“旧书”写作时说:很多考生平时很有思想,敢想敢说,考试时却非常谨慎小心,力求观点、文体、语言四平八稳,为分数而考试,久而久之,丧失了宝贵的的想象力。这里把“有思想”归为“敢想敢说”,我觉得这不叫“有思想”。“海城的博客”中点评“旧书”写作时说:高考作文有思想,是一类文的重要标志。没有思想的作文,如同没有灵魂的躯壳。所以,要用思想来作文。我又觉得这种说法没有区别出“思想”与“有思想”。
“思想”在现在的“公共话语”系统中多是指理念的,逻辑的,他人性的,群性的,意识形态化的;“有思想”则是指“思想”物化而形成优秀作品的科学体系。在文字写作、文学创作、高考作文三者上,属于生活实录的文字写作,仅存在于“思想”的表层;文学创作必须回答“写什么、怎么写、写作的目的是什么、能够表达什么内容、能够传递什么信息、有无价值”等问题,必须表现出“骨子里”的东西;高考作文则是一种特殊的文字写作(有的也算是文学创作),具有较大的规定性与突出的技巧性,从构思到写作,必须有独到的意识形态作用于“套路或章法”,不然,就不可能写出获取高分(满分)的作文。
《考纲》规定,高考作文的“基础等级”是“符合题意,感情真挚、思想健康、结构完整”,“发展等级”是“透过现象深入本质,材料丰富、论据充实、形象丰满、意境深远,善于运用修辞手法,构思新巧,有个性色彩”。也就是说,《旧书》要达到这些要求才能获取高分(满分)。而从阅卷组那里获悉,绝大部分考生选择了议论文体裁,而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思想苍白、情感虚伪、内容空洞、语言花哨,文风浮靡的“滥情作文”(因此没有得到高分),说明考生作文仅存在于“思想”的表层;也有不少考生选择了记叙文或散文体裁,很有一批作文以“旧书”喻人,或用情动人,或以事寓理,具有真情实感(所以得到了高分甚至是满分),说明有些考生作文很善于表现出“骨子里”的东西。
这样看来,考场中写《旧书》,考生若是将《考纲》中的条条框框撕裂了又融入到自己心底的“旧书”中去,这就叫做“有思想”。
二、“有思想”至少包含哪些要素
(一)作文必须赋予“旧书”本质意义及其之上的深刻寓意。
湖北名师甘德炎说“旧书”的命题目标是“能力立意、素质立意”。我觉得这与我提出的“有思想”的观点如出一辙;而考生要想达到命题目标,至关重要的一环在于写作之前首先必须明确“旧书”本质意义及其之上的深刻寓意。
湖北语文特级教师夏纯德认为,从字面上来看,“旧书”可理解为四重意义:(1)破旧的书;(2)时间;(3)古书;(4)人生的不同经历及各个阶段。女作家姜昕则认为“旧书”有两种:从书籍的创作年代,是指先人们撰写的书,包括甲骨文或刻在竹简、木片,写在丝织品上面的文章,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等;从书籍的新旧程度,是指被看旧的书,大都被博物馆保存、私人传承着。我觉得,上述说法有道理,但作为考生,要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积累,分别从本意和比喻意两个角度对“旧书”加以准确的理解,就可能在拿高分上更有把握一些。
从本意的角度,“旧书”泛指一切过往的书籍,可以指经典著作,包括古代文化经典著作、近现代哲人领袖的经典著述,如《论语》、中国古代四大名著、毛泽东《矛盾论》等哲学著作与《沁园春·雪》等诗词;也可以指一般的书籍,如使用过的教科书。具体可指:(1)品相旧的书籍,如残破的书籍;(2)出版时间久远的书籍,如古书;(3)过去的书信。
从比喻意义的角度,“旧书”可以喻指一切人、事、物。具体可以喻指:(1)或德高望众、或满腹经纶、或饱经风霜、或功勋卓著、或孝道为先、或平凡中而凸显伟大的前辈、师长;(2)厚重的历史或人生的经历,如中国古代文明史、中国近代屈辱史、中国共产党90年的风雨历程、中国抗日战争史、改革开放的30年经验教训、中国乒坛兴盛奋斗史、所在学校发展史、考生“负重”的童年;(3)书籍以外的物象,如已逝的高山大川、名胜古迹、老屋、母校,曾经玩耍过的沙滩、草坪、沟坎,记忆深处的莺歌燕舞、花开花落。
(二)作文必须从“旧书”中释放出考生相应的思想高度。
“旧书”是一个具象,考生把握准了其某种意义,还必须站在一定的高度看问题,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写作文要从大处着眼。这样,作文的内容才有深度,也才可能获得高分(满分),否则就完全不一样。近来网站、报刊上发表过不少《旧书》,我是看好诗人、《汉诗》杂志执行主编张执浩应约写的《旧书》(载2011年6月8日《楚天都市报》),文章写的事情很小:22年前的夏天买了本《刀锋》,却有着生活的维度、人生的厚度与思想的深度:一本平常的书却带给他的是“那份感动”——“一个迷惘的手无寸铁的青年,在陌生的人群或寂静的山谷中走动,因为手里有一本这样的书,便自觉无所畏惧起来”。我也欣赏武汉“13岁少女作家”操雨辰的《旧书》(中国教育在线),她能写“一年级教科书”“虽然书页早已泛黄,我却看见了童年的笑,童年的泪……”已属不易,但愿她在高考考场会写好她在文中提到的《论语》。我与身边的几名考生交流,不免有点感伤,有几个写《论语》、《三重门》、《天龙八部》,却不能对《论语》的内容、价值,对韩寒、金庸有深刻地认识和理解,所以只能停留在“爱不释手”、“永远珍藏着”的层面;有几个论述某一旧书的文化价值或历史价值或思想价值,可他们的着眼点不是呼唤文化经典的回归,或在旧书中寻求理想信念的重构,或在旧书中吸取科学文化营养的再塑,所以写出的《旧书》寡而无味。
具体地说,如写“旧书”——“教科书”,若是站在人文关怀的高度看问题,就可以让人彻悟“教科书”对塑造美好心灵、健全人格的重要意义;如写“我珍藏着很多旧书”,若是站在道德、情操、法律的高度看问题,就可以从中考量出考生的价值取向;如写“童年是一部旧书”,若是站在辩证法的高度看问题,就可以引发读者对素质教育的辩证思考;如写“奶奶是一部旧书”,若是站在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高度看问题,就可以闪烁出“奶奶”那一代人勤劳朴实的人性光辉;如写“老屋是一部旧书”,若是站在民族、国家、社会、人民的高度看问题,就可以由“老屋”折射出民族的辛酸与顽强;如写“学校是一部旧书”,若是站在人类文明、文化的高度看问题,就可以让人品读出现代学校教育所蕴含的文化精髓;如写“家乡的小河是一部旧书”,若是站在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高度看问题,就可以让人深刻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尊重规律与急功近利的关系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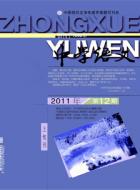
- 建设真正开放的语文学科 / 李国栋
- 漫谈语文教师的角色意识 / 李新生
- 语文教师的语文教育史知识探析 / 袁彬
- 学情探测:从评价方式到教学模式 / 胡根林
- 深度赏析 广角生发 / 席欣圣
- 功夫在诗外 / 梅晴
- 论“朱子读书法”对阅读教学的启示 / 佃礼杰
- 刍议说明文教学内容的确定 / 陈俊江
- 对话课堂:让生命在快乐中拔节 / 李利中
- 作文命题指导思想及基本要求管见 / 萧兴国
- 线性不足:作文常见的危险区域 / 崔国明
- “经验之塔”理论对作文情境教学策略的启示 / 晓棣
- 欣赏中领略写作奥义 / 黄希鹏
- 读出课文内容的“集合” / 余映潮
- 语文人本教育的开拓者 / 张晨
- 解读翠翠内心世界的N重悲凉 / 何莉
- “排” / 张旋
- 自我救赎的漫漫长途 / 惠军明
- “教”与“学”思维的差异与转化 / 章国华
- 借用多媒体 促进学生的探究能力 / 董旭午
- 人文性:语文教学的灵魂 / 张朝昌
- 高效的阅读,快乐的分享 / 刘娟
- 《学会描写景物》教学实录 / 胡礼仁
- 微博中的符号体态语 / 赵军
- 人究竟是不是东西 / 郝文华
- 析“考碗族” / 丁瑞华
- 对毛词《贺新郎》的五大辨正 / 肖科
- 写《旧书》欲得高分:关键在于“有思想” / 覃明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