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0年第10期
ID: 136356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0年第10期
ID: 136356
精神和言语共生
◇ 蓝 枫
入夜,记者徜徉在新安中学校园,仰望星空,思绪绵绵。2000年的一场语文教育大讨论,标志着我国中学语文教学改革进入了在反思中求发展的新时期。如今十年过去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所做过的、所想过的,到今天只不过是老问题翻新,语文课改仍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大面积地提高语文教学质量仍不能成为现实。然而,就在这十年间,吴泓突破应试教育的藩篱,完成了从单篇、单元注入式到专题研究性学习的转变。他的学生无论是在知识的积累、能力的培养方面,还是在思想的磨砺、精神的陶冶,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育等方面,都有全面的提高和根本性的改变,实现了语文教学改革难点的最大突破。那么,这位素质教育的践行者秉持着怎样的语文教育理念?他是怎样踏上“温暖而充满挑战的旅程”,让学生“不怕考试而又超越考试”的呢?前不久,吴泓老师在他的工作室接受了记者的专访,为我们解开了谜团。
蓝枫:2000年您来深圳,在单篇、单元教学方面已取得不俗的成绩,是什么原因让您有这么大的勇气去改变自己呢?
吴泓:之所以要改变,还得从我来深圳的学校说起。2000年,我来到了新安中学。这所学校地处特区二线关外,是一所区直属的二类学校。既是关外,就是农村或者城乡结合部;既是二类学校,生源状况当然就不会很好。当时校长要求我“特级教师教出的成绩就应该有特级的样”,而我也带着自认为炉火纯青的课文处理“技术”在学校刮起了阵阵旋风。学生写道:“老师的讲课犹如表演,问题设置精妙,语言幽默更是令人佩服之至……典型的‘文学知识融于实践生活’的合成级人物——酷毙了!”省一级学校评估组组长、督学孙寿年先生在听完我的课后总结说:“学校有很好的老师,特级教师就有四位,吴泓老师现在才38岁,年轻的专家啊!在省内也是极少的。”然而,一年下来,学生的学习现状不容乐观:50%的学生书写零乱,20%的学生字迹难辨,85%的学生阅读量少,阅读面窄,思维缺乏深度和广度,写作内容肤浅苍白、空洞无物。可以说是要说不能说,要写写不好。不仅我所在的学校如此,我曾多次参与过市、区高中语文统考改卷工作,看到学生的答卷很不理想,特别是阅读理解不得要领,作文东拼西凑,逻辑混乱。而这种情况在我们这类学校以至往下三、四类学校可谓比比皆是。改卷老师告诉我:“往上的一类学校也绝不少见。” 这样残酷的现实让我不得不思考:这究竟是为什么?老师讲得这么精彩,怎么就换不来学生的精彩?哪里出问题了?我当时就颇有危机意识。
蓝枫:有了危机意识并不意味着就有正确的方向。听说您是在做完第一个专题的时候才确定采用这种语文学习方式的?
吴泓:我和我的学生做的第一个专题是“读蒋廷黼《中国近代史》”。这本书篇幅很短,只有5万多字,可蒋先生却写得磅礴大气又深入浅出,刚好可以和历史教科书作对应来学习。没想到,短短一个月时间里,学生竟完完全全沉浸在一种自主自愿的、自由愉悦的、充满着思维挑战性和开放性的学习过程中;更让人惊讶的是,几乎所有的学生在阅读、思考和表达上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而这种在课堂上“读一本书”的学习过程和学习方式是我和我的学生以前从未有过的。这期间,学生不仅没有做那些为应试而编写的练习题,就是连正式的语文课本也暂时搁置一旁。一个月下来,当一本散发着油墨香味的专题学习习作集《家园》送到我和我的学生手中时,那份惊喜、激动、成就感、自豪感……无以言表。而在这之前,我的这些高中学生也只是会写“我的同桌”“我的老师”“我的父亲和母亲”“我们班上的一件有趣(或有意义)的事”的孩子,怎么一夜之间竟有天壤之别了呢?学生说:“原先的语文学习,我们是上课听讲,下课做题;而现在的语文学习,我们是自主阅读,自己提问,自我思考,自由表达。没想到我们居然还有思想!”一句话点醒了梦中人。原来,我一直在做着“上课不停地讲,下课让学生不停地做题”的这种蠢事。由此,我也开始思考“学生的思想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语文应该走怎样的路”这样的一些问题。
学生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我想起我在深圳结识的两类朋友:一类是炒股迷,这类朋友说起股票来眉飞色舞,滔滔不绝,一说就是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另一类是足球迷,这类朋友说起足球如数家珍,什么足球的纵向发展、横向比较,足球明星的家庭趣事、风流轶事等等。当时我就在想,这些人怎么能说得如此头头是道、有板有眼?原来是他们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既有纵向,也有横向;既有整体,也有局部;既有宏观,也有微观。这不就是当时倡导的“研究性学习”吗?说能说得如此头头是道,想必写也不成问题。而高中语文,能不能通过专题研究性学习来引导学生学会运用语言和表达思想呢?新课程标准不正在提倡“读整本书”吗?就这样,2001年,我毅然迈出了我教学生涯的新的一步——“高中语文专题研究性学习”;2003年,又完善了“网络环境下的高中语文专题研究性学习”,而这一“迈”就是十年。
蓝枫:28个专题都有哪些?您为什么要选这些经典之作来进行语文学习?
吴泓:第一组是中国古代9个专题:读《诗经》,读《楚辞》,读《世说新语》,读陶潜,读李白与杜甫,读韩愈,读苏轼,读王安石,读《红楼梦》。第二组是中国近现代9个专题:读蒋廷黼的《中国近代史》,读《呐喊》《彷徨》,读《雷雨》,读穆旦,读《边城》,读张爱玲,读《呼兰河传》,读《围城》,读中国当代诗歌。第三组是外国10个专题:读莎士比亚,读雨果,读托尔斯泰,读海明威,读《百年孤独》,读卡夫卡,读伍尔芙,读《等待戈多》,读加缪,读里尔克。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专题学习的内容也有适当地调整或替换。
我们知道,一部作品之所以能成为经典,是因为它们经过了历史的选择,具有典范性,具有永恒意义和普适价值。真正的经典可以丰富人类的心灵,给人以灵魂。阅读经典,学生不仅能获得广博的知识,还能提高他们各方面的语文能力,更能塑造他们的人格,确立其情感、态度、价值观。试想一下,一个经常在阅读和沉思中与古今哲人、思想家倾心对话的人,与一个只读明星轶闻和凶杀故事的人,两者思想空间和精神境界固然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而今天的学校语文教育,就应该摈弃那些非经典之作的语文学习,摈弃那些拦腰斩断、割裂经典、急功近利的“应试阅读”;还要拒绝那些快餐式的所谓的“浅阅读”“悦读”对学生的侵蚀。因为“读”什么决定了你“想”什么,“想”什么决定你“说”或者“写”什么;“说”“写”的质量取决于你“阅读”的质量,“说”“写”的高度取决于你“思想”的深度。学校的语文教育要有档次、要雅,要培养学生有不同于流俗的贵族气。
蓝枫:有人说您的课改体现了一种现代的语文教育观,您能说明一下吗?
吴泓:传统语言学、语文教学强调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后来又提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其实,载体和工具没什么本质的不同。现代语言学、语文教学则认为,语言是主体进入世界的方式,也是世界向人类展示其本质的方式,所以语言是一种本体论性质的媒介。从传统到现代,人类对语言的认识在不断深化。我过去是信奉语言工具论的,搞课改以后对语言的本体性有了更多的体认。教学实践告诉我:言、意是一体的,就像一个钱币的两面,不能分离,“精神和言语共生”就是从这里来的;在不同的学段,进入“共生”的切入点不同,达到“共生”的途径和方式也相异。如果说从小学到初中阶段,是从“言语”这一面切入,从言语技能的学习去领悟作品的思想、精神、意蕴,培育学生积极健康的情感态度,即侧重于先技后道、由技悟道,更多地体现出语言的工具性;那么,高中阶段的语文学习,则要从“精神”这一方面切入,把价值观的锻造、精神家园的构建放在首位,必须先道(精神、思想层面)后技(技巧、技能层面),由道悟技,以道御技,即由“形而上”至“形而下”,更多地体现出语言的本体性。这就决定了高中语文教学应当有不同于小学、初中的方式,也可以说,单篇、单元注入式的学习可能不大适合高中生了。要在短时间内使只有较少直接人生体验的高中学生渐进为一个有思考、有思想、有见地、有创意的人,就必须选择“专题研究性学习”。“专题”为的是集中,“研究”为的是深入。当一个学生聚焦某个“专题”(或一个人物,或一部著作,或一段历史,或某个话题),材料不断积累,认识逐步加深,体验点点汇聚,思想层层积淀,分解化合,发酵蒸馏,就会凝结成一种对社会、对人生独一无二的个体认识,即精神、思想层面的东西;就会去陈言而留真意,除粗秽而存精气,就能做到由博返约,厚积薄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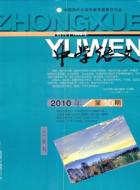
- 语文综合性学习研究:走向课程的视阈 / 申宣成
-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 文 勇 孙绍振
- 语文味:阅读教学内容的价值取向 / 贺克春
- 无一爱字,字字含情 / 吴晓湖
- 于语言细微处见语文精神 / 夏峥嵘
- 《小狗包弟》教学实录及教学反思 / 程 希
- 试论阅读教学内容的重构 / 冯齐林
- 精神和言语共生 / 蓝 枫
- 语文教学的大小传统 / 舒兴庆
- 散文阅读教学“四径” / 杨邦俊
- 在整合优化中突出重围 / 田 水
- 还高中语文课堂以琅琅书声 / 张 瑜
- 坦荡闲雅,春风拂面 / 袁汉杰
- 想象阅读教学研究 / 张春阳
- 陌上,繁花如锦 / 卢亚萍
- 教材中的“陌生化”对提高写作水平的暗示 / 温逸林
- 关于课堂教学中有效问题的思考 / 林汇波
- 文学作品的细读教学例说 / 潘文富
- 教材本无言 处处有良师 / 周 钰
- 书法艺术的鉴赏 / 万玉兰
- 对新课程语文教材价值的审视 / 茹红忠
- 作文评价:何日走出历史的迷雾 / 王俊杰
- “虽然”和“即使”有何异同? / 卢卓群
- 高考作文写作中的材料调动问题 / 赵文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