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0年第10期
ID: 136351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0年第10期
ID: 136351
无一爱字,字字含情
◇ 吴晓湖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
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
——《邶风·静女》
听惯了“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狼爱上羊呀,爱得疯狂”等当代爱情歌曲,回头读一读古人写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这样深情直白而厚重的爱情诗作,你会有怎样的感受?你再读一下《诗经》中的《邶风·静女》,相信你定会为这首诗作的爱情刻画之美而拍案叫绝。
一、“露”与“藏”的含蓄美
诗歌创作重委婉、含蓄,忌直白、外露。诗作的含蓄美,就如司空图在《诗品》中所说:“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清人刘大櫆也曾说:“或句上有句,或句下有句,或句中有句,或句外有句,说出者少,不说出者多。”(《论文偶记》)含蓄的诗当在最少的诗句中包含更为广阔的艺术画面、更为丰富的思想内容,给读者以最大的想象空间和最深厚的情感熏陶,让读者通过各自的主观感受去领会诗人未及言明的更深更广的内涵,以求“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就是一种“藏”与“露”的艺术。
《邶风·静女》就很好地体现了这样的艺术,诗作名为“静女”,女主人公却一直没有正面出场,对她的描写刻画都是借助男主人公“我”的口吻叙述、回忆展现的。诗作“露”与“藏”有机的结合让读者借助直接出场的“我”的口吻一点一点地想象未出场的女主人公的形象、性格,最后组合形成一个完整的形象。诗作第一章这样描写女主人公“静女其姝”,“静”是娴静,“姝”是美好,这一“静”一“姝”把“我”眼中那个娴静、美丽的姑娘用一种平静而又骄傲自豪的口气介绍了出来。“俟我于城隅”写“我”正美美地想到姑娘在城墙角落等着与“我”相见,读者还可以设想“我”还在激动不已地设想自己和姑娘约会的美好场景。正在男主人公兴奋不已之时,情节来了一个大转弯——“爱而不见,搔首踟蹰”,多情的姑娘却一直没有出现,一个“爱”(通“薆”,躲藏)字给我们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想象空间:那个美丽、多情的姑娘其实早早地就来到了约会地点,等待的恋人却迟迟没有出现,调皮可爱的姑娘为了惩罚恋人玩了一个小花招,悄悄地躲了起来,让恋人也着急着急,这才出现了诗作中“搔首踟蹰”的生动情景;因为有了姑娘的“爱而不见”,“我”的着急无奈全都暴露无遗,“我”越是抓耳挠腮,焦急难耐,躲在某个角落里的姑娘就越是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为数不多的诗句生动地描绘出姑娘调皮、天真、活泼的性格,刻画出一个美丽聪明、调皮天真、充满浪漫情趣的多情少女形象,让读者在想象之后顿生如临其境、如在目前之感。
余光中曾说过:“一切创作之中,最耐读的恐怕是诗了。……奇怪的是,诗最短,应该一览无余,却时常一览不尽。”《邶风·静女》就是这样一首让人百读不厌、含蓄深情的优秀诗作,可谓情到深处诗含蓄。诗作没有让姑娘直接出现,而是通过小伙子的视角再现姑娘的美、姑娘的情,通过小伙子的几个片断性的叙述、回忆,让读者尽情想象姑娘的形象、姑娘的深情,于是经过读者的想象加工——一个天真可爱、美丽调皮、情深似海的热恋中的少女形象就清晰地出现在我们眼前了。《邶风·静女》写出来的与未写出来的正好体现了一种“露”与“藏”的艺术,这种“露”与“藏”的艺术如海面的冰山,其真正的威力并不在露出水面的“八分之一”,而在那藏在水下的“八分之七”。
二、一个视角,两种深情
爱情是一个动人的话题,更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因此爱情常成为诗人的吟诵对象。诗人笔下有“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比翼双飞情;有“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的生死离别情;也有“我如果爱你,绝不学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的独立平等情……但如果读者把这些诗作与《邶风·静女》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其他诗作基本上是一个视角(或男性视角或女性视角)写一种感情(单一地表现男性对女性的感情或女性对男性的感情)。如《诗经·卫风·氓》以第一人称“我”的口吻、视角叙述了自己“恋爱——婚变——决绝”的整个人生经历。通过“我”被遗弃的遭遇,单向地为读者塑造了一个勤劳、温柔、坚强的妇女对“他”——“氓”婚前的深情、婚变后的委屈、最后的坚定,而极少写到爱情中的另一半“氓”对女主人公“我”的深厚感情。
《邶风·静女》是一首与众不同的诗作,是一首描写理想爱情的优秀诗作。它用男主人公的自叙角度通过回忆体现爱人对“我”的深情,又用这一角度更为直接地体现“我”对爱人的真情,它写的不是一个人的爱情,不是单相思也不是有主次之别的爱情,而是两个人的爱情,是两个相爱的青年男女情深意浓的两厢情愿的深情叙述,可谓“一个视角,两种深情”。
三、浪漫真诚的爱情模式
《邶风·静女》以男性“我”的口吻叙述了相恋男女你情我愿的双向的美好的爱情片断,借这一片断展现了男女双方高度和谐的美好的爱情模式,演绎出了一幕幕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爱情故事。
每个人都渴望拥有一份真正属于自己的美好浪漫的爱情,但并不是所有相爱的人都懂得爱的艺术;两情相悦是让人向往的,但并不是所有的爱情故事都充满喜悦和幸福。中国古代文学中有很多爱情诗作,但这些爱情故事大多以愁为基调,常是喜剧上场、悲剧结束。“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不为超度,只为途中与你相见”、“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些经典爱情诗句不都是充满了忧伤和遗憾吗?这些诗句让读者阅读之后不由为这些有情人最终不能成眷属的悲剧一洒同情之泪,在同情之余也不免让人发出这样的感叹和遗憾:爱情是那么的令人向往,相爱的人儿应当是幸福的,可为什么文学作品中的爱情却常见悲剧极少喜剧,充满了沉重的气息?
《邶风·静女》则不然,诗中这对平凡的男女却给后世的人们演绎了一个充满快乐与活力的爱情情景。“窥一斑可见全豹”,诗人只写了三个爱情片断,但通过“三”个小小片断,读者可以想象出更多的片断和瞬间。第一章写男主人公焦急的等待,而这一次的等待可以推想过去无数次的相约——等待——相见的情节。因为有过去约会中女孩的天真调皮的“爱而不见”,才有今日“我”“搔首踟蹰”之时的自我安慰——不是姑娘没来,而是躲藏起来,那只好耐心地等她出现。二、三章描写也是后世诗作中很少读到的相见的甜蜜情景。为何“我”会这样焦急万分却又痴情等待?原来这姑娘是一个懂爱会爱并能大胆表达爱意的多情女子、理想伴侣。传统的爱情往往是男性处于主动地位,女性处于被动地位。《邶风·静女》中则不然,在整首诗中看到的更多的是姑娘大胆的爱情表达,“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中“俟”“爱”字告诉我们提出约会并确定约会地点而且早早地来到约会地点的不是憨厚老实的男性——“我”,而是可爱的静女;“贻我彤管”“美人之贻”中的“贻”字告诉赠送爱情信物的也不是应该采取主动的男性,而是那个深情调皮的静女。在“我”面前,静女永远是先表达深情和浪漫的那一个,而“我”一直是默默接受静女的深情和浪漫的,明明心中已似烈火,表现出来的却永远是静静的湖水。《邶风·静女》无愁无悲,只有等待的紧急和回忆的甜蜜,是一首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爱情诗作,让你感受到满眼的青春气息、满心的清新淡雅,更主要的是它描写了一个极富生命力和朝气的幸福爱情故事。
什么样的爱情最迷人?两情相悦,朝朝暮暮相见,时时刻刻相恋。也许这浓浓的情多年后也会淡去最初的浓烈,但有过辉煌的一瞬,未来平淡又有何怨?因为不能大胆地爱,黛玉才会躲在人后终日以泪洗面;因为不能朝朝暮暮在一起,秦观才会发出“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爱情誓言;因为可以大胆地爱也可以时刻相见,静女才会这样任性率直地表达自己的爱。
姑娘美丽、娴静、调皮、浪漫,充满爱的想象,小伙子真诚、纯朴,是值得依赖的伴侣。这是一对真诚相爱的、懂得爱的真谛的、会表达爱的男女,这不正是恋爱中的人所希望的理想的爱情模式吗?
《邶风·静女》通过第一人称叙述方式记叙了相恋男女的一次还未真正见面的约会。读了这首诗,我们无不为之打动,为男主人公的一往情深,为女孩子的天真浪漫,为相恋双方的深情。这是一首难得的同时表现相恋男女深情的叙事爱情诗作,从头到尾没有出现一个爱字,但事事关情,字字含情。情到深处诗含蓄,可谓“无一爱字,字字含情”。
什么是真正的爱情?什么是正确的爱情观?怎样的诗作才是既含蓄又美好的?《邶风·静女》给了我们最好的答复,美好的爱情不仅在诗作中,更在生活中。“情到深处诗含蓄”的例子给了我们表达爱情的最好典范。我们怎么有理由不去争取属于自己的美好的真诚浪漫的爱情呢?我们又怎能有理由不写出更好的诗作呢?
[作者通联:云南昭通第一中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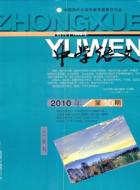
- 语文综合性学习研究:走向课程的视阈 / 申宣成
-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 文 勇 孙绍振
- 语文味:阅读教学内容的价值取向 / 贺克春
- 无一爱字,字字含情 / 吴晓湖
- 于语言细微处见语文精神 / 夏峥嵘
- 《小狗包弟》教学实录及教学反思 / 程 希
- 试论阅读教学内容的重构 / 冯齐林
- 精神和言语共生 / 蓝 枫
- 语文教学的大小传统 / 舒兴庆
- 散文阅读教学“四径” / 杨邦俊
- 在整合优化中突出重围 / 田 水
- 还高中语文课堂以琅琅书声 / 张 瑜
- 坦荡闲雅,春风拂面 / 袁汉杰
- 想象阅读教学研究 / 张春阳
- 陌上,繁花如锦 / 卢亚萍
- 教材中的“陌生化”对提高写作水平的暗示 / 温逸林
- 关于课堂教学中有效问题的思考 / 林汇波
- 文学作品的细读教学例说 / 潘文富
- 教材本无言 处处有良师 / 周 钰
- 书法艺术的鉴赏 / 万玉兰
- 对新课程语文教材价值的审视 / 茹红忠
- 作文评价:何日走出历史的迷雾 / 王俊杰
- “虽然”和“即使”有何异同? / 卢卓群
- 高考作文写作中的材料调动问题 / 赵文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