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9年第9期
ID: 135913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9年第9期
ID: 135913
60年语文课改的范式转型:从指令到创生
◇ 潘 涌
一、60年语文课程范式转型的历史视角
建国以来,60年语文课程改革的历史就是课程范式演绎的过程。“范式”(paradigm)这一特定概念,为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S·Kuhn)于20世纪60年代所创。在这个古希腊已有的词中,库恩赋予了其科学哲学的新含义:“在一定时期内,可以向研究者共同体提供的典范性问题及解决方法的普遍公认的科学业绩。”①库恩否认了科学知识和理论的积累式发展这个旧命题,确立了科学理论的进步是通过具有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的新旧范式之间的转换来实现这个颇有创意的革命性科学观;换言之,库恩认为科学理论新旧范式之间存在着一种使得两者不可沟通、交流的断裂,并不存在逻辑上的共同准则(即具有不可通约性)。库恩“范式论”的理论贡献在于其不仅给予了连续积累的旧科学进步观以致命打击,而且给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发展带来了新的视角和启发。后来,作为哲学用语的“范式”演化为被人们公认的某个时代、某个专业领域内的范例或体系。观照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所发生的具有实质内容的革命性变化,当是显著对立的新旧范式之间的划时代转换。教育学领域内亦复如是。真正具有深度和创意的课程变革,往往就是新旧课程范式之间的革命性转换。
所谓课程范式(curriculum paradigm),是指一个课程共同体所普遍拥有的课程哲学观与相应的诸种具体课程主张的统一②。两者既相互独立,又有内在联系。居于上位的课程哲学观规定了课程共同体的独特的价值取向,而具体课程主张则是在课程哲学观指导下对课程问题的具体认识,它决定了课程价值目标实现的可能性。换言之,在某个课程共同体中,各门学科课程尽管内容不同,但都建立在同一教育哲学观和课程观基础上,从课程目标制定、课程计划实施直至课程终端评价,都具有若干共性的特征,从而适应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思潮。
汉语文课程就是这种转型中的课程范式之样本。自1949年建国以来,语文课改的实质就是课程范式转型,即从儿童经验型转向教师指令型、再转向师生创生型。每一种课程范式的诞生,都以一定的教育哲学思想为背景,并有自己的实践主张,对课堂教学创造力产生了或禁锢或解放的显著影响。教学创造力是贯穿学校所有教育活动的主题词,能否激发师生作为课堂主体的教学创造力,是衡量某种课程范式是否具有历史合理性和进步性的基本标准。正如在经济领域内,物质生产创造力能否获得充分解放是判断生产关系是否具有历史合理性和进步性的主要尺度。教学创造力不简单等同于灌输和复制教学中的知识承传。教学创造力基于知识承传,但超越了在某种文明形态中作周而复始平面化循环的知识承传。质言之,每个生命体内都蕴含了求知激情、灵性智慧乃至创新思维等诸多重要的精神能量,教学创造力就表现为师生的这些精神能量在开放性教学互动中的最大释放,特别是学习者在心灵的倾听和对话中自主探索、独立判断和自由想象的活跃强度与效度。
二、语文指令型课程的形成和后果
自1949年以来,伴随着整个社会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巨大变革,包括语文在内的课程范式亦发生了新的转折。建国之初,毛泽东、刘少奇已确定了文化与教育建设向苏联学习的基本方针。在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中,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明确指出:要“以老解放区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③。这一方针明确限定了包括语文课程在内的整个教育改革的价值取向,突出了语文课程与教学发展以前苏联为借鉴对象的基本特点。此后,随着中国政治形势的极端左倾化,语文课程与教学自然难免被“苏化”的时代思潮所裹挟而逐渐丧失了自我。
作为前苏联所谓社会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代表,凯洛夫教育学说在整个50年代对中国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教育部师范教育司的提议下,凯洛夫著的《教育学》和凯洛夫主编、赞可夫等协助编辑的《教育学》相继翻译出版,恰好填补了中国教育学的理论真空。凯洛夫本人来华讲演,对中国教育的改造产生了更直接的影响。在宏观方面,他过度强调教育的阶级性,认为教育是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而用来巩固自身阶级统治的一种工具,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目的就是培养共产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的积极建设者。具体到教学实践中,他要求“在学校的一切教学工作中,绝对保证教师的领导作用”,视教师为“教学中最重要的、有决定作用的因素”,教师单向的“讲授起主导作用”;关于教科书,认为它是学生“知识的主要源泉之一”,教科书内容只能选择确定不移、颠扑不破的原理,而不是在科学上尚无定论或正在争论的问题④。凯洛夫没有深究学生的年龄特征、学习特点及其在教学中的作用,忽视学生作为独立生命的主体性功能,当然也排斥学生的综合实践活动。视教科书为神圣不可挪移的法典,在客观上必然导致教师在备课和教学中作为独立主体的缺席,导致其沦为教科书的附属者。这种以凯洛夫教育学说为理论指导的指令型课程范式,是前苏联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和一统化的计划经济的必然产物,在全面苏化的时代背景下直接导致中国“三中心” (以课堂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以教科书为中心)课程实施模式的产生,又在掺和了极左政治思潮及应试教育的负面因素后,逐渐演化为以国家教育意志为本位的中国式指令型课程范式。
语文指令型课程就是其中的一个样本,它以所谓确凿无疑的义理和语文知识系列为中心,以全预制、全封闭和全垄断的教学目标为基本价值取向,逐渐使学生变为语修逻文和字词句篇的被动接受者。这与“五四”以后所形成的现代语文课程“生本位”的主导价值取向是完全相悖的。
(一)十七年时期。“苏化”最盛期给新中国语文教育造成了直接的负面影响,表现在课堂教学方法、教科书编撰和作文指导方面均是目中无“人”、唯上是从。凯洛夫所谓的“五个环节”教学法,即组织教学→复习旧课(检查作业)→讲授新课→巩固新课→布置作业,已成为课堂教学的基本方法而被不加甄别地“滥用”。这种苛刻的教学流程,导致语文教师按部就班、“入套”授课,教师个体成为共性化教程的“依附者”而很难有独特的教学创造;学生个体更无勃发的灵性思维产生之可能。在对《红领巾》进行教学讨论后,苏联专家普希金教授所主张的“谈话法”、“人物形象分析法”又被普遍套用,使语文课迅速演化为一成不变的“分析课”,原本浑然一体、生气横溢的课文被“肢解”成时代背景、作家生平、人物性格、艺术手法等几大块,成为后来遭人诟病的大陆语文的“经典教法”。它漠视特定的学习群体和个体,使教学双方总是处在一种机械的教学平面上消磨生命,充其量再加上“此知识点”和“彼知识点”,久而久之,深深禁锢了个性化的教学创造力。这个时期,语文教科书的编撰也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裹挟下日益失去自身的学科特征,特别是日益偏离学生的生活世界和真实的阅读需求。从最早由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改编出版的统一的《初中语文》和《高中语文》开始,选文标准因服从于思想教育的新使命而益趋政治化,到“大跃进”时期尤甚。古今中外历经岁月筛选而葆有生命力的优质文学作品被排斥,剩下来的基本是政治文本或准政治文本。更兼“教学参考”与“阅读提示”的导向性规范,即使是偶有“人民性”的作品《石壕史》、《卖炭翁》之类获幸编入教科书,也往往遭受价值异化的厄运。当优质文本陷入浮泛空洞的庸俗说教时,其言语形式的审美价值就荡然无存了,语文课就异化成思想教育课了。此时,作文教学也被卷入了“浮夸风”。如盲目地配合凸显为社会生活之主题的政治运动,完全不尊重学生的童心、童趣和童真,使作文教学陷入“假大空”的恶性循环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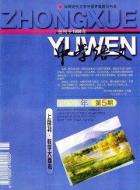
- 本 / 徐曼宇
- 古诗词阅读的深度开掘 / 苗金德
- 60年语文课改的范式转型:从指令到创生 / 潘 涌
- 感受性阅读的价值寻获 / 徐余忠
- 文学定篇的组合类型(二) / 胡根林
- 《故都的秋》主旨争鸣及教学处理 / 袁 菊
- 孔子的教育之道(八) / 韦志成
- 浅论写作中真实与虚构的和谐统一 / 冯齐林
- 迷茫后的坚守——对语文高考“怎么考”的思考 / 孙凤丽 乐中保
- 作文激励性评价例谈 / 王礼平
- 语文课堂陶冶式教学的探索 / 夏 磊 曹明海
- 对当前作文教学的思考 / 张志祥
- 《变形记》的四种残忍 / 梅其涛
- “桃花源”里寻“美” / 侯麟耀
- 合宜的教学内容是一堂好课的最低标准 / 孙 娴
- 教会学生作点辩证分析 / 李 平
- 大浪淘沙 / 赵晓非
- 《逍遥游》:放飞心灵的自由(上) / 何永生
- 要扎扎实实上好“梳理探究”课 / 郭振海
- 李商隐《锦瑟》诗旨为“陈情说”探析(上) / 曹兴戈
- 高中语文选修课“同质化”现象及对其的反思 / 李园香
- 以问促读,以读促思 / 葛惠霞
- 2009年湖北与台湾高考语文试卷的比较分析 / 庞 新 王明建
- 新材料作文:中考作文考试的大趋势 / 刘 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