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07年第8期
ID: 93128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07年第8期
ID: 93128
跟我到草堂看望杜甫
◇ 丁启阵
前后一共五次到成都,我都去了杜甫草堂。
也许有人会说,你是研究杜甫的,当然会对杜甫格外有感情,看看杜甫草堂也可能对研究杜甫有所帮助。这话当然不能说是错了,但是,它只能算是部分正确。因为,前两次去草堂的时候,还没有开始研究杜甫。我一直认为,到成都而不去草堂走一走,是难以想象的一件事情。
之所以一定要到那里转一转,主要是想重温一下那熟悉的厅堂草木,感受一下那氤氲翠绿的气息,借机任由着思绪飘飞过时光的隧道,去看望一下我所喜爱的落魄诗人——杜甫。
如果你也对杜甫这个人、杜甫的诗歌、杜甫一家在成都草堂时期的生活怀有浓厚的兴趣,那就请你静下心来,暂时撇开一切关乎名利的杂念,跟我一道去看望一下这位值得我们所有人尊敬的唐代诗人吧。
杜甫一家是唐乾元二年(759)年底来到成都的。挈妇将雏,翻越崇山峻岭后来到成都,这个蜀汉故都、玄宗李隆基不久前的避难之地,让杜甫的眼前为之一亮:
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成都府》)
杜甫虽然仕途坎坷,人生境遇一直不得意,但毕竟也是见识过世面的人:开元天宝盛世年代,长大于东都洛阳,游历过吴越,曾经频繁出入于长安达官贵人的府第花园。成都再繁华,大约也无法跟“安史之乱”爆发前的长安相比吧。但是,“安史之乱”以后,一切都不一样了。“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春望》),长安已经是遍地瓦砾,满目疮痍了;华州弃官之后,秦州、同谷一带的漂泊,一家老小时时陷入饥寒交迫之中,对于繁华都市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了。这个时候,成都突现眼前,一家老小的欣喜之情不难想象。杜甫本人虽然也在心头掠过对战火中的中原、家乡的惦念和不安,但是,由于一批亲友的帮助,一家人的生活马上有了着落。杜甫的亲友在当地都是手掌中有权、褡裢里有钱的头面人物,因此,他很快就有了不小的一片土地,有了修建住宅的资金。日常生活费用有做官的老朋友提供,热情的邻居也给他们送来了蔬菜。暂时寄居在浣花溪寺的诗人,年近五十、身体衰病、久经流离的诗人,一下子感到了满足,决定安心在这里长住下去。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营造他自称“草堂”的住宅。不过,“草堂”本身的营造情形,现存的杜甫诗歌里并没有提到。杜甫自己饶有兴致地做了记录的是植树造林。他种树,种竹,也种果树;到处跟一班县级地方官员索要秧苗种子,忙得不亦乐乎。请看他的树种来历:
桃树秧苗100棵(《萧八明府实处觅桃栽》)
绵竹(《从韦二明府续处觅绵竹》)
桤木(《凭何十少府邕觅桤木栽》)
松树(《凭韦少府班觅松树子栽》)
果木(《诣徐卿觅果栽》)——可能是有多种果树,“不问绿李与黄梅”。
在此之前,除了回忆童年时代有喜爱爬树的淘气表现,“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百忧集行》),我们没有看到杜甫对于栽种植物的兴趣。而这个时候,杜甫简直像一个园艺家一样从事起栽种工作。十年树木,这说明杜甫这个时候是准备在这里一直住到老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经营,草堂营造好了,周边的植树造林也初见成效,杜甫一家的生活步入正轨。
我选择看望杜甫的时间是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初夏某日。
杜甫当年的草堂,内部既不能跟现在的“杜甫草堂博物馆”相比,周边环境跟今天的情况也完全不一样。据文献记载,晚唐著名诗人、晚年任前蜀国宰相的韦庄,为了表示对前辈诗人的崇敬,最先在杜甫草堂原址上重建茅屋,使杜甫草堂故址的概念得以确立,不至于轻易被人占用。宋代又重建茅屋,并在室内壁间绘杜甫像,开始具有祠宇性质。经过历代尤其是明清时期的重修,规模不断扩大,建筑也不断增加。今天的杜甫草堂,包括祠堂、展览馆、园林、寺庙等部分,占地二百四十馀亩。论占地规模,论园林清幽,论建筑豪华,都超过了国内任何大地主庄园。我今年刚参观过的刘文彩地主庄园,就无法跟杜甫草堂相提并论。难怪有些人在游览杜甫草堂之后,开玩笑说,这哪里是草堂啊?简直是皇家花园!草堂一位管理人员有一次开玩笑说,他自己就是得到杜甫“广厦”庇护的寒士之一。成都市园林局等有关部门在杜甫草堂的东、南、西三面修建了浣花公园,掘湖堆山,植树造林,在正对着杜甫草堂南门的地方修建了“中国诗歌大道”,刻历代著名诗人诗句于大理石路面,旁边树立诗人雕像。浣花溪公园,已经成为一处风景优美的诗歌文化主题公园。今天,杜甫草堂、浣花公园周边地区,已经成了成都市地产的黄金地段,有些被开发成了别墅式住宅区,只有财富新贵才买得起那里的房子。就是说,杜甫草堂今天已经被成都的富人们包围了。
当年的杜甫草堂,位于成都府城的西门外,属于郊区地带,可以算是农村。东边是浣花溪,有万里桥,南边有百花潭。李白二十来岁到过的散花楼,司马相如故里琴台,都离得不远,即使步行,也片刻可至。今天杜甫草堂一处大门口的楹联非常直接地表明了当年杜甫草堂的地理位置:
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
这副对联,出自杜甫诗《怀锦水居止二首》之二,作于离开成都不久。描写草堂地理形势,杜甫另有类似诗句道:“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狂夫》)
结合杜甫的其他一些诗句来看,我们知道,当时杜甫草堂附近住着八九户人家。邻居中颇有几个不俗的人物。北边住着一位退休的县令,“爱酒晋山涛,能诗何水部”(《北邻》)。能饮酒,会作诗,是晋代大名士山涛、诗人何逊一流的人物。南边住着一位隐士,此人富有童心,很受杜甫的孩子们欢迎,一旦有了粮食,就在自家院子里喂鸟雀,鸟雀因此都听他的话,喜欢到小溪流里划船。这两位都跟杜甫有频繁的来往,其中后者有时候天晚了才回家,以至于“相送柴门月色新”(《南邻》)。他们来往的一个重要内容,大约就是聚在一起喝酒。
稍微远些的,还住着一位有趣的女性——黄四娘,就是杜甫《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六中所说的“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中的黄四娘。这位黄四娘曾引起后代一些文人的愤愤不平,说黄四娘是什么人,竟然凭借着老杜的诗歌得以流芳百世、永垂不朽。还作了种种猜测,有人说是富贵人家的妇女,有人说是普通农家妇女,有人说是妓女。而根据我的研究,应该是“花禅”,也就是曾经沦落风尘的尼姑。撇开身世出处不说,这位妇女至少有一个可取之处:庭院花草侍弄得很不错。她竟然能够吸引诗人杜甫前去赏花,合理想象—下,这黄四娘总须有些过人之处吧,不是姿色,便是文才。我们知道,杜甫走后三四十年,万里桥边就又住了一位著名的色艺双全的女子——薛涛。或许,这一片土地对才貌双全的女子有着特殊的吸引力。
自然,除了有文化的邻居之外,杜甫也跟一些农夫有来往。特别是寒食节的时候,农夫们很乐意邀请杜甫去他们家喝酒。说到这个,我要把后来发生的一次饮酒情节提前来说。杜甫的老朋友严武到成都做长官之后,一位老农于寒食节的社日邀请杜甫去他家品尝新酿的春酒。喝得高兴,他就要求杜甫当天不要回家了,住在他家。一边吆喝他妻子打开大酒瓶,大声吩咐家人拿果子栗子来。杜甫几次起身,都被他粗鲁地扯住胳膊肘。月亮都升上天了,还在那里挽留杜甫,装着生气的样子责备杜甫不该问喝了多少酒,说自己家里有的是酒(《遭田父泥饮美中丞》)。这农夫经过杜甫诗歌的描绘,就成了一个不朽的文学形象,相当可爱。
说话间,我们就来到了杜甫的家门口——柴门。
假如我们到达杜甫家的时候是晌午时分,杜甫在做什么呢?他可能在园子里种菜,同时照料他的药草;可能在水槛那里坐着钓鱼,边琢磨着诗律;可能在树林里散步,察看他新种的四棵小松树;可能在砍伐竹子,嘴里默诵着“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的诗句:可能正面对被风刮倒有二百多年历史的楠木,吟出“我有新诗何处吟,草堂自此无颜色”这样令人伤感的句子;可能正跟妻子杨氏在由她手画的棋局上下棋,应该是围棋——几年前草堂里边发掘了一个唐代遗址,就发现了一枚围棋子,旁边,他们的孩子正在将妈妈的缝衣针敲弯了准备做钓鱼钩;也可能这一天天气比较热,杜甫正跟他妻子在划船,他们的孩子在附近水里游泳戏水;不巧的话,杜甫家因为好久没有得到好朋友高适等人的接济,揭不开锅了,尚不懂事的小儿子因为肚子饿,正在东门口大哭,喊着要吃饭。我们假设,这一天还是比较巧的,没有赶上杜甫的倒霉时刻。他们一家的心情都不错。
[##]
我们当然是杜甫的爱慕者,是他的粉丝,能够背诵他的不少诗句;我们还带了几瓶好酒去。这两点使我们的造访受到了杜甫的欢迎。他吩咐家人多做一些饭菜,招待我们共进午餐。
饭前,我们征得主人同意,参观了一下他们的住家。杜甫的家当然不是今天房地产商所说的高尚住宅,就是茅草为顶、筑泥为墙的几间平房。不过里外收拾得都相当敞亮,一尘不染。客厅正中应该挂着杜甫朋友王宰的山水画。请这王宰画画儿,据说还颇不容易,这家伙架子摆得不小,“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慢慢悠悠,一副能者不慌的样子,好不容易才画完这画儿(《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按照惯例,山水画的两边应该有对联。对联或许是杜甫自己的诗句,当然不是“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登楼》),那是三年以后才写的。对联的书写者是谁呢?假设是杜甫的外甥李潮,这李潮在当时虽然赏识的人不多,但杜甫很欣赏他的八分书。杜甫喜欢笔画偏瘦的字,说“书贵瘦硬方通神”。李潮的字就是又瘦又硬的(《李潮八分小篆歌》)。可以肯定的是,客厅东边的白墙上画着一幅画儿,是两匹马,“一匹啮草一匹嘶”。不用看落款也知道,画儿出自当时著名的画家韦偃之手。据杜甫介绍,当时韦偃信手拈过一枝秃笔,就画了这幅画儿(《题壁上韦偃画马歌》)。杜甫的书房里自然也有一些书画,因为杜甫是很喜欢这两门艺术的。具体是谁的作品,他本人没有说,我们也不好随便猜测。
开饭了。饭当然是家常便饭,但是杨氏夫人毕竟是大家闺秀出身,厨艺相当好,粗茶淡饭,也做得中看又好吃。杜甫还为菜少招待不周表示歉意,说:“盘飧市远无兼味。”(《客至》)换成白话就是,住得偏僻,离市场远,买东西不方便,因而菜肴不免单调。而我们只好一再表示,饭菜已经很丰盛了。至少比他当年在华州任上,路过卫八处士家,卫八招待他的那顿夜饭,“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赠卫八处士》)要强得多了。也比他身陷安史乱军占领的长安时,一次病后在王倚家吃的饭菜——就是有长安冬菹、金城土酥的那一次(《病后过王倚饮,赠歌》),要丰盛一些。即使是比起阕乡县县尉姜七先生招待的那顿生鱼片、白米饭,“无声细下飞碎雪,有骨已剁觜春葱。偏劝腹腴愧年少,软炊香饭缘老翁”(《阌乡姜七少府设,戏赠长歌》),大约也差不到哪里去。我们列举杜甫以往的几次美食故事,逗得诗人一阵大笑。
饭后,我们要求诗人带领我们看风景。大家都说杜甫善于讲故事,“三吏”、“三别”,讲得催人泪下,大家也都接着杜甫自评的话“沉郁顿挫”,说杜甫诗歌的风格是偏于悲苦的。但是我们不忍心再惹出诗人的不快,就要求他给我们描述细致的风景。我们知道,诗人在这一方面也相当厉害。果然,杜甫就一边领着我们在田垄上行走,一边出口成章,全是他近日所作的写景句子,有一些还是当时即兴咏出的:
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为农》)
风含翠筱娟娟净,雨渑红蕖冉冉香。(《狂夫》)
榉柳枝枝弱,枇杷树树香。鸬鹚西日照,晒翅满鱼梁。(《田舍》)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春夜喜雨》)
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遭心二首》其一)
仰蜂粘落絮,行蚁上枯树。(《独酌》)
芹泥随燕嘴,花蕊上蜂须。(《徐步》)
一下子领略到这么多细致入微的写景诗句,我们简直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五十多岁的诗人,身患肺气肿、糖尿病等多种疾病,走路也不太稳健了,眼神却仍然这么好。诗人的一双眼睛,简直是显微镜啊。杜甫当然不只是观察事物细致,还很幽默。走到一处小村子,他吟出了“地僻相识尽,鸡犬亦忘归”两句(《寒食》),真是写尽了乡村生活的温馨与亲切。
尽管仕途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但是杜甫作诗的兴致还是十分浓厚。对于诗歌艺术,他依然十分执著地追求着。就像他自己说的。“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他还在用心学习陶渊明、谢灵运,期望着自己的成就能跟他们并肩(《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杜甫也有不少愁心事,“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可惜》)。可见,他是离不开诗的。
交谈之中,我们更多地了解到诗人内心的苦恼。刚刚到达成都的时候,一次参观诸葛亮祠,联系到他自己的一生,政治理想未能实现。对诸葛亮不禁又是羡慕,又是同情。“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每当想起战乱,想起兄弟离散,想起自己年老体衰,他也常常黯然神伤:
京洛云山外,音书静不来。(《云山》)
干戈犹未定,弟妹各何之!……衰疾哪能久,应无见汝期。(《遣兴》))
中原有兄弟,万里正含情。(《村夜》)
故林归未得,排闷强裁诗。(《江亭》)
不用说,杜甫也想起了,他的好朋友李白。这个时候李白因为参与了永王李磷的军事行动,李?被定性为叛乱,李白也不能逃脱牢狱之灾,世人纷纷指责。只有杜甫力排众议,主张李白才华超群,理应宽待。“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不见》)。前一年秋天八月的大风,卷走了杜甫家茅屋顶上的茅草,结果,一夜里茅屋四处漏雨,家人受冻。杜甫由此想到了普天下的寒士,希望着眼前突然出现千万间广厦,“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要真有那么一天,即使是他自己受冻而死也无怨无悔(《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当他说到这里,我们不禁为之悚然动容,肃然起敬。
天色将晚,再不走,太阳一下山,我们就无法穿过时光隧道回到21世纪,冥王星被贬出太阳系行星之列降级为矮行星的2006年8月底,明天上班还须起早呢。我们只好跟诗人告辞,祝福诗人一家生活幸福美满。晚霞中,我们向着草堂,向着茅屋,向着柴门,向着诗人伫立的方向不住挥动衣袖。
再见了,草堂!再见了,诗人!
(选自《文史知识》2007年第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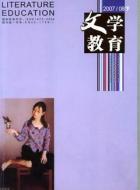
- 难忘的一件事 / 李 楠
- 思想的碎片 / 薛应平
- 话说杨志 / 刘正军
- 寝室文化与德育 / 桂艳溢
- 语文教学要留住学生 / 林运娟
- 拓展作业的五个空间 / 汤 蒙
- 自主学习是学好语文的关键 / 刘春才 胡善姣
- 新课程下的语文教学 / 黄 伟 叶春敏
- 应提倡语文教学生活化 / 张丽霞
- 语文情景教学例谈 / 来文玲
- 综合性学习与美育熏染 / 李光明
- 拓展语文学习的渠道 / 陈活兰
- 同理心是师生沟通的润滑剂 / 王丽霞
- 语文基础学段要重视养成教育 / 李密红
- 多媒体使语文教学更精彩 / 吴仲华
- 图书馆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阵地 / 赵伟达 高志刚
- 整合资源是校本开发的有效起点 / 刘方池
- 让学生自己站起来发言 / 吴鹏飞
- 从鲁迅作品看仿词仿句的妙用 / 刘伟琳
- 尝试训练型课堂教学 / 马永红
- 怎样培养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 / 康小曼
- 2007年安徽高考作文命题的现实背景 / 苏金文
- 2007年高考湖北卷作文答卷分析 / 吴红梅
- 职校作文教学方法谈 / 刘清明
- 手机短信创作十法 / 王爱红
- 写作教学的几点心得 / 李 丽 王章材
- 激发农村中学生写作兴趣的尝试 / 杨流德
- 作文教学须系统有序地进行 / 黄 兴
- 作文教学要充满人文关怀 / 刘振利 李善伦
- 指导中专生写好作文的实践与体会 / 曾晓芳
- 写作教学漫谈 / 洪 丽 龚玉华
- 下水作文的论争起源及主张 / 何 武
- 中学生应多读经典 / 杨佳君
- 从历史的角度再看焦母 / 杨英梅
- 关于幼儿教育的几点认识 / 王学玉
- 《心声》呼唤了怎样的新思想 / 印保群
- 对网络文学的整体认识与思考 / 刘玉有
- 语文教学要注重文化传承 / 骆怡龄
- 什么样的语文课才是优质课 / 原 野
- 透视当下网络文学 / 赵 燕
- 析《于园》山水之奇 / 周小辉
- 品《记承天寺夜游》的 / 程小芳
- 《断魂枪》主题解析 / 朱枝娥
- 《黄生借书说》的结构分析 / 李美芳
- 《琵琶行》中琵琶女的情感世界 / 杨晓莹
- 《行行重行行》诗意新辨 / 张守文
- 秦观《鹊桥仙》的情与爱 / 王力明
- 《长生殿》剧中杨玉环形象再析 / 张曼娣
- 《师说》搏海弄潮的对比艺术 / 李汉云
- 《雷雨》中繁漪的三种悲剧抗争 / 粟凤华
- 《蒹葭》的朦胧美 / 吴亚娥
- 阅读说明文方法谈 / 颜学凤
- 在朗读中培养学生的语感 / 姬永辉
- 让课外阅读成为学生的习惯 / 陈礼兰
- 巧用历史地图有效进行阅读 / 李建军
- 文学作品阅读技巧 / 张盛剑
- 网络时代的阅读教学 / 龙平波
- 中学外国文学课文阅读教学例谈 / 吴思思
- 用科学的方法进行阅读教学 / 王岩秋
- 高中学段怎样进行朗读教学 / 郑巧红 姜颖琳
- 语文课外阅读的实践与思考 / 张晓玲
- 阅读教学是培养语文素质的重要途径 / 王喜玲
- 语法切入法在文言文阅读中的运用 / 郑承猛
- 在阅读教学中如何让学生主动学习 / 罗小容
- 找回失踪了的阅读 / 葛友民
- 关于古诗词个性化阅读能力的培养 / 梁春燕
- 化整为零阅读方法初探 / 杨小丰
- 文言文三读教学模式探析 / 马红霞
- 让语文课成为挥洒激情的课堂 / 丛慧芳
- 开发语文课程资源的几条途径 / 王慧丽
- 迁移在语文学科中的运用 / 彭旭升
- 如何让古诗教学充满灵秀之美 / 韩海霞
- 自主学习方法设计 / 布丽榛
- 初中语文个性化教育初探 / 黄 祚
- 一堂特殊的诗歌欣赏课 / 钟 文
- 多媒体在高中小说教学中的应用 / 韦远脉
- 浅谈初中生语文素养的培养 / 徐晓燕
- 诗歌综合性学习教学案例 / 黄国林
- 语文课堂应成为师生共唱的天堂 / 侯西法
- 上好高中语文第一课的自我尝试 / 徐小平
- 制约语文课堂活跃因素的心理学分析 / 金 砚
- 高中新课改对师生关系的期待 / 张 莉
- 以修辞学为视角上好《雷雨》 / 朱国娟 范兴信
- 探究式学习课堂模式的本质与原则 / 朱小灵
- 论诗之意境 / 谭 娅
- 苏轼词艺术特色例析 / 刘名新
- 论阮籍与魏晋玄学的关系 / 彭 闹
- 《毛诗正义》的注疏成就 / 谈春蓉 李 锐
- 欧阳修与苏轼赋的立意比较 / 季三华
- 解读海明威的死亡意识 / 范海侠
- 纳兰性德咏物词的情感色形 / 海 刚
- “美”字的起源及其初义研析 / 冯海玲 杨 莹
- 金庸及其侠义思想研究 / 田 伟
- 冯梦龙笔下婚姻中的女性形象 / 罗 荣
- 王安忆与张爱玲笔下的城市主题 / 倪 新
- 幸福是件俗事 / 卫宣利
- 艳遇 / 洪 晃
- 思想杂碎 / 朱铁志
- 跟我到草堂看望杜甫 / 丁启阵
-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语文教育 / 侯姝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