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07年第8期
ID: 93122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07年第8期
ID: 93122
金庸及其侠义思想研究
◇ 田 伟
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必有金庸的小说。在很久以前,就有人这么说。诚然,以传播学的观点来看,金庸小说的传播范围是很大的,在世界上有许多名著传播范围也很广,像《圣经》,大仲马、托尔斯泰等大作家的作品。在中国也是如此,像《毛泽东选集》,巴金、鲁迅等作家的作品,但这些作品的传播仅限于固定的接受人群,如宗教人群,文学爱好者以及某种意识形态下的接受人群。而金庸先生则创造了一个奇迹,不仅传播范围广,而且“受众”也形形色色,诸如国家领导人、大学教师、学生、工人、普通老百姓……可以说涵盖了所有中国人,不仅如此,在外国也有广泛的受众,越南政党辩论就引用金庸《笑傲江湖》中的“左冷禅”来讽谕对方强权。
金庸之所以成功,一方面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对“侠”有一种割舍不掉的情感,有广泛的接受心理,另一方面是金庸的艺术手法和创新意识与当时的接受氛围相吻合。
一、侠之大者
在《神雕侠侣》中,金庸对“侠”下了个定义: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可以说,这不仅仅是金庸,也是所有武侠小说家笔下“侠”的一个基本特征,至少是“为国为民”二者有其一,以金庸小说为例,郭靖、杨过、张无忌、乔峰、乃至包括韦小宝,俱是如此。金庸试图通过武侠小说来塑造一种全新的人格,具体来说就是在中国文化的框架里构建一种全新的人格。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呈现一种三教并存的多元化趋势,但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儒家思想逐渐占了主导地位,儒家思想的包容和对统治的实用价值很快使其成为中国后世的主流思想,但这种思想从一开始就注定要畸形,它的创始人孔子出身没落贵族,使他的思想带上了保守的烙印,他游学于世,兴办教育,固然有建立一个较和谐社会的目的,所以强调仁。但更多的是周旋进退和经世致用,其政治目的,只不过较为理性,并对手段加以规范,所以强调“道”和“礼”。这种思想本身是比较健康的,但很不幸,这种思想和权力结合的一塌糊涂,在经过统治阶级以及“伪儒学派”如董仲舒等的改造,儒家思想开始成为一种统治工具,一种精神枷锁,至宋朝经过“二程”、朱熹的阐发,儒家思想逐渐法律化,宗教化,开始显示出其两重性的一面。一方面它在发挥其道德律令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让这律令为统治服务,而且无论统治阶级的好坏,所以很容易出现理的和谐与现实的肮脏相冲突的情况,这种冲突造成了中国知识分子两重性的人格特点,在他们身上充斥了虚伪、矛盾乃至肮脏的东西,造成这种畸形与儒家思想形成的初衷大相径庭,儒家思想至宋已经成为一种“存天理,灭人欲”的工具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所以畸形,就因为本身的正常欲望受到不合理的扼杀,从而也扼杀了任何一种带自由的思想,使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遭受了一次集体阉割,成为一群知识太监,完全丧失了自我。在整个社会被毒害的情况下,这种阉割受到推崇,受到膜拜,所以在金庸小说《笑傲江湖》里东方不败、岳不群、林平之才会为了达到武学上的至高境界而自我阉割,因为要达到这种境界,就要至高的武学宝典——《葵花宝典》,但这本宝典第一句话就说的很明白:欲炼此功,必先自宫。这与理学的观点一脉相承。
在这种文化背景和基础上,金庸试图重新建构一种新的文化人格,这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人格,而是所有中国人的人格。在五四运动打倒的传统文化的废墟上,金庸接受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内核,借鉴西方文化中与中国文化相适应的一部分,形成新的人格标准,并在小说中塑造具有这类标准的人物,最开始是陈家洛,他是个很传统的人,他的人生目标是“反清复明,匡护正义”,但他很快就茫然了,反清是因为它残暴和不正义,那么复明呢,明朝就不残暴,就正义吗?!当然不,所以他这个目标很是苍白和没理由,而“匡护正义”,在反抗清廷的残暴和社会的不公上,陈家洛的确身体力行,算是有所成就,但他仍然是幼稚的,他读对圣贤书,身体力行,却没看出对圣贤书所代表的儒家思想的两重性、虚伪性,傻呼呼的绑架乾隆,并以乾隆有汉人血统为理由,要求他还汉家河山。陈家洛不知道,乾隆是满人则可统治天下,是汉人则自家性命尚且难保(他所倚重的满族力量是不会让一个汉人当皇帝的),更不用说什么还汉家河山了!陈家洛的失败在于他读懂了圣贤书,却没读懂人性,他大大的高估了教化对人的作用,也存在缺乏与时俱进的保守主义的色彩。陈家洛的失败也是中国历史上许多有良知,可爱可敬的读书人失败的一个缩影。
郭靖则与之有所区别,郭靖虽傻,但经历的坎坷却使他大彻大悟,有一种大智若愚的味道。“出世”和“入世”都把握的很好,出世则和黄蓉在桃花岛闲云野鹤,入世则国难当头时挺身而出,就算这个国国将不国,就算兵败自杀也在所不惜,表现出一种优秀中国人的素质,真正做到了舍身取义。虽然带有完美主义之嫌。
郭靖之死有一种为文化殉葬的意味,他的死是一个悲剧,但他还有一种文化可以殉葬。乔峰则不然,乔峰是契丹人,相对于大宋他是异族,但他长在大宋,从异族身份暴露的那一天开始,乔峰开始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对大宋人来说他是契丹人,对契丹人来说他是大宋人,就算有个当契丹皇帝的拜把子兄弟也无济于事,猜忌和防范始终如影随行,而伴随这种尴尬的是昔日兄弟的反目,心爱的人死在自己手里,在大宋和契丹敌对关系中的左右为难……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乔峰仍然以自己的生命换来了大宋和契丹的和平,所以说乔峰是金庸小说中的大人物和大悲剧,也是最能担的起“侠之大者”的人。
金庸在小说里结合东西方各种思潮通过侠的塑造对中国人的人格进行了整合和再造,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人格。从陈家洛到乔峰,从杨过到韦小宝,金庸开始让他的主人公面对自己或者说人本身的情感与感受,而不仅仅是制度与框架。
二、葵花宝典
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在武侠小说中武功秘籍成为必不可少的桥段,一旦获得武功秘籍,就会功力大增乃至天下无敌,这种桥段一向被评论家攻击,认为这与西方小说中的“飞来横财”一样带唯心的功利主义,这种桥段在中国旧小说和传奇中屡屡出现。金庸小说里也带有这种旧小说的痕迹,但格调要比旧小说和西方类似作品高的多,且多多少少带有哲理思辨的味道。比如《天龙八部》中逍遥派的功夫就跟庄子扯得上关系,庄子有部著作叫《逍遥游》,其中有句话说:北冥有鱼,其名为鲲。所以逍遥派中的一种很厉害的武功就叫北瞑神功。但金庸笔下最富有哲学意味的功夫却是葵花宝典,葵花宝典是太监所创,所以练习的人也必须先成为太监。这种武功特别厉害,练习的人又必须是太监,这就决定了要想武功厉害,就得自宫,这种生理上的自我摧残直接导致了心理变态。《笑傲江湖》中东方不败就是典型的例子,他(或她)的手段之所以残忍,一方面因为男人生理机能的丧失,另一方面,因为想做女人而不可得,性别的模糊,得不到的欲望,使之将这种缺憾的痛苦转嫁到其他人身上,进而演变为一种血腥的暴力,让鲜血来淡化这种缺憾,达到心理平衡的目的。
通过葵花宝典我们可以看出人性的压抑对人的正邪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东方不败的自宫是源于对权力的追逐,岳不群、左冷禅的自宫同样是一种自我行为,在《笑傲江湖》中除了林平之的自宫是源于复仇的需要外,其它人莫不是因为利欲薰心而产生的一种病态的导致变态的行为。在金庸的小说里还有一种人性压抑,这种压抑来自一种框架和律令的束缚,像《倚天屠龙记》里的灭绝师太,佛教的禁忌使人性受到了扭曲,使她虽正犹邪,在一种值得怀疑的正邪理论的支配下,进行一种合理的屠杀,这同东方不败是同样的心理,有所不同的是灭绝师太有一柄合法的倚天剑。
[##]
人性的压抑还会使一种合理的行为演变成为犯罪,尹志平(《神雕侠侣》)爱慕小龙女,这种再正常不过的感情在尹志平身上发生就是不正常,因为他身上披了一身道袍,而且还有名利的纤绊,最后在压抑中做出对小龙女轻薄侮辱的事来,成了一名罪犯。
这种对人性不合理的压抑使社会是非评判的标准发生偏颇,《倚天屠龙记》中明教中杨逍等人历来被视为魔头,就因为他们行事不拘一格而注重合理人性的挥洒,这与社会中对人性压抑的框架相抵触,所以不管他们做什么总是错的;《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亦是如此,令狐冲的放荡不羁岂是框架内人们所能接受的。明教兴盛于元末明初,正是理学转入鼎盛的时期,所以明教诸人铁定是悲剧性结局,而令狐这一姓氏最初出现在魏晋,那个时代是中国文化史有名的高压时期,在这一时期狂娟名士辈出,像竹林七贤,令狐冲身上有他们的影子,他们大都以悲剧结束人生,相对而言,令狐冲的命运算是圆满的。
金庸小说中有许多人性的悲剧,这让我们唏嘘,也让我们深思。
三、问世间情为何物
金庸小说之所以读者甚广,还因为小说中各种缠绵的爱情,陈家洛和香香公主,胡斐与苗若兰,杨过与小龙女,郭靖与黄蓉……金庸笔下的爱情拒绝低俗,美丽动人,就连反派的爱情也颇有动人之处,像李莫愁、成昆。在爱情中是最没有是非之分的。
有人说人与人之间是永远无法沟通的。恋人之间也是如此,在金庸笔下,恋人之间也常出现误解猜疑,要么就是外界因素的干扰,总而言之,爱情通常都要付出代价和创伤。爱情是美丽的,但美丽总是令人忧愁。
杨过和小龙女的爱情是金庸小说中最美丽的爱情,小龙女年纪比杨过稍大,杨过还是小龙女带大的,他们之间有一种姐弟恋的味道。他们的爱情发生在一个叫古墓的地方,古墓是王重阳和林朝英两个前辈爱情失败的见证,是一个埋葬爱情的所在,在杨过进入古墓时,墓中就两个人,还有一个孙婆婆照顾小龙女,自从杨过来后,孙婆婆因伤去世,基本上与世隔绝的古墓就有两个人了,这个世界也就两个人了,杨过一生受尽侮辱和挫折极其敏感和脆弱。小龙女冷漠自闭,爱情的出现让两人感到了温暖,特别是对杨过实现了灵魂的拯救,小龙女和杨过的爱情是一种情感的依赖,但另一个出自古墓的人李莫愁则不然,李莫愁虽坏,但对爱情却出奇的忠贞,她为了一个不爱自己的人守身如玉了一生,而且因爱成恨,变得冷酷无情,残忍毒辣,她对爱情的占有欲大于依赖,她很可怜,但更可怕。爱情有时也会成为人疯狂的理由。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金庸对爱情的描述让人觉得在一个人性的荒漠里尚有一块绿洲可供我们徜徉,让我们尚能得到些许温暖,这种爱情是非物质的,是不受意识形态支配的,但也是不大可能和令人绝望的,因为他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葵花宝典至高无上的时代。
四、刀剑如梦
金庸先生以武侠小说而享誉世界,也以武侠小说反映了作者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他的叙事风格和方式,小说情节和推进都明显带上西方文学影响的印迹,但是却自然不显生硬,还给人一种传统评书的味道,中西方艺术的结合与完美无限接近,是中国文学史上划时代的作品之一,也是那个时代的鲜明特征之一。对中国人的观念有着重要的影响。
金庸先生是一个带传统色彩的知识分子,固然在小说中可看出人性与文化根源的诸多关系,但作为小说家,金庸先生显然把人物塑造,与故事情节以及艺术魅力作为他创作的出发点,小说中出现的人性文化根源的关系,有许多只是读者的再发现,金庸是一个优秀的小说家,也是一位不自觉的思想家。他用他的作品以及他本身向人们显露出了一个在中西方文化,伦理与人性的冲突中挣扎的中国人的心理状态和观点。作品和自身都具有文化史上的重要意义。
武侠小说自诞生开始就打上了文人梦幻的烙印,陈平原先生的武侠小说研究专著的书名就叫《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在梦幻里赋于文人超人的力量去实现现实生活中不大可能实现的梦想,有文人思想情感上挣扎、追寻的痕迹。如在金庸先生早期的作品中主人公的意志行为大多服从于一种大而泛的理念,如国家,天下苍生,主人公也就是维护这些理念的神和超人,他们的情感,思想,在这些理念面前要么被同化,要么退居次要;而中后期的作品中这些大而泛的理念逐渐淡出,而注重人本性的挥洒,开始脱离一种泛和谐主义,重新确立人之自由的首要地位让人依靠自己的思想情感去自由选择,带上了萨特的存在主义色彩,这些都向我们展示了作者的心路历程和思想轨迹。但小说本身仍是梦幻之言,注重真实历史氛围的金庸也摆脱不了这种梦幻的宿命,正所谓刀剑如梦。现实中绝无出现武侠世界之可能,武侠小说中人物的行为和所表现出来的人性,用现实的眼光来看实际上是戴着镣铐跳舞,换句话说只有充满神话和超人力量才可能有武侠世界。金庸先生明白这一点,所以在他的收山之作《鹿鼎记》中描述了一个与现实无限接近的武侠世界,或者说是一种脱离了武侠氛围的境地,也塑造了一个带无厘头感觉的侠——韦小宝,这是否是在繁华落尽,梦醒之后的反思和回归呢?毕竟现实生活中的侠才能给人一种真实的感觉或者说一种可能。
田伟,湖北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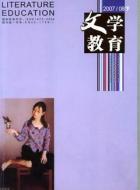
- 难忘的一件事 / 李 楠
- 思想的碎片 / 薛应平
- 话说杨志 / 刘正军
- 寝室文化与德育 / 桂艳溢
- 语文教学要留住学生 / 林运娟
- 拓展作业的五个空间 / 汤 蒙
- 自主学习是学好语文的关键 / 刘春才 胡善姣
- 新课程下的语文教学 / 黄 伟 叶春敏
- 应提倡语文教学生活化 / 张丽霞
- 语文情景教学例谈 / 来文玲
- 综合性学习与美育熏染 / 李光明
- 拓展语文学习的渠道 / 陈活兰
- 同理心是师生沟通的润滑剂 / 王丽霞
- 语文基础学段要重视养成教育 / 李密红
- 多媒体使语文教学更精彩 / 吴仲华
- 图书馆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阵地 / 赵伟达 高志刚
- 整合资源是校本开发的有效起点 / 刘方池
- 让学生自己站起来发言 / 吴鹏飞
- 从鲁迅作品看仿词仿句的妙用 / 刘伟琳
- 尝试训练型课堂教学 / 马永红
- 怎样培养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 / 康小曼
- 2007年安徽高考作文命题的现实背景 / 苏金文
- 2007年高考湖北卷作文答卷分析 / 吴红梅
- 职校作文教学方法谈 / 刘清明
- 手机短信创作十法 / 王爱红
- 写作教学的几点心得 / 李 丽 王章材
- 激发农村中学生写作兴趣的尝试 / 杨流德
- 作文教学须系统有序地进行 / 黄 兴
- 作文教学要充满人文关怀 / 刘振利 李善伦
- 指导中专生写好作文的实践与体会 / 曾晓芳
- 写作教学漫谈 / 洪 丽 龚玉华
- 下水作文的论争起源及主张 / 何 武
- 中学生应多读经典 / 杨佳君
- 从历史的角度再看焦母 / 杨英梅
- 关于幼儿教育的几点认识 / 王学玉
- 《心声》呼唤了怎样的新思想 / 印保群
- 对网络文学的整体认识与思考 / 刘玉有
- 语文教学要注重文化传承 / 骆怡龄
- 什么样的语文课才是优质课 / 原 野
- 透视当下网络文学 / 赵 燕
- 析《于园》山水之奇 / 周小辉
- 品《记承天寺夜游》的 / 程小芳
- 《断魂枪》主题解析 / 朱枝娥
- 《黄生借书说》的结构分析 / 李美芳
- 《琵琶行》中琵琶女的情感世界 / 杨晓莹
- 《行行重行行》诗意新辨 / 张守文
- 秦观《鹊桥仙》的情与爱 / 王力明
- 《长生殿》剧中杨玉环形象再析 / 张曼娣
- 《师说》搏海弄潮的对比艺术 / 李汉云
- 《雷雨》中繁漪的三种悲剧抗争 / 粟凤华
- 《蒹葭》的朦胧美 / 吴亚娥
- 阅读说明文方法谈 / 颜学凤
- 在朗读中培养学生的语感 / 姬永辉
- 让课外阅读成为学生的习惯 / 陈礼兰
- 巧用历史地图有效进行阅读 / 李建军
- 文学作品阅读技巧 / 张盛剑
- 网络时代的阅读教学 / 龙平波
- 中学外国文学课文阅读教学例谈 / 吴思思
- 用科学的方法进行阅读教学 / 王岩秋
- 高中学段怎样进行朗读教学 / 郑巧红 姜颖琳
- 语文课外阅读的实践与思考 / 张晓玲
- 阅读教学是培养语文素质的重要途径 / 王喜玲
- 语法切入法在文言文阅读中的运用 / 郑承猛
- 在阅读教学中如何让学生主动学习 / 罗小容
- 找回失踪了的阅读 / 葛友民
- 关于古诗词个性化阅读能力的培养 / 梁春燕
- 化整为零阅读方法初探 / 杨小丰
- 文言文三读教学模式探析 / 马红霞
- 让语文课成为挥洒激情的课堂 / 丛慧芳
- 开发语文课程资源的几条途径 / 王慧丽
- 迁移在语文学科中的运用 / 彭旭升
- 如何让古诗教学充满灵秀之美 / 韩海霞
- 自主学习方法设计 / 布丽榛
- 初中语文个性化教育初探 / 黄 祚
- 一堂特殊的诗歌欣赏课 / 钟 文
- 多媒体在高中小说教学中的应用 / 韦远脉
- 浅谈初中生语文素养的培养 / 徐晓燕
- 诗歌综合性学习教学案例 / 黄国林
- 语文课堂应成为师生共唱的天堂 / 侯西法
- 上好高中语文第一课的自我尝试 / 徐小平
- 制约语文课堂活跃因素的心理学分析 / 金 砚
- 高中新课改对师生关系的期待 / 张 莉
- 以修辞学为视角上好《雷雨》 / 朱国娟 范兴信
- 探究式学习课堂模式的本质与原则 / 朱小灵
- 论诗之意境 / 谭 娅
- 苏轼词艺术特色例析 / 刘名新
- 论阮籍与魏晋玄学的关系 / 彭 闹
- 《毛诗正义》的注疏成就 / 谈春蓉 李 锐
- 欧阳修与苏轼赋的立意比较 / 季三华
- 解读海明威的死亡意识 / 范海侠
- 纳兰性德咏物词的情感色形 / 海 刚
- “美”字的起源及其初义研析 / 冯海玲 杨 莹
- 金庸及其侠义思想研究 / 田 伟
- 冯梦龙笔下婚姻中的女性形象 / 罗 荣
- 王安忆与张爱玲笔下的城市主题 / 倪 新
- 幸福是件俗事 / 卫宣利
- 艳遇 / 洪 晃
- 思想杂碎 / 朱铁志
- 跟我到草堂看望杜甫 / 丁启阵
-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语文教育 / 侯姝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