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07年第8期
ID: 93124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07年第8期
ID: 93124
王安忆与张爱玲笔下的城市主题
◇ 倪 新
有些作家将他们的小说写作定于一个固定的空间:他们的故事都发生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故事环境中,这里的人物互相认识,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结成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作家笔下所出现的每个特定写作环境多半存留着乡村社会的遗迹,作家所喜爱的固定写作空间往往是一个村落或一个乡村边缘小镇。通常乡村社会拥有更为严密的社会成员管理体系,宗教、伦理、风俗、道德共同组成了乡村社会的文化。乡村空间轮廓清晰,版图分明,相对的封闭致使他们的叙述集中而富有效率,这些作家的心爱人物不至于走出他们的叙述中,消失在叙述的辖区之外。
与众不同的是,王安忆和张爱玲两位才女更乐于为她们的小说选择城市——一个开放而又繁闹的空间。“这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源于她们的女性立场。在她们看来,作为一个人造的自然,城市更为适合女性生存,她们卸下了农业社会对于体魄的苛刻要求,这个崭新的场所更多地接纳了女性的灵巧与智慧。”[1]可以看到,城市是张爱玲、王安忆两人持久注视的一个主题,理所当然的,女性成了城市的代言人,成了两者小说中的灵魂与精髓。
一、不同的城市画卷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城市在文学中成为一个令人反感的字眼。在人们的头脑中基本形成了一种模式:乡村是先进思想与高尚品德的发源地,而城市则是罪恶、贪欲的温床。在王安忆的笔下,尤其在《长恨歌》这部作品中,她彻底地把城市从这种传统的文学观念中解放出来,她把城市视为一个文明发展的必然阶段,她甚至善意的体谅了城市所难以回避的庸俗、奢靡和功于心计,作品中不无掩饰流露出作者对城市的好感。《长恨歌》不时体现出欣赏城市的眼光和趣味,她深知咖啡厅气氛,花团锦簇的窗帘以及街上电车之间隐藏了何种迷人的气质。王安忆的城市不仅仅是一个宏伟的景观,不仅仅是一些方形、柱形、锥形以及球形等单纯建筑物在地面上的组合;同时,王安忆深入到城市的纵深,栩栩如生的描写了一个城市的意象。《长恨歌》的第一章别出心裁地写到了几种典型的城市片断:弄堂、流言、闺阁、鸽子,王琦瑶式的女人这几个方面共同组成了一个城市的初步肖像。也许,“肖像”并不是一个比喻的用法,王安忆的《长恨歌》的确是将城市作为小说之中一个活灵活现的主人公,赋予了它生命和灵气。
《长恨歌》这部作品中,王安忆不仅企图绘制城市的图像;同时,王安忆的叙述还竭力诱使这些城市图像浮现出种种隐而不彰的含义。散文式的抒情和分析大量地填塞了人物动作的叙述空间。可以说这部小说是由人物的命运和一系列以城市为主题的散文、随笔连缀而成。种种机警而精彩的辨析恰如其分的抵消缓慢的故事节奏而导致的沉闷。的确,人们从《长恨歌》之中读到许多对于城市的想象,譬如说“上海的弄堂是性感的,有一股肌肤之亲似的”[2],说流言“是那黄梅天的雨,虽然不暴烈,却是连空气湿透了”[3];还说“上海弄堂里的闺阁已经变了种,贞女传和好莱坞情话并存,阴丹士林蓝旗袍下是高跟鞋,又古又摩登”[4]。这些城市的想象既抽象又具体。这些想象之中的城市没有具体的时间和空间坐标,种种弄堂、流言、闺阁仅仅是一种概括;另一方面,这种概括又十分感性——它不仅包含着生活的油烟气味,墙壁裂缝和背阴外的绿苔这些可感的细节,而且还包含着一系列极为个性的比拟。人们还可以在《长恨歌》这部作品中看到许多细节描写散发出世俗气息:白色滚白边的旗袍,鸭掌和扬州干丝,弄堂里夹了油烟和水气味的风——这种世俗气息得到了女性的体会和认可,形成了一个城市的底部。在这里,抽象与具体的协调致使种种散文式的片断产生了足够和故事相互映衬的诱惑魅力。
张爱玲采用传统的现实主义和西方现代的理分析派的手法,侧重从家庭婚姻角度来反映抗日战争时期沦陷了的上、香港两地的洋场生活,写了一批个人主义浸透的半殖民地特殊文化背景下的人物。
张爱玲久居沪港,对中西杂糅的都市洋场自有主见。由于她自身生活经历与环境,尤其是她对社会人生的衰感理解,很少去注意外在的都市生活中所包含的积极意义。当时上海成为孤岛,沦陷已成定局。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昨天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这种文化的失落感形成了她的人生意识和哲学意识,她使她的小说基调与现实有着相当的距离。张爱玲小说的底色是荒凉,她作品中荒凉的基调是建立在对于日常生活的描述上的,而且是对日常细节的不厌其烦的描述上的。“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往往是悲观的。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5]张爱玲的荒凉是一种悲观的感叹,一种女性化和敏锐细腻的感叹。时代、国家、革命的一切大题目都浓缩在家庭生活的一幕或一角,家庭的卧室、客厅、公司的办公室、电车、咖啡厅的一角……都在张爱玲笔下磨蚀生命,一天天地萎缩下去。世界是喧嚣的,然而用张爱玲笔下一个人物的话说:“多么寂寞,死一样的寂寞。”
张爱玲的场景往往是时间性场景,例如家传首饰,出嫁时的花袄,雕花的家具,重重叠叠的物质的影子间,晃耀着沧桑变幻、辉煌衰败喜怒衰乐的影子,人的面影黯淡,直至虚无。
对洋场东西文化混杂造成的腐烂霉变,张爱玲给予了辛辣的讽剌。如在《倾城之恋》、《沉香屑·第一炉香》中,香港的文化好似“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便硬性地给搀糅在一起”。一面是上层阶级刻意摹仿英伦生活,一面又无法褪去殖民地式的东方色彩。富孀梁太太的府邸,房子是流线型几何图案,类似最摩登的电影院,而屋顶却是仿古的碧色琉璃瓦。四周宽绰的通廊又被装饰成美国早期建筑风格。饰以西式布置的立体式客厅,却充斥着翡翠鼻烟壶、象牙观音与斑竹小屏风等中国摆设。园会本是英国上层社会的户外交际活动,而梁府的园会,“处处模仿英国习惯,然而总喜欢画蛇添足”。福字灯笼与海滩洋伞并置一和;没有穿著燕尾服的男侍,而代之以拖着油松大辫的丫头老妈子,在伞柄与灯笼之中穿梭。香港文化中那一点点东方色彩,“显然是看在外国朋友面上”的,所以“这里的中国,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荒诞、精巧、滑稽”。就如同梁府的园会布置,像好莱坞拍摄《清宫秘史》的道具一样,在香港,清季的时装被当作学生制服,据说“把女学生打扮成赛金花模样,那也是香港当局取悦于美游客的种种设施之一”。[8]更有甚者,《倾城之恋》中那个建筑、灯光、乐队都属老英国式的香港饭店,居然有怪模怪样的西崽,大热天仿着北方人穿着扎脚裤,以表现欧美人眼中的东方情调。自己民族的文化居然是受西方的刺激,才得以保留,而那一点可怜的传统文化,又竟然是西方人猎奇心理中的中国文明的小杂碎,足见其十足的殖民地色彩。
二、用相同的介入视角来反映大都市
王安忆与张爱玲两人都从小人物、小背景、小故事的角度入手,力求用小世界来反映大都市,所谓“以小见大”当如是也。我所归纳的小人物如白流苏、范柳原、佟振保、壶烟鹂、曹七巧、王琦瑶、蒋丽莉、程先生、严师母……他们都是平凡的小人物,是你在生活中所能见到原型的普通人物,他们是这个社会的底层基柱,他们是真正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人,他们的生活是城市的底蕴色彩,他们才是这个城市的灵魂与精髓。正如王安忆《长恨歌》中所言:“他们又都是生活在社会芯子里的人,埋头于各自的柴米生计,对自己都谈不上什么看法,何况是对国家、对政权。”他们远离政治:
这是一九五七年的冬天,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大事情,和这炉边的小天地无关。这小天地是在世界的边角上,或者缝隙里,互相都被遗忘,倒也是安全。窗外飘着雪宵美景啊!他们都很会动脑筋,在这炉子上做出许多文章。烤朝鲜,屋里有一炉火,是什么样的良鱼干,烤年糕片,坐一个开水锅涮羊肉,下面条。他们上午就来,来了就坐到炉子旁,边闲谈边吃喝。午饭,点心,晚饭都是连成一片的。雪天的太阳,有和没有也一样,没有了时辰似的,那时间也是连成一气的。等窗外一片漆黑,他们才迟疑不决地起身回家。这时气温已在零下,地上结着冰,他们打着寒噤,脚上滑着,像一个半梦半醒的人。(节选自王安忆的《长恨歌》)
[##]
两位作家都善于用环境来作为叙述的背景,背景不光包括环境且包含着情感基调。如张爱玲中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就是作者往往在叙述故事之前就已经设计好了别致的情景,用平静的语言铺造了一种良好的气氛,为故事环境、背景创造了不可缺少的灵光一笔。《茉莉香片》:“我给您沏的这一壶茉莉香片,也许是太苦了一点。……您先倒上一杯茶——当心烫!您尖着嘴,轻轻吹着它。在烟茶缭绕中……”又如《倾城之恋》:“胡琴咿咿呀呀地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一种苍凉的意味便在小说中弥漫、拓展、延伸开来。为作品叙述创造了一个必不可少的背景。细细观察一下,不难发现,这些背景都是由一些微小的细节,小场景组合而成,与那些宏伟壮大的历史或故事等大场面,相比而言显得更富女性的细腻的一面,所以,在这种意义上说,我把她们笔下的背景简括为“小背景”。
无论是张爱玲还是王安忆,生活、爱情、婚姻永远是她们所关注的焦点,两人笔下的故事感情细腻,回味悠长,与那些开天辟地,建功立业的故事相比而言,不能不言之为小故事。但正是这些不起眼的平凡小事,即像一面放大镜,不管生活有多少美丽和瑕?,都能照得一清二楚,不能加以丝毫的掩饰。如《沉香屑·第二炉香》中用两个男人相似的故事,揭示性力再遭到压抑乃至屈辱的同时,意味着生命也承受了同样的污辱。当人和社会再用假道德去玷辱、嘲笑、压抑性力时,人的生命便濒临干涸,最后成为一堆人生香灰,一个筑在土地上的香屑坟。作者在同情的背后充满了对禁欲的怒斥,揭露了禁欲教育对人的生命的摧残,作者用这样一个小故事揭露了社会的丑恶面。又如《长恨歌》中王安忆通过描写王琦瑶的大半生来展开故事情节,一个个的小故事组合起来展现了一个色彩明丽的女性温馨天地。
三、同中有异的“叙述策略”
“王安忆为改变自己审美的‘自我倾诉’路数,把‘创造存在物’作为创作追求。她觉得要达到‘创造存在物’的目的,依靠个人经验和认识毕竟有限,于是开始了对‘叙述策略’的探索。”[7]“她提出了创作‘四不要’原则:‘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不要材料太多,不要语言的风格化,不要特殊性’,以完备好的‘叙述策略’。”[8]在《长恨歌》里,王琦瑶这个人物,就是通过作者慢慢悠悠、絮絮叨叨地叙述走到面前的。她是个“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生活得琐琐碎碎,平平淡淡,偶尔参加个“上海小姐”评选,时代风雨也淋不到她身上。平淡的叙述之中夹杂着精彩、精辟的比喻,抒情和分析式的语言填塞了叙述的间隙,缓解了缓慢发展的故事情节所导致的沉闷,可以说《长恨歌》这部小说是由人物的命运和一系列以城市为主题的散文、随笔连缀而成,王安忆在《长恨歌》善用“是……的”句型,这也是她叙述策略中的一种叙述模式,用这种模式把平常的东西创造成为另一种存在,如“上海的弄堂是性感的,有一股肌肤之亲”,“流言是黄梅天的雨,虽然不暴烈,却是连空气都湿透了”。作者对“上海”“流言”用“是……的”句型给了它又一重定义,使读者眼中的上海不仅是一个城市,更是一个性感的女人,流言四处飞就如黄梅雨渗透了空气,不暴烈却无法让人躲避,在《长恨歌》作品中,作者的语言极富特色和诱惑力。王安忆“平实”的叙述功力非一般人所能企及,她能把常态的东西创造成为另一种存在,实在值得我们学习。
情感是文学创作的动力,“情动于中而形于言”[8]在一定意义上说,“艺术掌握即情感掌握”[9]在小说中,张爱玲甩开一般女作家惯用的“直叙法”的创作模式,绝不直接显露出大江奔腾或小溪潺潺的情感流,而采用隐叙法的情感表现方式,把作品人物的情感。如《倾城之恋》:“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一种苍凉的意味便在小说中弥漫、拓展、延伸开来。情节的组织、人物的设置、细节的处理,与作者的人生观、审美观、情绪个性是有着联系的,张爱玲生活经历决定了她作品的风格、基调。时代的变迁,家境的败落和不幸的童年,使她变得敏感,沉静庄重而忧郁,过早地接触社会,认识人生,并由此产生了对人生的否定情绪,决定了她沉默、孤僻、冷淡、不趋时的性格,同时也决定了张爱玲小说的底色——苍凉。
张爱玲这种“隐叙法”不直言情而暗含着情,留给读者无穷的回味余地,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王安忆也是用“隐叙法”来描写人物内心的复杂心情。
对于整个女性文学而言,王安忆与张爱玲两位作家的创作融百花而又自成一体,是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和学习的。
注释:
[1]王安忆《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见《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时代文艺出版社
[2][3][4][5]王安忆《长恨歌》作家出版社1995年出版
[6]《张爱玲的情感美学意识》吴敏转载《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5期
[7][8]《作家的语言》盛英转载《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9]《文艺理论》1995年第5期城锡华《艺术掌握即情感掌握》
倪新,武汉商业服务学院教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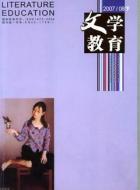
- 难忘的一件事 / 李 楠
- 思想的碎片 / 薛应平
- 话说杨志 / 刘正军
- 寝室文化与德育 / 桂艳溢
- 语文教学要留住学生 / 林运娟
- 拓展作业的五个空间 / 汤 蒙
- 自主学习是学好语文的关键 / 刘春才 胡善姣
- 新课程下的语文教学 / 黄 伟 叶春敏
- 应提倡语文教学生活化 / 张丽霞
- 语文情景教学例谈 / 来文玲
- 综合性学习与美育熏染 / 李光明
- 拓展语文学习的渠道 / 陈活兰
- 同理心是师生沟通的润滑剂 / 王丽霞
- 语文基础学段要重视养成教育 / 李密红
- 多媒体使语文教学更精彩 / 吴仲华
- 图书馆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阵地 / 赵伟达 高志刚
- 整合资源是校本开发的有效起点 / 刘方池
- 让学生自己站起来发言 / 吴鹏飞
- 从鲁迅作品看仿词仿句的妙用 / 刘伟琳
- 尝试训练型课堂教学 / 马永红
- 怎样培养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 / 康小曼
- 2007年安徽高考作文命题的现实背景 / 苏金文
- 2007年高考湖北卷作文答卷分析 / 吴红梅
- 职校作文教学方法谈 / 刘清明
- 手机短信创作十法 / 王爱红
- 写作教学的几点心得 / 李 丽 王章材
- 激发农村中学生写作兴趣的尝试 / 杨流德
- 作文教学须系统有序地进行 / 黄 兴
- 作文教学要充满人文关怀 / 刘振利 李善伦
- 指导中专生写好作文的实践与体会 / 曾晓芳
- 写作教学漫谈 / 洪 丽 龚玉华
- 下水作文的论争起源及主张 / 何 武
- 中学生应多读经典 / 杨佳君
- 从历史的角度再看焦母 / 杨英梅
- 关于幼儿教育的几点认识 / 王学玉
- 《心声》呼唤了怎样的新思想 / 印保群
- 对网络文学的整体认识与思考 / 刘玉有
- 语文教学要注重文化传承 / 骆怡龄
- 什么样的语文课才是优质课 / 原 野
- 透视当下网络文学 / 赵 燕
- 析《于园》山水之奇 / 周小辉
- 品《记承天寺夜游》的 / 程小芳
- 《断魂枪》主题解析 / 朱枝娥
- 《黄生借书说》的结构分析 / 李美芳
- 《琵琶行》中琵琶女的情感世界 / 杨晓莹
- 《行行重行行》诗意新辨 / 张守文
- 秦观《鹊桥仙》的情与爱 / 王力明
- 《长生殿》剧中杨玉环形象再析 / 张曼娣
- 《师说》搏海弄潮的对比艺术 / 李汉云
- 《雷雨》中繁漪的三种悲剧抗争 / 粟凤华
- 《蒹葭》的朦胧美 / 吴亚娥
- 阅读说明文方法谈 / 颜学凤
- 在朗读中培养学生的语感 / 姬永辉
- 让课外阅读成为学生的习惯 / 陈礼兰
- 巧用历史地图有效进行阅读 / 李建军
- 文学作品阅读技巧 / 张盛剑
- 网络时代的阅读教学 / 龙平波
- 中学外国文学课文阅读教学例谈 / 吴思思
- 用科学的方法进行阅读教学 / 王岩秋
- 高中学段怎样进行朗读教学 / 郑巧红 姜颖琳
- 语文课外阅读的实践与思考 / 张晓玲
- 阅读教学是培养语文素质的重要途径 / 王喜玲
- 语法切入法在文言文阅读中的运用 / 郑承猛
- 在阅读教学中如何让学生主动学习 / 罗小容
- 找回失踪了的阅读 / 葛友民
- 关于古诗词个性化阅读能力的培养 / 梁春燕
- 化整为零阅读方法初探 / 杨小丰
- 文言文三读教学模式探析 / 马红霞
- 让语文课成为挥洒激情的课堂 / 丛慧芳
- 开发语文课程资源的几条途径 / 王慧丽
- 迁移在语文学科中的运用 / 彭旭升
- 如何让古诗教学充满灵秀之美 / 韩海霞
- 自主学习方法设计 / 布丽榛
- 初中语文个性化教育初探 / 黄 祚
- 一堂特殊的诗歌欣赏课 / 钟 文
- 多媒体在高中小说教学中的应用 / 韦远脉
- 浅谈初中生语文素养的培养 / 徐晓燕
- 诗歌综合性学习教学案例 / 黄国林
- 语文课堂应成为师生共唱的天堂 / 侯西法
- 上好高中语文第一课的自我尝试 / 徐小平
- 制约语文课堂活跃因素的心理学分析 / 金 砚
- 高中新课改对师生关系的期待 / 张 莉
- 以修辞学为视角上好《雷雨》 / 朱国娟 范兴信
- 探究式学习课堂模式的本质与原则 / 朱小灵
- 论诗之意境 / 谭 娅
- 苏轼词艺术特色例析 / 刘名新
- 论阮籍与魏晋玄学的关系 / 彭 闹
- 《毛诗正义》的注疏成就 / 谈春蓉 李 锐
- 欧阳修与苏轼赋的立意比较 / 季三华
- 解读海明威的死亡意识 / 范海侠
- 纳兰性德咏物词的情感色形 / 海 刚
- “美”字的起源及其初义研析 / 冯海玲 杨 莹
- 金庸及其侠义思想研究 / 田 伟
- 冯梦龙笔下婚姻中的女性形象 / 罗 荣
- 王安忆与张爱玲笔下的城市主题 / 倪 新
- 幸福是件俗事 / 卫宣利
- 艳遇 / 洪 晃
- 思想杂碎 / 朱铁志
- 跟我到草堂看望杜甫 / 丁启阵
-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语文教育 / 侯姝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