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07年第8期
ID: 93112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07年第8期
ID: 93112
以修辞学为视角上好《雷雨》
◇ 朱国娟 范兴信
一、引言
修辞一般指在特定语言环境下选择、组合语言形式、表达特定的思想内容以增强表达效果的言语活动,是具体运用调音、遣词、择句、设格、组织话语的各种修辞手段的活动。修辞学就是专门研究修辞现象的科学。修辞学知识是指修辞学这一领域里的知识。而我们通常所说的修辞手法,即修辞格,是从大量的自觉或不自觉的修辞手段或使用语言技巧概括并提炼出来的被人们承认或使用,又自然显现出来的比较固定的语言修辞格式,即语言语调的修辞手法,属于积极修辞。
修辞学本身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如语体类型,表达效果,修辞目的,辞章结构等等,在选择教学内容时,可关注其中一点,即明确教什么或用什么教,而后明确怎么去教。修辞学方面的知识能够拓展教师的视野,下面将以研析《雷雨》为例,为教师如何确定口语语体文本教学内容提供一些参考。
教学内容是在教学过程中创立的。钟启泉先生把教学过程中的文本分为两种:一种是相对于现成文献形式的文本,能够形成教学的媒介过程与习得过程基础的文本,诸如教科书文本,资料文本,学生所生产的报告文本,练习文本,同种媒体结合的文本;另一种是在教学沟通过程中所生产的种种文本,诸如板书、教授、对话、讨论、笔记、摘要乃至对学生的操作活动进行激励和发出的指令。这两种文本的结合生成了教学内容。钟先生认为第一种文本侧重于预设性,第二种文本倾向于生成性。教学内容是预设和生成的统一。
二、以交际对象把握人物性格
《雷雨》作为中国戏剧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教师在教学这篇课文时可根据言语环境的构成要素之一交际对象预设教学内容。《雷雨》故事以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为大背景,课文节选其中的第二幕。本文开篇的对话,交际对象是周朴园与四凤的妈。谈话涉及的对象是繁漪和鲁侍萍。课文中第一句是周朴园说“这是太太找出来的雨衣么?”周朴园把眼前的交际者定为下人,因为他把谈话所涉及的对象称之为“太太”。如果周朴园交际的对象是周萍或是周冲的话,他会说:“这是你们母亲找出来的雨衣么?”“不对,不对,这都是新的。我要我的旧雨衣,你回头跟太太说。”这是周朴园指令性的话语,他认为眼前的这个人应该是众多下人中的一个。从这一句话可以看出周朴园对繁漪的不满和指责,但在下人面前又不能表现得太明显,所以周朴园的话说得恰如其分。因为他意识到交际对象的身份是底下人。周朴园看到鲁侍萍站着不走,有点生气,“你不知道这间房子底下人不准随便进来么?”因为他不容许有任何不服从他命令的人,而当他得知眼前这个人是自己下人的母亲时,态度稍稍好转,“那你走错屋子了”,语气比先前有所缓和。当道破天机之后,周朴园得知眼前人竟是梅侍萍,交际对象转变为和自己有着千丝万缕联系,有着极其复杂情感的一个人的时候,周朴园下意识地非常严厉地说道:“你来干什么?”话语中带有斥责,有恐惧,有惊愕。面对同一交际对象,只因交际对象身份的转变,引起了交际者三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有命令式到淡漠到惊愕。
教师在设计这一部分教学内容时,可抓住交际对象身份的转换引发人物语言、神态、心理的变化为切入点来探究周朴园的性格特点。问题可设计为:周朴园面对不同交际对象身份,语言发生了怎么的转变?态度又发生了怎样的转变?请推测周朴园的心理变化。“交际对象”这一切入点是预设的成分,但它是动态生成过程的起点,又为动态生成设置了特定的程序,即按“交际对象”规定的方向进行探讨。教师对教学内容的预设是教师原有知识体系的外显。职前所受的修辞学知识是教师预设和生成的基础。在教学创生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正确把握“交际对象”这一要素,使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得以深化,使教学目标得以顺利实现。
三、以语言风格体察人物内心
语体是适应不同的交际领域、目的、对象和方式需要,运用全民语言而形成的言语特点体系,是运用词汇、语法、辞格、语音手段以及话语组织等语言材料,表达手段所形成的诸特点的综合体。语体风格是各种语体的言语特点综合呈现的言语格调。语体风格中最重要的两大类是口头语体风格和书卷语体风格。《雷雨》就属于口头语体风格。教师可根据口头语体风格的基调、特点来分析《雷雨》的语言特色。以下三种切入点可作为参考:切入点一:多变的语音;切入点二:简短灵活的句式;切入点三:即时多变的话语。
切入点一:多变的语音。《雷雨》(节选)开头到“你自然想不到侍萍的相貌有一天也会老得连你都不认识了”。这一部分中,“嗯”字出现了7次,“哦”字出现了16次,“哦”单独成句是有10次。“嗯、哦”高频率的单独成句是一个独特的现象。
鲁侍萍语气词单独成句的例子有:
周朴园:“那你走错屋子了。”鲁侍萍:“哦。……老爷没别的事了?”
周朴园:“三十年前,在无锡有一件很出名的事情——”鲁侍萍:“哦。”
周朴园:“窗户谁叫打开的?”鲁侍萍:“哦。”
鲁侍萍以“哦”字作答,单独成句的共有三处,皆以句号结果。对于侍萍投河这样一件大事,在鲁侍萍踏进周家大门的那一刻起,应是时时浮现在心头,为了压抑自己的情感,不至于失态,她尽量掩饰自己激动的心境,尽量使自己的话语中不透露出任何感情色彩,故而都以句号结尾。这几个句号的背后,是鲁侍萍内心痛苦的挣扎,她又想让周朴园知道自己的身份,又怕周朴园知道自己的身份。
周朴园语气单独成句的部分有:
鲁侍萍:“不敢说。”周朴园:“哦。”
鲁侍萍:“我倒认识一个年轻的姑娘姓梅的。”周朴园:“哦?你说说看。”
鲁侍萍:“听人说她生前是不规矩的。”周朴园:“(苦痛)哦!”
鲁侍萍:“大孩子就放在周公馆,刚生的孩子她抱在怀里,在年三十夜里投河死的。”周朴园:“(汗涔涔地)哦。”
鲁侍萍:“嗯,就在此地。”周朴园:“哦!”
“哦”字后带祈使语气又有疑问语气。当鲁侍萍表示“不敢说”时,周朴园只是象征性地说了个“哦”字,只表示一般的停顿。当鲁侍萍提到认识一个梅姓的姑娘时,周朴园有些惊奇,又急切想知道两者会不会是同一个人,故而“哦”字后带“?”。但当周朴园尘封的回忆被鲁侍萍开启时,他的内心既有微微的苦痛又有微微的羞愧。“哦!”字用来掩饰内心的震动。鲁侍萍关于孩子的叙述使周朴园仿佛回到了三十年前,内心又有怕自己的丑恶面目被揭开的恐惧,所以他汗涔涔地说了个“哦”。当听到侍萍就在此地,周朴园掩饰不住内心的慌乱与惊讶,“哦”急促而慌乱。
语气,语调,语速,语气词都可帮助体现人物的思想情感和内心情绪的波动。如对“哦,嗯,呢,么”等语气词的分析,对“陈述语气,疑问语气,感叹语气”的辨别都可作为教学内容的“用件”材料。选择教学内容时,教师可让学生分角色朗读课文,特别关注“哦”字在特定话语情境中的语气、语调、语速。可比较周朴园台词中单独成句的“哦”字后标点变化,体会“哦”字背后的人物心境的变化,从而分析周朴园的性格。有了修辞学知识的积淀,教学就不光停留于统领的诵读感悟,而能够抓住感悟的具体的切入点。
切入点二:简洁灵活的句式。人物对话中,交际双方都有一定的前提和背景知识,因此指称相当简洁,省略了很多不必要的成分。比如“什么?鲁大海?他!我的儿子?”这几句中,交际的参与者心知肚明,就不必指明鲁大海,就是那个矿场上闹得最凶的工人,鼓动矿工罢工的人。“什么?”“鲁大海?”两个疑问句后又转变为“他!”一个感叹句,接着“我的儿子?”又是一个疑问句。两次句式的转化,是一个心理转承的过程。周朴园对“鲁大海”这个名字,早有耳闻,却怎么也不会和自己联系在一起,现在居然证实是自己的儿子,他思索着鲁大海怎么会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自己的亲生儿子居然反对自己的父亲?!惊讶之余一时难以接受。教师可引导学生关注类似的句式如“哦,!(低声)是你?”,选择表达意思相同,但句型不同的假想句子,如“什么,鲁大海他是我儿子?”“你是侍萍?”体味这些句式所产生的修辞效果对理解人物性格有何帮助。
[##]
切入点三:体态语的表达功能。体态语也是口头语体风格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对体态语的关注可帮助教师深入挖掘文本的深层内涵。体态语包括手势,动作,表情等等。《雷雨》中,周朴园与鲁大海冲突那一段(周朴园在桌上找电报……大海被仆人拥下,侍萍随下。)鲁大海(怒)、(笑起来)、(如梦初醒)、(看合同,伸手去拿)、(切齿),均表现了他对周朴园伪善、丑恶面目的清醒认识。怒是鲁大海对不公平待遇的反抗,他试图争取属于他们的权利。切齿是对周朴园罪行的控诉,是对争取权利的绝望。体态语是戏剧作品教学中易忽视的方面,但它是人物内心情感最外露的表现形式。所谓“喜形于色”,教师可设计体态表演引导学生走进角色,使学生在表演中感知人物内心,在表演中创造更多的教学内容。
教师对语体风格的预设精心但不精密,为教学的生成有足够的空白。当学生朝教师指引的方向与文本接触时,会碰撞出更多思维的火花。在学生与文本,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生的多元沟通交流中,教学能创造出更多有价值的课程资源。在朗读、比较、表演等一系列教学活动的预设中,学生成了教学过程的主体,成了教学内容的创生者。在教学内容的预设和创生过程中,学生发展了自由个性,重构完整的人格。
四、以话语分析体味言外之意
话语分析是现代修辞学的一个重要课题。运用话语分析知识可突破文本的表层含义,体会文本的言外之意。钟嵘在《诗品》中就提到过“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吕叔湘先生也说过:“修辞所说的‘比喻’、‘借代’、‘反语’等等都是这种‘言在此而意在彼’的例子”。《雷雨》虽以浅易的对话组织全文,但仍是话中有话。对话与对话之间要遵循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而话语偏离了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就有可能产生言外之意。合作原则是指质的原则、量的原则、关系原则、方式原则,即根据特定语境和对象说什么,说多少,为什么说和怎么说的原则。如:
鲁侍萍:“她遇人很不如意,老爷想帮一帮她么?”周朴园:“你先下去吧!”
按照关系原则,周朴园的回答应该是帮或者不帮,而这里周朴园却是示意鲁侍萍离开,这里违背原则的对话使这一话题中断,周朴园的言外之意是“到此为止,不要再继续这个话题了,我不想提这个人了。”再如:
鲁侍萍:“老爷,那种绸衬衣不是一共有五件?您要哪一件?”
周朴园:“要哪一件?”
鲁侍萍:“不是有一件,在右袖襟上有个烧破的窟窿,后来用丝绒绣成一朵梅花补上的,还有一件——”
鲁侍萍的话违背了量的原则。周朴园本来只是让她传达拿旧衬衣的事,鲁侍萍却添加了“一共有五件,有一件绣着梅花”等信息,这样的效果是暗示周朴园:我对你过去的事情知道得非常清楚,我是与你有这密切关系的人,可你却不知道。教师在处理相似的文体时以对话的原则为突破口,可以为教学设计提供更多关注的视角。此外,话语分析可还关注语篇的衔接。如:周朴园:你来干什么?/鲁侍萍:不是我要来的。/周朴园:谁指使你来的?/鲁侍萍:命,不公平的命指使我来的!话语中“来的”反复出现,使话语达到了很好的衔接效果!
对话原则、语篇分析的预设本身是对教师知识体系的考验。教师只有在精通修辞学知识的前提下才能设计切实可行的教学内容。教师预设教学内容的过程,是自身知识结构的成长过程,也是对教学过程的预设与课堂教学生成的准备过程。
五、小结
(一)修辞学知识是教师选择教学内容的理论依据,对教学过程的实践操作具有指导意义。
教学内容回答了“实际上需要教什么”和“实际上最好用什么去教”的问题。语文教学内容既包括教师在教学中对现成教材内容的运用,也包括教师对教材内容的“重构”,既包括对课程内容的执行,也包括在课程实施中教师对课程内容的创生,是预设和生成的统一过程。教师如何选择教学内容,从哪些方面入手,这是教师知识体系的问题。修辞学知识涉及到语言学知识体系中的语言学、词汇学、语义学等方面的知识,以它们为基础并渗入到知识的内部。修辞学的知识以显性知识储存在教师脑海里,但在具体的课程实施过程中,教师可处理为隐性知识传递给学生,也就是不必给学生道明这部分是语音学的知识,那部分是修辞学的知识。
修辞学方面的知识可引导教师关注以往容易忽视的语言形式。除上文提到的切入角度外,教师还可从修辞手段(表现手段、描绘手段)、修辞方法(择语、调音、设格、谋篇)、修辞格(双关,借代、比拟、反复、夸张等)入手,体悟文章的内蕴,把握文章的风格。
(二)修辞学知识可丰富教师的知识体系,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
在教学环境相同,学生身心发展相近的情况下,课堂教学效率的优劣,教学的内容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如何选择、创新教学内容,教师的素质又是决定性的因素。教师的专业素养是教师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专业基础知识是专业素质的基层。修辞学知识是教师专业基础知识——语言学知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专业知识的提高,使教师更能有效地把握教学内容。丰富的修辞学知识开拓了教师的教学视野,改变以往陈旧的教学套路。聚合零散的修辞知识点,能以更宽广的背景重新审视教材。
朱国娟,女,浙江宁波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范兴信,男,浙江苍南县马站高级中学教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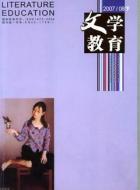
- 难忘的一件事 / 李 楠
- 思想的碎片 / 薛应平
- 话说杨志 / 刘正军
- 寝室文化与德育 / 桂艳溢
- 语文教学要留住学生 / 林运娟
- 拓展作业的五个空间 / 汤 蒙
- 自主学习是学好语文的关键 / 刘春才 胡善姣
- 新课程下的语文教学 / 黄 伟 叶春敏
- 应提倡语文教学生活化 / 张丽霞
- 语文情景教学例谈 / 来文玲
- 综合性学习与美育熏染 / 李光明
- 拓展语文学习的渠道 / 陈活兰
- 同理心是师生沟通的润滑剂 / 王丽霞
- 语文基础学段要重视养成教育 / 李密红
- 多媒体使语文教学更精彩 / 吴仲华
- 图书馆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阵地 / 赵伟达 高志刚
- 整合资源是校本开发的有效起点 / 刘方池
- 让学生自己站起来发言 / 吴鹏飞
- 从鲁迅作品看仿词仿句的妙用 / 刘伟琳
- 尝试训练型课堂教学 / 马永红
- 怎样培养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 / 康小曼
- 2007年安徽高考作文命题的现实背景 / 苏金文
- 2007年高考湖北卷作文答卷分析 / 吴红梅
- 职校作文教学方法谈 / 刘清明
- 手机短信创作十法 / 王爱红
- 写作教学的几点心得 / 李 丽 王章材
- 激发农村中学生写作兴趣的尝试 / 杨流德
- 作文教学须系统有序地进行 / 黄 兴
- 作文教学要充满人文关怀 / 刘振利 李善伦
- 指导中专生写好作文的实践与体会 / 曾晓芳
- 写作教学漫谈 / 洪 丽 龚玉华
- 下水作文的论争起源及主张 / 何 武
- 中学生应多读经典 / 杨佳君
- 从历史的角度再看焦母 / 杨英梅
- 关于幼儿教育的几点认识 / 王学玉
- 《心声》呼唤了怎样的新思想 / 印保群
- 对网络文学的整体认识与思考 / 刘玉有
- 语文教学要注重文化传承 / 骆怡龄
- 什么样的语文课才是优质课 / 原 野
- 透视当下网络文学 / 赵 燕
- 析《于园》山水之奇 / 周小辉
- 品《记承天寺夜游》的 / 程小芳
- 《断魂枪》主题解析 / 朱枝娥
- 《黄生借书说》的结构分析 / 李美芳
- 《琵琶行》中琵琶女的情感世界 / 杨晓莹
- 《行行重行行》诗意新辨 / 张守文
- 秦观《鹊桥仙》的情与爱 / 王力明
- 《长生殿》剧中杨玉环形象再析 / 张曼娣
- 《师说》搏海弄潮的对比艺术 / 李汉云
- 《雷雨》中繁漪的三种悲剧抗争 / 粟凤华
- 《蒹葭》的朦胧美 / 吴亚娥
- 阅读说明文方法谈 / 颜学凤
- 在朗读中培养学生的语感 / 姬永辉
- 让课外阅读成为学生的习惯 / 陈礼兰
- 巧用历史地图有效进行阅读 / 李建军
- 文学作品阅读技巧 / 张盛剑
- 网络时代的阅读教学 / 龙平波
- 中学外国文学课文阅读教学例谈 / 吴思思
- 用科学的方法进行阅读教学 / 王岩秋
- 高中学段怎样进行朗读教学 / 郑巧红 姜颖琳
- 语文课外阅读的实践与思考 / 张晓玲
- 阅读教学是培养语文素质的重要途径 / 王喜玲
- 语法切入法在文言文阅读中的运用 / 郑承猛
- 在阅读教学中如何让学生主动学习 / 罗小容
- 找回失踪了的阅读 / 葛友民
- 关于古诗词个性化阅读能力的培养 / 梁春燕
- 化整为零阅读方法初探 / 杨小丰
- 文言文三读教学模式探析 / 马红霞
- 让语文课成为挥洒激情的课堂 / 丛慧芳
- 开发语文课程资源的几条途径 / 王慧丽
- 迁移在语文学科中的运用 / 彭旭升
- 如何让古诗教学充满灵秀之美 / 韩海霞
- 自主学习方法设计 / 布丽榛
- 初中语文个性化教育初探 / 黄 祚
- 一堂特殊的诗歌欣赏课 / 钟 文
- 多媒体在高中小说教学中的应用 / 韦远脉
- 浅谈初中生语文素养的培养 / 徐晓燕
- 诗歌综合性学习教学案例 / 黄国林
- 语文课堂应成为师生共唱的天堂 / 侯西法
- 上好高中语文第一课的自我尝试 / 徐小平
- 制约语文课堂活跃因素的心理学分析 / 金 砚
- 高中新课改对师生关系的期待 / 张 莉
- 以修辞学为视角上好《雷雨》 / 朱国娟 范兴信
- 探究式学习课堂模式的本质与原则 / 朱小灵
- 论诗之意境 / 谭 娅
- 苏轼词艺术特色例析 / 刘名新
- 论阮籍与魏晋玄学的关系 / 彭 闹
- 《毛诗正义》的注疏成就 / 谈春蓉 李 锐
- 欧阳修与苏轼赋的立意比较 / 季三华
- 解读海明威的死亡意识 / 范海侠
- 纳兰性德咏物词的情感色形 / 海 刚
- “美”字的起源及其初义研析 / 冯海玲 杨 莹
- 金庸及其侠义思想研究 / 田 伟
- 冯梦龙笔下婚姻中的女性形象 / 罗 荣
- 王安忆与张爱玲笔下的城市主题 / 倪 新
- 幸福是件俗事 / 卫宣利
- 艳遇 / 洪 晃
- 思想杂碎 / 朱铁志
- 跟我到草堂看望杜甫 / 丁启阵
-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语文教育 / 侯姝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