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4年第2期
ID: 421063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4年第2期
ID: 421063
魏晋乐府诗的音乐文化探析
◇ 陈曦泽
摘要:本文关注的是魏晋时代的音乐文学——乐府诗。魏晋乐府诗在音乐文学史上具有变革的重大意义。本文对魏晋乐府诗的文献著录情况及特点进行深入考察,对魏晋乐府诗的现状、歌辞类别进行相关的统计、补录及分析,并对魏晋乐府诗文献著录所反映的复杂问题进行必要的考辨、分析。
关键词:乐府诗 文学 音乐
一、魏晋乐府诗现状分析
古典诗词是我国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它包含着丰富的人生意蕴,体现了高雅的审美情趣,达到了高超的艺术境地。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诗的国度,歌诗始于吟唱,吟唱即须依乐。吾国诗歌,与音乐之关系,至为密切,盖乐以诗为本而诗以乐为用,二者相依,不可或缺。文献学研究是魏晋乐府诗音乐与文学研究展开的重要基础。前人在这方面已经取得过不少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对魏晋乐府诗的辑录、选释、考订等诸多方面。郭茂倩的《乐府诗集》无疑是一部乐府歌辞的集大成之作,但是《乐府诗集》所收录的是历代相沿而见诸文献的乐府诗,而实际上魏晋时代的某些乐府诗在流传过程中,因各种原因失传、缺佚的现象十分严重。
如果要对魏晋乐府诗进行全面研究,首先须将魏晋所有乐府诗的创作情况尽可能客观、全面地复原出来。从西晋苟勖《苟氏录》、崔豹《古今注》、无名氏《歌录》、刘宋张永《元嘉正声伎录》、萧齐王僧虔《大明三年宴乐技录》、梁沈约《宋书·乐志》、陈释智匠《古今乐录》、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等相关文献中,我们仍可补辑部分缺佚的魏晋乐府诗题或曲名。例如:相和歌辞中的清调曲:武帝《董逃行》“白日”。魏武帝曾作有《董逃行》“上谒”歌辞,见于《苟录》、王僧虔《技录》,后失传。
二、魏晋时期乐府诗的主体研究
宋代郭茂倩认为:“自黄帝以后,至于三代,千有徐年,而其礼乐之备,可以考而知者,唯周而已。”传说中的夏、商、周三代的乐舞,尤以周代乐舞对后代乐府发展的影响有直接、深远的意义。周王朝十分重视礼乐建设,它承接殷商旧制,建立了中国古代史上第一个宫廷雅乐乐舞体系和制度。周朝从公元前1058年便开始制订礼乐计划,主要内容包括如下三方面:
第一,在礼乐的行政管理方面,设立了专门的乐舞机关—“大司乐”;第二,重视乐舞的教育作用,规定世子和国子从13岁至20岁期间,必须循序渐进地掌握有关音乐美学理论、演唱艺术和舞蹈艺术方面的知识和技能;第三,礼乐表演方面建立起正统的宫廷雅乐体系。
此外,周代的民间主要分成散乐和四夷乐两种。散乐是俗乐与戏弄、杂技的配合。四夷乐是王朝周边各族的乐舞。当时的乐舞机关甚至设立了专门管理外族乐舞的官员。由此可见,周王朝对四方外族的乐舞已经相当熟悉,并且已将外族乐舞用于宗庙祭祀和宴饮娱乐之中。
周代的雅乐体系包括了后代的郊祀乐舞、宗庙乐舞、燕射乐舞和鼓吹乐舞等。自此以后,历代历朝都十分重视礼乐建设,并且仿照周代建立本朝的雅乐体系。汉代也不例外。继承周以来礼乐建设的成果和范式,仍然是汉乐府创作的基本主题。除了已见的汉乐府创作都是郊庙祭祀内容之外,我们在讨论汉乐府时常用到《汉书·礼乐志》中记载:
(武帝)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斌,略论律吕,以和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圈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
后人常用它来讨论汉乐府采集诗歌的民间性质。根据张永鑫先生《汉乐府研究》的解释:“夜诵”一词中的“夜”是因汉时祀太一尊神祭典由昏夜至明而得名;“诵”则是音乐术语,意为“独奏”。所以“夜诵”是指专门祀太一尊神的祭歌独奏者。《汉书·礼乐志》提到的采诗制度,与古代采诗制的缘起不同,它是在先代雅乐曲调并未传世的情况下,只能从民间各地采集曲调以配古辞。而司马相如等人创作的乐辞,因“多尔雅之文”,过于艰深古奥,连通一经之士都不能完全领会歌辞,所以难于理解,难于合乐。于是,有必要对文人乐辞加以挑选方能入乐。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称得上是“采诗”。因此,张先生从汉武帝“定郊祀礼”取辞合乐的两个途径来得出结论,古代采诗是采集民歌怨刺之诗,而汉初的“采诗”却是创制内容典雅,改造民间曲调的新雅乐;汉武帝时的乐府并不是一个完全以采集、搜集民歌为主要职能的机构,西汉乐府的制礼作乐大多与民歌无关。
秦统一六国之前,古代的雅乐便已经衰落,俗乐已经拥有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并且达到了相当发达的程度。俗乐得到了当时统治者和儒家的重视和提倡:
至于六国,魏文侯最为好古,而谓子夏曰:“寡人听古乐则欲寐,及闻郑、卫,余不知倦焉。”子夏辞而辫之,终不见纳,自此礼乐丧也。
今之乐,犹古之乐也。
夫击瓮叩击,弹筝搏稗,而歌呼呜鸣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甲击击瓮而就郑、卫,退弹争而取韶度,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类。
考察两汉郊祀礼受到重视的原因,它主要是迎合了汉代统治者巩固政治的需要。汉初推行“黄老之学”,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汉高祖刘邦在建国之初曾向陆贾询问治国之道,陆贾认为新朝应该吸取赢秦速胜速亡的经验和教训。“高祖时,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可以推测,西汉的礼乐建设应该包括了吸取秦代礼乐文化的成分。而后来武帝接受儒生董仲舒的建议,大大加强了礼乐制度的建设。
西汉的乐府自武帝兴盛以后,延续数百年大体仍遵从其旧制。至东汉明帝时,改称郊祀乐为“大予乐”,负责郊祀乐的乐官改称为“大予乐令”。至此,大予乐仍是东汉雅乐的主体。
值得一提的是,对当时的音乐起到促进作用的还有东汉乐府的“举谣言”制。“举谣言”制据《汉书》、《后汉书》记载,开始于西汉末王莽时代。朝廷派出使者到民间推行皇帝的恩德,询问民间的疾苦,以此考察政教得失,行险官吏。平民百姓也借此机会,利用歌谣的形式倾诉自己的喜怒哀乐,展现百姓们生活中美丑善恶的标准,所以《宋书·乐志》所载的街陌讴谣大多出自东汉的民间乐府,这不能不说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综上所述,汉代的音乐文学创作基本服从传统的礼乐精神,其主体是雅乐。
三、结语
综上所述,魏晋时代,各家思想竞相齐放,层出不穷,人的本性和生命主体意识得到了充分的张扬,使得乐府诗能够获得公开认可和传播。乐府诗呈现出文人化和娱乐化的倾向,这是音乐文学体现在文化上的特点。乐府文人化的趋势是在文人介入了音乐文学创作以后才发生的文化现象,也是文学剥离音乐,独立发展的显著表现之一。作为文学作品的乐府诗在内容上成为了士子们立言写志的载体;形式上趋于齐整。古代先人们经历了从天神崇拜、祖先崇拜到人性觉醒,一路走来,至此,乐府诗能与人的心灵契合,是更本质的特性。
参考文献
[1](宋)郭茂倩.乐府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黄欣华.谈古典诗词教学的切入点[J].语文建设,2004(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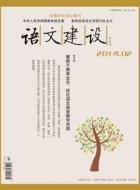
- 柳州方言“得”的用法 / 易丹
- 《百万英镑》写作手法与创作背景探究 / 史雅坤
- 莫里森《宠儿》“异化”母爱意蕴探析 / 向国华 阎莉
- 解读《小妇人》中女性人物的写作特点 / 王欣欣
- 浅析唐诗中的女子球类运动 / 代万雷
- 启蒙认知的思想观念下解读英美文学 / 刘曼琳
- 魏晋乐府诗的音乐文化探析 / 陈曦泽
- 论先秦诸子语用观 / 梁燕华
- “火星文”的结构类型及其对规范汉字的影响 / 李丽群
- 固原方言的反复问句 / 高顺斌
- 符号学视阙下的语言模糊性探源 / 翁向华
- 网络语对大学生语言的异化蠡测 / 孔瑛
- 连词“就算”的形成 / 韩启振
- 跨文化交际在语言教学中的重要性的研究 / 张俊伟
- 语块理论与语言表达的相关性研究 / 沈娟 王冬梅
- 语言变异的概念整合阐释 / 马娟
- 四行诗集《鲁拜集》的翻译浅析 / 晋剑琴
- 我国明代体育活动的文学管窥 / 敬文
- 文学作品中民间音乐初析 / 孟昆
- 当代体育文学价值观念定位的思考 / 于秋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