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建设 2013年第12期
ID: 358703
语文建设 2013年第12期
ID: 358703
写作的界限与自由
◇ 成旭梅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指向高考的写作不再是独抒性灵的凭借,而是精神遭遇作文律令绑架的、并非触动真实内心的、隔靴搔痒的“伪表达”。
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吴义勤曾说,现在中国的文化环境还是相对比较宽松的,文化的自由带来了言说的自由。《南方周末》(2008年12月9日)亦提出类似的看法:1998年中国思想学术界最值得注意的景观之一,是自由主义作为学理立场的公开言说。这足以说明,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或者大的文化环境阻碍了学生自由写作、真实表达。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一、高中写作面对怎样的界限
我们先来思考这个问题:高考出题者与阅卷者究竟看重什么?
摘取周宏老师(上海高考语文阅卷中心组负责人兼作文组大组长)近年谈高考作文中的系列言论如下:1.真实有品位;2.材料作文勿因审题而满盘皆输;3.考场作文,四平八稳还是标新立异?4.“不限文体”不是写“四不像”作文;5.提高高考作文的思辨力。[1]
以上导向大致可形成这样的高考写作的身份再认:高考写作是一个在技术上很容易框限,而在思想上、艺术品质上很难品评并规约的对象;高考命题存在一个居高临下的成人视阈,因而在精神气质、叙事模式上呼唤写作的跨龄同构。写作命题作为成人的期待与命令,对高中生写作所形成的言说的绝对界限是不言而喻的。
除此而外,高中阶段写作中的“伪表达”还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新课程标准写作要求的模糊性。《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中的写作要求是大而化之的,更缺乏具体可操作的方案,这直接导致了一线写作教学无措又无序的状态。
第二,高考写作“真实”的定位定性问题。高考写作的“个性化”与文艺领域的以虚构为本质的“艺术的真实”是有着霄壤之别的;高考写作的真实又不等同于日常生活的绝对真实,它应与实用写作、功利写作有着本质区别,且对平面的生活有所超越。
第三,书写观的裂变与冲突。传统写作的“文以载道”书写观对高考写作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而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为人生”“向内转”的现代书写观与传统写作书写观产生了巨大裂变,并在长时间内形成牵掣。
以上错综复杂的原因所构成的框限与不明,使得学生写作成为规定动作下的受限行为,从而使学生进退失据以致失语。
二、我们可以拥有怎样的自由
如何拯救失语了的高考写作?我的看法是:高考写作——内部语言的适度示现。
提出这个看法是基于两个理论依据:文艺生产原理与创作的心理机制。文艺生产的一个重要原理是四维创作论,基于这个理论,读者对世界的反映首先源自内部映射,不是源自外在意义;而心理学家A. P.鲁利亚指出:“内部语言体现了言语主体的强烈欲望和需求,充满了言语者浓厚的情绪和情感,黏附着言语者丰富的心理表象和意象,蕴含着语言的充沛的生殖力。”[2]
认识到一个言语主体的内在书写力量,我们就不会自以为是地去按照自己的意愿或是随时摇摆的评改标准去改变学生,我们就会在写作教学的过程中充满对学生本身表达个性的尊重,就会用“成全”的态度全力帮助他们成为最好的自己。
更进一步,在本质上,以内部语言来写作,所体现的是一种精神践行的能力,它呈现不同阶段、不同境界的人的精神真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拯救失去自由发言与真实发言的写作,就是拯救了人格。
以下分别以“内部语言”“适度示现”为主题词进行解说。
(一)“内部语言”对于写作的意义
1.内心秩序建构真实写作
写作基于语言学,写作却不只是语言学,叶蜚声先生指出:“文章属于语言研究的最高层面……近年来,‘话语分析’‘篇章语言学’的讨论甚嚣尘上,看来距作文法尚远。”[3]日本符号学家池上嘉彦亦提出类似的观点:“一般认为人类是构造化的动物,给自己的处境赋予某种意义和价值,并把自己所居住的世界秩序化,这就是把‘自然’改造成‘文化’的活动。”[4]他们不约而同地指出,写作是一种响应内心秩序的文化活动,是一种内心自由的极大张扬。正因如此,同样是写风景,不同人笔下的山水风物才会形态各异;同样是记人记事,不同的人对于同人同物的感知与辨识却判若云泥,这是因为生命个体有所差异,精神触觉有所差异。由是观之,无论是广义的文艺创作,还是狭义的高考写作,都必须遵从内心秩序的创生,否则,便失去写作的意义与价值。
马丁·海德格尔在论述语言的本质时这样写道:“语言是存在的家。”法国文学结构主义及符号学之父罗兰·巴尔特说:“语言既不反动,也不进步,它只不过是法西斯,因为法西斯不是阻止人说话,而是强迫人说话。”海德格尔和巴尔特共同的意思是,语言所呈现的是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在其时其境的感受,从某个层面上来看,即语言是个体生命内心秩序的外在呈示。
2.特定时空情绪体验呈现心灵走向
写作是对生活事件与心灵事件的书写,但在写作里,“事件”的定义是特殊的。诗人柏桦这样解释诗歌与事件的关系:“这些由特定情境下的‘事件’组成的生活之流,就是诗歌之流,也是一首诗的核心,一首诗成功的秘密,……‘事件’试图‘解释’了生活,‘解释’了某种人格类型,也‘解释’了时光流逝的特定涵义。”[5]在此,诗人强调了创作实际是特定时空下情绪作用于事件的结果。
金圣叹有“以文运事”说与“因文生事”说,他认为《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传》是因文生事,由此指出了历史叙事与小说叙事的界限:前者表明,历史不过是一种叙事话语,是与外部世界构成“毗邻性”关系的“转喻”世界;后者则表明小说实际上是借助写作法则建构而成,是与外部世界构成“相似性”关系的“隐喻”世界。这正说明文艺创作生态是根植于生存文化的写作,是时空情绪体验的结果;作者所追求、憧憬的理想的时空情绪就是自由生命的实现、自由生存的表征,是化而为文的核心力量。马正平说:“价值观念的评价是依据个体的理想性事物(时空情绪)而做出的。因此,作为评价标准的理想性事物(时空情绪)比评价本身更为先在,也更为本质、更为本体。”[6]
用材料来阐释一下我的这个观点。莫言曾因在《欢乐》里颠覆了国人经典“母亲”形象而遭遇乱箭齐射。对此,余华如此评价:“母亲的形象在虚构作品中逐渐地成为了公共产物,就像是一条道路,所有的人都可以在上面行走;或者是天空,所有的人都可以抬起头来注视。阅读者虽然有着不同的经历,对待自己现实中的母亲,或者爱,或者恨,或者爱恨交加,可是一旦面对虚构作品中的母亲,他们立刻把自己的现实,自己的经历放到了一边,他们步调一致地哭和步调一致地笑,因为这时候母亲只有一个了,他们自己的母亲消失到了遗忘之中,仿佛从来就没有过自己的母亲。”[7]
但在当下学校教育里,写作命题的真相是:写作命题更多体现为作为上一代的教师,单项命令与导引下一代的学生个体针对他们可能未曾经历的事、未曾窥见的物和未曾体验过的情开展写作。这种教学缺乏实际可体验的情境,也就难以使学生产生相应的时空情绪体验,于是,学生的实际写作只能沦为堆砌事例、机械议论、程式化结构的结果。长此以往,则不仅有害于其成文,更有害于其成人——因为,如果说时空情绪的体验具有一种亲身感受的自明性,那么生存与生命则是一个基于这种感性自明与理性反思的意义判断。
因而,教师在指导写作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创设生活感强烈的情境,还原学生生活感知,形成时空情绪体验是殊为必要的;在直接生活情境不可能创设的情况下,可尝试经由间接体验达成的方法,即阅读(文化)生成写作。这将在后面部分给出解释。
(二)内部语言的“适度示现”
卡西尔说,秩序有“一般的秩序”(时间的、空间的、因果的)和“更高的秩序”之分,“更高的秩序”就是“人类真正的生命力”的方向感、价值感[8],因而,强调内部语言在写作中的重要性,强调写作遵从内心秩序的创生,乃在强调它是事物价值的“合理性”感受、体验和认识,而不是随心所欲的宣泄或梦呓般的自诉。那么,怎样建立这种有规约的秩序、合理性的感受呢?这就需要有一个合适的度。
如何做到“适度”?笔者认为,文化的内在积淀是一个有效的途径,是规约心灵走向与提升写作品格的关键。
我们日常给学生提供的文学范式往往是生产艺术真实的大文化与大文本,可是一旦提到写作范式的时候,教师即刻改换了路子,推荐大量范文集作为提升写作能力的阅读材料。将范文集作为学生写作范本,是典型的经验主义。范文选可能在技法上解决学生写作难的实际,但这是一个短期作为;而大文化与大文本则是一种精神滋养,是由内而外的改变。
文化写作是一个方向性的选择,也是一个教师教学机智的表现。如果说时空情绪体验是写作生成的内在机制,那么积极的文化响应姿态则是形成写作品质的外在催化。
接下去的问题是,怎样实现大文化、大文本与高考写作的对接。所谓“文化写作”,就是要关注写作的人文性、文化味、书卷气,换句话说,叫“诗性写作”。“诗”的空间是很大的,往往带有象征、隐喻等文化跨越色彩,支撑“诗”的往往是哲学、哲理,是“诗”和“思”的结合。因此,我把文化写作称为“文明的对话”“哲学的对话”。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在写作创生中的同位刺激的功用,这就是对话;而文明的对话,不仅要与文明的生活对话,更重要的,是与文明的文本生态对话——一方面,引导学生与他人作品对话,以感受历史更替中的人性;一方面,又引导学生与自我作品对话,走向更深层的自我否定、自我否定之否定的超越。这样生成的写作,才是写作者主体建构的写作。
因此,文化写作与普通生活写作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对人的文化积淀与文化内省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写作,归根结蒂是“我”的发言,而积极的文化响应姿态,则使“我”的发言更具品格。因而,如何企及“适度”的情感与美,是优质文化与哲学存在于写作,也是优质文化与哲学存在于人类的意义之一。文化写作的深度要求,是在哲学的引领下,带着哲学理性的心灵的自我适度约制;也是心灵在优质文化和哲学的引领与净化下获得的无限自由的可能性,是精神践行者的高蹈姿态。
综上而观,“高考写作——内部语言的适度示现”基本要义为:内部语言的被许可,意味着对人的真实和自由权利的基本尊重;适度,则意味着对自由的德性规约,意味着自由之审美意义的实现。
参考文献
[1]周宏.高考阅卷组长教你写作文[N].文汇报,2010-12-10至2011-1-20,各期第10版.
[2]转引自刘胜利.语言的痛苦蜕变——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综述[J].当代小说(下),2011(4).
[3]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3..
[4]池上嘉彦.符号学入门[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1985:133.
[5]柏桦.谈诗歌中的事件//今天的激情——柏桦十年文选[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99.
[6]马正平编著.高等写作学引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77.
[7]余华.谁是我们共同的母亲[J].天涯,1995(6).
[8]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1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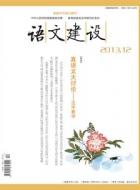
- 卷首 / 佚名
- 从文化的视角教学汉字 / 李金云 李胜利
- 培养逻辑理性的三种策略 / 吴格明
- 真语文须明辨的几对关系 / 黄厚江
- 把握小说解读的层次与视角 / 付煜
- “比喻论证”还是“比喻说理”? / 于军民
- 文学鉴赏要有文体意识 / 范松义
- 写作的界限与自由 / 成旭梅
- 语法教学缺位不容忽视 / 苗蔚林
- 草原之美,因人而迥异 / 孙绍振
- 文化场域下的多元解读 / 张明琪
- 情感的节制和情节的空白 / 周致吟 詹丹
- 描“天然”本色,抒“英雄”气概 / 方麟
- 谈《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的婉约风格 / 陈洪娟
- 语病设置不能走向误区 / 杨帆
- 说说“儿戏不如的供料作文” / 黄佳铭
- 黎锦熙的近代语文教育研究 / 范桂娟
- 近30年小学语文寓言教学研究综述 / 张青民
- 一道数学竞赛题中的语文问题 / 王灿龙
- “北漂”之“北”及其他 / 李云龙
- 语文课质疑与探究的走向 / 佚名
- 立人:语文教学的必然担当 / 佚名
- 推进植根于汉语泥土的语法研究 / 邢福义
- 语文教学要抓住两个“根本” / 刘仁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