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建设 2013年第12期
ID: 358702
语文建设 2013年第12期
ID: 358702
文学鉴赏要有文体意识
◇ 范松义
一
中国古典文学历史悠久,文体种类也极为丰富。不同的文体,语言、结构、体式、表达、题材、格调等互不相同。古人也有强烈的文体意识。早在三国时期,曹丕就曾说过:“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典论·论文》)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也说:“文辞以体制为先。”他们都对文体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古代作家在创作时,会有意识地选择恰当的文体,以更好地表达思想、情感,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写作目的。
既然如此,在阅读古典文学的时候,读者亦应有鲜明的文体意识。面对诗、词、曲、散文、小说等不同的文体,显然应有不同的接受模式,如此方能更好地接受、解读、阐释作品。反之,若缺乏文体意识,阅读就容易千篇一律,不能真正地贴近对象的本质。若是文体相差较大,这个问题尚不明显;若是文体比较接近,问题就比较突出了。
在某种意义上,“写什么”对作家固然重要,而“如何写”就更为重要。我们要关注作品写了什么,更要关注它是如何写的,这才是鉴赏的重点所在。不同的文体,设置了种种不同的规矩,以提醒、约束作家如何表达。这种不同并不仅仅在于外在体式的不同,更多、更重要的是内在的文学精神。不同文体、不同类型的作品,有不同的读法,有不同的评价标准。读者阅读古典文学作品,一个重要目的是培养审美、鉴赏、分析与评价作品的能力。如果缺乏文体意识,显然不利于这些能力的培养。像有着血缘关系的诗、词、曲,由于文体类似,读者在接受中文体意识缺失的问题就更严重。本文针对此,试对文体间的不同展开讨论。
二
诗、词、曲同属韵文,属于广义上的诗歌,同时又有各自的文体特征。我们有时虽然也会注意到其中的区别,如词有词牌、句式为长短句,形式与诗歌不同,但对文体间真正的不同并不在意,甚至可以说并不明了。无论面对何种文体,鉴赏模式并无本质区别,总是背景、意象、意境、修辞、技法等,根本不涉及对象的特性。如此这般,仿佛诗、词、曲完全是一种文体,那么它们在文学史上何必独立存在?我们读诗、读词与读曲又有何区别?又如何体验不同文体的独特美感?
这种对文体有意无意的忽视,自然会造成鉴赏的不到位。如果独立分析一首作品,诗也好,词也好,曲也好,若是写情,则常说直抒胸臆、托物言志等;若其中有景,则张口即是“情景交融”;若是咏史,借古讽今、深沉的历史感等话语又极为常见。若是论及语言,则无非优美、动人、流畅等。这样的赏析当然不能算错,但过于套路化、表面化。实际上,即使同是写情,诗与词并不一样;同是咏史,同样采用借古讽今,词与曲也不一样。
至于诗、词、曲三种文体的差别,形式上固然很明显,而更多的表现在内部,这才是本质的不同,是我们在鉴赏中所应特别注意的。
从美学风貌上看,诗体典雅、庄重,而词体委婉、柔媚。明李东琪谓“诗庄词媚,其体元别”(清王又华《古今词论》引),见解极为精辟。这里可将杜甫《羌村三首(其一)》与晏几道《鹧鸪天》相比较。《羌村三首》云:“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鹧鸪天》云:“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拚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杜诗写战乱之中的夫妻相逢,风格浑厚沉郁。晏词写自己与早年相识的歌女重逢,风格则婉约娇媚。尤其“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本是从杜诗“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化出,而二者风格之差别极为明显。与诗词相比,曲体则显得通俗质朴。如关汉卿《沉醉东风》写离情别绪:“咫尺的天南地北,霎时间月缺花飞。手执着饯行杯,眼阁着别离泪。刚道得声保重将息,痛煞煞教人舍不得。好去者,望前程万里。”明白如话,浅近通俗。
从风格上看,诗体直白含蓄皆有,词体更重委婉,曲体则追求直率。词如柳永《八声甘州》云:“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栏干处,正恁凝愁。”由人到己,又由己到人,婉转动人。即使是豪放之作,笔法也崇尚曲折,忌直露。如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即深沉蕴藉,非一般粗浅之作能比。曲体则最忌曲笔,反以明快显豁为美。如王磐《朝天子·咏喇叭》云:“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儿大。官船来往乱如麻,全仗你抬声价。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哪里去辨甚么真共假?眼见的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只吹的水尽鹅飞罢!”自然酣畅,可谓直率。
从语言上看,诗体语言典雅,从词到曲则显示出口语化的趋势。比如写孤独感,杜甫《登高》云:“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而李清照《声声慢》云:“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像开始的叠句以及“怎生”“这次第”这样的语言,在诗中尤其是近体诗中,就不多见。至于曲,则大量使用口语。试读睢景臣《哨遍·高祖还乡》:“社长排门告示:但有的差使无推故。这差使不寻俗,一壁厢纳草也根,一边又要差夫,索应付。又言是车驾,都说是銮舆,今日还乡故。王乡老执定瓦台盘,赵忙郎抱着酒葫芦。新刷来的头巾,恰糨来的绸衫,畅好是妆么大户。”再读关汉卿《一枝花·不服老》:“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槌不匾、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其口语化的特色极为明显。
由此可见,即使是较为接近的诗、词、曲,其文体间的区别也很明显。同一作家,从事不同文体的写作,会有意识地区分主题、内容、情调。如南渡之后,李清照目睹国土沦丧,痛恨当局苟且偷安,希望能够恢复中原,作有《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作者表达对历史、人生、现实的认识与体悟,慷慨激昂。而在《武陵春》一词中,李氏写道:“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这里所写更多的是一种深沉的悲苦之情。诗、词之别,清晰可见。我们在鉴赏作品的时候,自然就不能采取固定的模式,而应注意其文体特征,挖掘出各自的独特性。
三
关于作品鉴赏中的文体意识,还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
一是在某一文体内部,又有更细的文体划分,则“小文体”间又有区别。刘勰《文心雕龙》曾说:“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其区分就相当细微。在诗歌中,《诗经》和《楚辞》不同,乐府诗和文人诗不同,古诗和律诗不同。同时,四言诗和五言诗不同,五言诗和七言诗又不同。在文章中,骈文、散文各有不同。在散文中,哀祭、尺牍、碑志、序跋、杂记等,也各有不同。在赋中,大赋、小赋、文赋、律赋,同样各有不同。同时,某一种文体,在不同的时代,其特点也会有不同。比如诗分唐宋,自南宋至今众说纷纭。钱锺书《谈艺录》云:“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二家所云可谓真知灼见。唐诗主情,宋诗主理,唐宋诗风之不同即由此决定。若以花作比,唐诗如牡丹而宋诗如梅花,前者丰腴而后者瘦劲。若以景作比,唐诗如天然山水而宋诗如人间园林,前者具自然美而后者具人工美。那么在鉴赏中,显然鉴赏的方式、关注的重心都会有区别。如果拿同样的评价方式来衡量所有的文学作品,那么既不能给予作品以准确的评价,也不能贴近作品的本质。
二是文体间的渗透。不同文体各有特色,但也并非壁垒分明,而是互相借鉴、互相影响,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极为常见。我们鉴赏时,对于这种现象,就应注意其中的新变。比如宋词有“以诗为词”“以赋为词”“以文为词”,即属此类。辛弃疾词即是“以文为词”的代表。“以文为词”的内涵也很丰富。如辛氏《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这是对话体,对词体来说就是一种革新。再如《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云:“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这种句式较为松散,语意连贯,意脉流动,不同于传统诗词意象密集、结构跳跃的语言特点。又如《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云:“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作者运用典故,告诫执政者要铭记历史,不要草率从事,以免重蹈古人覆辙,落得“仓皇北顾”的下场。这实际上是在发表议论。词体本多抒情,在词中议论说理者甚少,自稼轩起始突破常规,大发议论,将本应该写入散文的内容置于词中表达。诸如此类,如果我们不加注意,只是按常规分析其字、词、句、典故、结构等,显然就不能真正读懂作品。
其实,不仅古典文学的鉴赏需要文体意识,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的鉴赏同样如此。应该说,这是文学鉴赏中的一个普遍问题。
参考文献
[1]彭定求等.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2]唐圭璋.全宋词[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隋树森.全元散曲[M].北京:中华书局,1991.
[4]郭绍虞.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5]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6]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7]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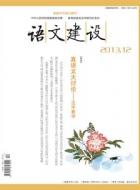
- 卷首 / 佚名
- 从文化的视角教学汉字 / 李金云 李胜利
- 培养逻辑理性的三种策略 / 吴格明
- 真语文须明辨的几对关系 / 黄厚江
- 把握小说解读的层次与视角 / 付煜
- “比喻论证”还是“比喻说理”? / 于军民
- 文学鉴赏要有文体意识 / 范松义
- 写作的界限与自由 / 成旭梅
- 语法教学缺位不容忽视 / 苗蔚林
- 草原之美,因人而迥异 / 孙绍振
- 文化场域下的多元解读 / 张明琪
- 情感的节制和情节的空白 / 周致吟 詹丹
- 描“天然”本色,抒“英雄”气概 / 方麟
- 谈《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的婉约风格 / 陈洪娟
- 语病设置不能走向误区 / 杨帆
- 说说“儿戏不如的供料作文” / 黄佳铭
- 黎锦熙的近代语文教育研究 / 范桂娟
- 近30年小学语文寓言教学研究综述 / 张青民
- 一道数学竞赛题中的语文问题 / 王灿龙
- “北漂”之“北”及其他 / 李云龙
- 语文课质疑与探究的走向 / 佚名
- 立人:语文教学的必然担当 / 佚名
- 推进植根于汉语泥土的语法研究 / 邢福义
- 语文教学要抓住两个“根本” / 刘仁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