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建设 2008年第2期
ID: 81203
语文建设 2008年第2期
ID: 81203
论课文教学化的意义与实现
◇ 黄华伟
课文要想在教学中真正有效地发挥作用,就必须教学化。这个过程可通过读者化、语文化和课堂化三个阶段来实现。这里的课文,主要指文学类文章。课文教学化即教师、学生根据实际情况对课文做出使之符合教学要求的理解和处理。
一、课文必须读者化
“……要使它(文学对象)显现出来,就需要一个叫做解读的具体行为,而这个行为能持续多久,它也只能持续多久,超过这些,存在只是白纸上的黑色符号而已。”〔1〕(萨特语)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读者有权怀有某种骄傲,因为他把作品提升到了它的真正存在”。〔2〕而我们语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是:我们一直以来没有意识到或不敢认为自己是课文读者,我们很少把课文当做可以由读者(教师和学生)来解读的作品。
1.课文必须教师化
新课程的意义之一体现在教师不再是教“课文”而是教“他自己的课文”。诚如王栋生老师《不跪着教书》序言里所说的那样:“想要学生成为站直了的人,教师就不能跪着教书。如果教师没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他的学生会是什么样的人?……就觉得我们中国首先得有铁骨教师,教育的辞典中才配有‘铸造’这样的词条。”〔3〕也正如《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教学建议”中所说的:“教师……在教学中,要合理使用教科书和其他有关资料,充分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
这就要求语文教师对课文有自己的判断。套用一句话,对于具体课文,我们除了“照着讲”,即准确传达课文的原有意思外,还要“接着讲”,讲得比课文更有针对性、更新鲜、更透彻;意犹未尽时,还可以从讲课文到“讲我”,脱出课文的窠臼,创造性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和看法。当然,最好是能引发学生“讲”。学生只要肯讲、能讲,都是好的。学生对课文的读者化,应该是最有意义的。这就要考验教师的思想修养和学识、水平了。
比如,对《祝福》中“杀死祥林嫂的凶手到底是谁”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对传统看法提出疑问:是鲁四老爷吗?鲁四在小说中其实不过是个稍有家财的乡间小地主,虽然思想守旧,对祥林嫂也很冷漠,但说是他杀死了她,实在是夸大了他的作用;相反,倒是他给祥林嫂提供了帮佣的机会,收留了她,使她有机会“白胖”起来。是封建礼教吗,比如“三从四德”之类?祥林嫂虽然深受其害,也拼死维护过它,但在头上撞了个大洞之后,却也平安地活下来了。是夫权吗?祥林自然没有迫害她,贺老六对她也很好。那是族权吗?她婆婆虽然绑了她卖了她;阿毛死后,祥林嫂的大伯虽然夺走了她的房子,但还不至于让她走上绝路。那么,究竟是什么害死了她呢?——神权,准确地说是迷信思想,是愚昧,是柳妈的一番“鬼话”把她吓死了,所以小说开头写到她第一个要问的就是有没有“魂灵”——这才是她的死因。鲁迅固然是反封建斗士,但他更是一个启蒙主义思想家。当然,我还认为阿毛的死对她精神的死亡也有很大作用:一个女人,在这世上爱无所爱,何以堪?尤其是在有过美好的生活和爱之后。
2.课文必须学生化
如果我们想真正体现对学生的尊重,突出他们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就不应该剥夺他们解读课文的权利。也就是说,学生之所以长期以来没有读者意识,都是我们教的。其实越是好的作品,其内涵意义越是常读常新,我们有什么权力让学生屈从于一元解读?虽然有人说教学阅读不同于一般的文学阅读,但如果从“一切从学生出发”的角度来看,学生存有不同见解是理所应当的,至于怎么使他们的阅读是“教学”的而不是“文学”的,我想,或者我们在教学中要做的,就是让学生的“一千个哈姆雷特”都是哈姆雷特,而不是其他人。
课文(主要是文学作品)本身就有不一般的艺术魅力,如果让学生真正有读者的权力和主体地位,就一定能激发他们的热情和兴趣,我觉得课文的许多趣味常常被我们“教”坏了。
比如,我在教《阿Q正传》时,让学生说说阿Q的形象,学生就能讲出许多不同的见解,也有一些新思想,其中一位学生是这样说的:“阿Q只不过是一块玻璃而非一面镜子,我们应透过他去看前面的路,而不是看那镜中的虚像。”
3.尊重作者和编者
沈德潜先生说,“有第一等的襟抱、第一等的学识,才有第一等的真诗”。我们的课文作者,大都是这样的“第一等”;而编者的眼界、见识也自有过人之处。对他们我们应怀有尊重之心,我们不能因为有了“课文读者化”的权力就随便对课文指指点点甚至任意曲解,更不可凭自己的主观臆断,妄下断语。我们要在充分读懂的前提下,做一些适当的教学处理。同时对学生的作用也应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有原则有分寸,他们是主体,有权力,但并不是任由他们瞎理解瞎处理。只有这样才能使课文读者化更加科学合理,不走向极端。
二、课文必须语文化
“语文教材中的选文,和一般文化课教材中的选文似乎没有什么区别,都分属于一般人类文化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比如《松鼠》属于生物学的领域,《赵州桥》属于物理学的领域,《苏州园林》属于地理学的领域。每一篇文章,都可以将它们归属到各自的文化领域。”〔4〕也就是说,我们的课文或为文学,或为哲学,或为历史,或为政治,或为地理,或为生物……几乎无所不包,它们都不是为语文教学而写的。换句话说,语文不像其他学科那样可以从自己学科内容中选取合适材料直接用于教学,我们并没有真正的“语文的”课文。可能正是这个原因,我们在上语文课时才会一不小心就上成政治课、文学课、历史课……而独独不是语文课。
1.课文必须言语化
“语文课程为了形成和发展学生的语文素养,学生的读写听说活动必须指向如何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而主要不是它们的内容。”〔5〕更明白地说,“在语文教学中,为了学习言语方式才需要学习义理内容,如果某一篇文章的义理内容十分简单,不会在学生学习言语方式时起障碍作用,那也就可以不必涉及义理内容的教学”。〔6〕从这个意义上说,语文就应该是言语的,至少“言语的”就是“语文的”重点,所以这里把“语文化”直接用“言语化”来替代。
我以为对已经经过9年正规语文教育的高中生来说,更应如此,无论哪一套教材中的课文,在思想内容的理解上,学生都不会存在大的困难。不论是经典的《祝福》《记念刘和珍君》,还是新入选的《我与地坛》《听听那冷雨》等,而且文章的言语水平也必须成为判断一篇课文教学价值高低的标准。
2.言语必须精细化
课文必须言语化说明了课文教学化的方向和内容,而言语的精细化则是课文教学化的方法和手段。否则,我们就有可能只停留在言语材料的表面,只知好差,却不能道出所以,从而学不到言语的精髓。例如史铁生《我与地坛》中有一句:“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说我家和地坛很近。但这还不够。“地坛离我家很近”暗含有从家里出发,去往地坛的意思。比如,我们从家里去学校,遇人问为何要步行,你就会说,因为学校离我家很近。如果是从学校回家,你可能就会说,因为我家离学校很近。一般不会说反了。所以,如果只说“地坛离我家很近”或“我家离地坛很近”就没有把作者和地坛的关系讲清楚,而如果改为“我家和地坛很近”,简则简矣,但意韵全失了。这样写就表现出两者是对等关系,暗示了情感上的契合,我想去,地坛也想接纳我,两者有不分彼此、互为主体、相互吸引的言外之意。“总之”是对前文的概括总结,但前文就只这两句,似乎还不值得“总之”,这透露出作者一言难尽,不想多说,或者觉得说不清楚,或者觉得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于是“总之”。“只好认为”不是无奈,而是庆幸、欣慰。“缘分”是佛家用语,和“只好认为”一起,显出一种大事已定般的平静心情,也显示出一种参悟人生后的通透境界。值得关注的还有两个句号,一般说来,在这样的语句中,应该用逗号才对,作者这样用,是认为逗号的停顿已不足以表达中间的许多内涵,非用句号不可;好像他写这几句时是一句一顿的,仿佛引发了他无尽感慨似的。
[##]
3.勿忘课文人文性
从上面的“咬文嚼字”中其实已经可以看出,关注言语表达不可能离开言语的思想内容,调整言语就是在调整我们的思维。就像在“课文必须读者化”中所举的例子,虽是思想内容上的读者化,但同时也必须是“言语的”一样。这里之所以还要提到这点,只是想说我们并没有忘记课文所蕴涵的人文内容,我们只是应该从语文的角度、从言语的角度入手。
三、课文必须课堂化
课文的读者化使课文变成了“我们的”课文,课文的语文化使课文变成了“语文的”课文,而它的课堂化则是要让课文变为“教学的”课文,从而最终完成课文的教学化。
1.课文必须现实化
课堂是个现实的存在,而课文“从编写程序看……无非是少数专家根据学生能力发展的有关调研、对教材的整体构架进行讨论和论证,对精心遴选的课文进行加工、编辑和再创造……”“不管专家们如何博采众长、深谋远虑,它终归只是一种有明显局限的主观意志。因此,编者意图不应该成为语文教学唯一的行动指南”。〔7〕也就是说,编者的课文和师生的现实是有距离的。我们一定要让课文适合学生,适合学生的认知水平、认知规律。即“语文教学内容的选择也不是由教材以某一个要素决定的,它还涉及学生认知发展阶段性的问题。因此也不可能是教材有什么我们就教什么、学什么,我们只能选择教材内容中与学生认知发展相一致的内容”。〔8〕“语文教材要让学生感兴趣、有用并与日常生活有关,应能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现实问题,能够让学生把学习教材课文与自己的现实生活感受结合起来,这样他们才有学习的愿望,否则学生感受不到时代气息,就不能产生共鸣,无法与之对话。”〔9〕
《课程标准》更是强调这一点,“前言”“课程理念”中反复提及:“……必须顾及学生在原有基础、自我发展方向和学习需求等方面的差异……为每一个学生创设更好的学习条件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促进学生特长和个性的发展……向学生展示层次多样的语文课程图景,提供丰富的语文营养和多向度发展的途径……满足不同学校和学生的需要……按照具体条件和学生的需求,有选择地、创造性地设计和实施课程……”
教材的普适性必然带来针对性不强的弊端。各地区的文化背景、经济状况、社会环境等各不相同,教学目标也各有差异,孩子们的情况更是千差万别,这也是课文现实化时必须考虑的。
2.课文必须有效化
课堂是现实的,它要求我们对课文内容加以选择;课堂同时也必须是有效的,因为它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有任务和速度的要求,我们不可能把现实化后的课文内容不加区别、不加组织地搬到课堂上。
比如对课文切入点的精心选择。教学苏教版必修三高尔斯华绥的《品质》,我抓住课文中的“渐变”现象,让学生找出有哪些东西在“渐变”(计有格斯拉外貌的变化5次、店面的变化3次、靴子牢固程度的变化3次、“我”定做靴子数量的变化4次),这些正是作者精心刻画的细节,言语精美、描写生动,而且还和格斯拉不变的“品质”形成对比。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其他还有对课文重点的突出、对课文问题的设计等。
3.课文课堂化不是传统的备课
课文课堂化和我们的传统备课看起来有点相似但却根本不同:一是指向不同,传统备课是为了完成教学任务,指向教参上既定的教学目标;课文课堂化则从教学实际出发,指向学生的学习,考虑为学生服务,——当然也会考虑教学任务。二是内容不同,传统备课是对一整节课的安排设计,还包括导入、设境、板书、作业等多个环节,而且它对课文的处理往往带有更多非语文化的内容;课文课堂化侧重于关注课文的言语,显得比较专业,而且范围狭小,至多只能算是备课中的一个主要步骤。三是深度不同,传统备课很大程度上只是从课文、教参转移加工到教案,往往只是平面化的知识传递和整合;课文课堂化经过了课文的读者化和语文化,有了教师的思考,考虑了学生的反应,突出了教学重点。——当然,这里最根本的差异是新旧教学理念不同。
〔1〕伍蠡甫编《现代西方文论选》,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93页。
〔2〕[法]米盖尔·杜夫海纳著、孙非译《美学与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58页。
〔3〕吴非著《不跪着教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4〕〔8〕李海林《文选型教材的双重价值》,《语文学习》2004年第3期。
〔5〕王尚文《紧紧抓住“语文”的缰绳》,《中国教育报》2004年7月8日第5版。
〔6〕李海林著《言语教学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版,第355页。
〔7〕黄耀红《没有语文的语文课》,《湖南教育报》2001年5月8日。
〔9〕王尚文主编《语文教学对话论》,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9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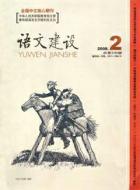
- 如何进行中考的复习备考 / 唐建新
- 新课程高考语文考试评价标准及试卷结构技术指标构想 / 王后雄 张建中
- 《2008年江苏高考语文科考试说明》解析 / 江 熙
- 中学语法教学的原则和策略 / 周一民
- “干物女”与“肉松男” / 于 涛
- 话说“金包银” / 何明延
- 说说“闺蜜” / 傅 宏
- “各个”不同于“个个” / 隆 林
- “黑檀”正名 / 王 洁
- 从“喂死他”谈起 / 孙晓惠
- 一口井还是两口井 / 高全军
- “贵贱情何薄”的词义与句法 / 方有国
- 宁静之美,自足之情 / 周秀林
- 无处可寻、无处不在、无可奈何的忧愁 / 孙绍振
- 《愚公移山》中“夸蛾氏”为“巨蚁神”补证 / 王克家
- 美国高中语文爱情婚姻题材作品的教学 / 王爱娣
- 从“五十者”的翻译探究孟子的思想 / 梅其涛
- 细节的魅力 / 杨和平
- 走出范读的误区 / 莫艳辉
- 举例子与举例 / 武宏伟
- 论课文教学化的意义与实现 / 黄华伟
- 回归生活,重塑作文之魂 / 李本华
- 高中作文教学现状之管见及建议 / 储开华
- 教出语文课的灵气 / 刘占泉
- 《列夫·托尔斯泰》教学实录 / 侯 雪
- 一树绚烂,点燃生命的火花 / 王 江
- 设计课前预习问题的策略 / 李志清
- 论点摘编 / 佚名
- 同侪语言的生成价值与开发策略 / 刘晓伟
- 温故知新 / 饶杰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