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教学之友 2007年第1期
ID: 359240
语文教学之友 2007年第1期
ID: 359240
半“生”不遂可悲可叹
◇ 祁俊来
《孔乙己》一文,作者主要是通过外貌、语言、动作等方面的描写来塑造孔乙己这个人物形象。但是,在仔细研究这些内容的同时,笔者又发现,孔乙己的一生始终没有跳出一个“半”字,正可谓是半“生”不遂,让人可悲可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姓名让人半懂不懂
从课文中我们看到,他的姓名来源描红纸上的“上大人孔乙己”这句半懂不懂的话。他作为在封建社会熟读《四书》《五经》的知识分子,却连一个像样的、好听的名字都没有,说明他社会地位低下,是个有姓无名的人。作者用这个叫人半懂不懂的绰号作为他的名字,正是表现了人们对这个人物迂腐可笑的性格的嘲弄。
二、说话让人半懂不懂
每当来到酒店时,他总是说一些“之乎者也”之类的话,让人听了半懂不懂。当别人取笑他偷书时,他却说:“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紧接着就是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的话。他用这些半懂不懂的话一方面是为了搪塞别人,应付那种使自己尴尬的局面,另一方面是表示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经书上圣人所教,非一般人所能理解,很带有卖弄之意,使人读了深感他的迂腐不堪,麻木不仁,自欺欺人。当孩子们再向他要茴香豆吃时,他却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仍然是“之乎者也”无用的东西,这进一步反映出了他对自己卑下的地位和知识的陈腐毫无认识,同时也表现了他三句不离本行的迂腐思想。
三、做事半途而废
“他身材很高大”,又“写得一笔好字”,这些本应该是他维持生计的有利条件,但是他好喝懒做,好逸恶劳,把体力劳动看作是最低下可耻的事,因而从来没有想过既然不能中举,何不凭借自己的双手挣碗饭吃,就是替别人抄书一类的工作,他也坚持不了几天,到最后“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一齐失踪。他一直想通过科举考试实现做官的梦想,他信奉的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但是他怕吃苦,想不劳而获,到须发花白的年纪,他也还只是个“童生”,最终潦倒穷困,成了封建社会的牺牲品。
四、读了半辈子书
孔乙己读了半辈子的书,把自己的理想、希望全寄托在通过科举取得功名上,可是到头来连半个秀才也没捞着。但又不死心,认准只有读书才是惟一的能够谋取功名的途径。在长期的封建教育熏陶下,他和一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士大夫一样,鄙视体力劳动,养成了好喝懒做的恶习。科举的途程对他来说已是毫无希望的了,但他仍抱幻想,聊以自慰,一旦没能“进学”,便“不会营生”,于是他生活越过越穷,沦为乞丐,最后默无声息地吊死在“科举制度”这棵树上。
五、身份半短衣半长衫
在酒店中,孔乙己一出场,作者就写道:“孔乙已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惟一的人。”虽然只有一句话,但含义极为深刻。“站着喝酒”,说明他经济拮据,买不起酒菜,进不了柜台内,不能享受“长衫顾客”的待遇,跟“短衣帮”一样,都处在社会的最下层,过着饥不择食的生活;可是他又是“短衣帮”中惟一“穿长衫”的人,这又说明他是一个社会地位低下而又不能爬上去的“知识分子”,是一个从“长衫顾客”中被挤出来的人,跟短衣帮不同。但他不肯脱掉长衫和短衣帮为伍,因为这件长衫是“读书人”身份的标志,有了这件长衫,他似乎在精神上还可以得到些安慰。这样,他既不能爬到上层,又不肯甘居下层从事劳动,挣碗饭吃,硬装斯文,死要面子,从而沦落成了一个畸形的“多余的人”。
另外,他到丁举人家偷东西,让丁举人抓住,打了大“半”夜,结果被打折了腿,成了一个“半死不活”的残废人。文章结尾写他虽然死了,但是他的名字仍然还留在酒店的粉板上,仍然被老板念叨着,这不是老板对他的怀念,而是他还欠着酒店老板的十九个钱,才被人牵挂着,所以,他并没有完全死了,只死了一“半”。这说明他的人生是悲惨的“半”个人生,也表现了这个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冷漠无情。
小说中作者通过上述的“半”字现象,描绘了孔乙己这个被旧社会扭曲了灵魂的“多余的人”的悲惨一生,刻画了他自命清高、麻木不仁、自欺欺人、可悲可笑的性格特征,锐利地剖析了封建文化、科举制度的虚伪与无耻,以及对历代知识分子的严重精神戕害。
(作者单位:天祝县第二中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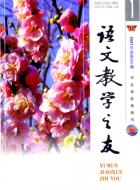
- 高中语文课程目标需要修改 / 陈祥书
- 不宜选入中学教材的鲁迅作品 / 魏永雅
- 高考作文命题视野中的中学文学教育命运 / 周圣荣
- 语文课堂的三种基本功能 / 朱 江
- 平衡与偏移:语文知识选择的原则 / 栾雪梅
- 语文课堂在于品 / 王中意
- 从主导的失位谈起 / 朱文武
- 语文课堂教学征引四忌 / 丁佳友
- 略论阅读教学中的模糊艺术运用 / 王针桂
- 诗的含蓄与含蓄的诗 / 陈元勋
- 精心打造文章的骨架 / 罗章华
- 找准说明文的“动情点” / 邹仕泽 冯正雁
- 校园AB剧 / 王小华
- 公开课《记承天寺夜游》教学设计 / 付秀艳
- 跨越时空的“评选” / 石玉成
- 热闹之后的冷思考 / 严爱军
- 《奇妙的克隆》指瑕 / 方逸帆
- 解读《心声》里的陈老师 / 施海刚
- 半“生”不遂可悲可叹 / 祁俊来
- 为鲁四老爷减刑 / 李 玲 曹长发
- 在魂灵的有无之间,祥林嫂希望什么 / 谢月梅
- 从“非人间”谈开去 / 李廷周
- 也谈《失街亭》孔明“三哭” / 李殿林
- 《赤壁赋》的景、情、理 / 于树华
- 重建高中作文教学序列的探索 / 曹玉兰
- 试论朱自清的写作教学观 / 梁秋实
- 记叙文时间词语的运用技巧 / 许翠先
- 文学作品阅读解题指津 / 单 猛
- 为高考作文支招 / 姚慧格
- 文本与问题的碰撞 / 康九星
- 文言中考新特特点与新启示 / 黄先法
- 2007年普通高考新课程标准语文科考试大纲 / 教育部考试中心
- 《在安静中盛享人生的清凉》读与练 / 佚名
- 《美洲豹的悲剧》读与练 / 佚名
- 《运载火箭的发射与飞行》读与练 / 佚名
- “缩水”新义 / 王明春
- “上当”溯源 / 靳建炬
- 成语之“最”戏解 / 苟大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