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教学之友 2011年第1期
ID: 146595
语文教学之友 2011年第1期
ID: 146595
震撼人心的悲剧
◇ 杜太平
“悲剧”一词作为广义的美学范畴,不仅存在于戏剧艺术中,也存在于非戏剧艺术的其他形式中。鲁迅正是把美学意义中的“悲剧性”熔铸到了他的创作实践中,仅从中学课本所选的小说来看,这些小说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全面反映了个人悲剧和社会悲剧。如《狂人日记》反映了中国农民的悲剧,《孔乙己》反映了下层知识分子的悲剧,《祝福》反映了劳动妇女的悲剧,《药》反映了旧民主主义革命者的悲剧。这些悲剧小说,从美学角度来看,有如下几个共同特征。
一、真实性
真实性是鲁迅先生构建小说悲剧的最基本特征。他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先生“如实描绘,并无讳饰”地反映了封建统治铸造的各种形形色色的人间罪恶。《祝福》中的祥林嫂,由于死了丈夫,逃到鲁家帮佣。她聪明能干,吃苦耐劳,希望以劳动换取生存的权利,但不久被婆婆劫回卖到山墺里。第二个丈夫死于伤寒,儿子被狼叼去,她被贺家族人赶了出来,第二次来到鲁家。受封建迷信的愚弄,她认为自己要受“神”的惩罚,不惜用自己的血汗钱去庙里“捐门槛”作替身,让“千人踏,万人跨”来消除罪愆。随着小说情节的展开,读者眼前仿佛会现出一幅幅生活的真实图景。犹如亲身经历那个黑暗如漆、冷酷如铁的时代。尽管她不断挣扎,依旧冲不破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交织着的天罗地网。这种真实性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相反,几千年来的中国封建文人总是不愿睁开眼睛正视现实,喜欢“瞒”和“骗”,用盲目乐观的团圆主义,为统治阶级“曲终奏雅”。鲁迅先生对“瞒”和“骗”的虚假艺术是深恶痛绝的。鲁迅把大胆否定与破坏社会邪恶的真实性,看作是悲剧的基础和前提。
二、幽默性
幽默属于审美层次的高层。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说,幽默的本质,“是在平凡渺小里发掘价值”。鲁迅先生是深得幽默奥妙的。《阿Q正传》在塑造阿Q这一形象时,运用严肃认真的现实主义法则,对阿Q的自轻自贱、自欺欺人、恃强凌弱、健忘等诸多弱点,给予了辛辣的讽刺。然而对阿Q的悲剧命运又倾注了深切的同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对阿Q的所作所为,语言心理,发出温和的、善意的、含泪的微笑。阿Q在挨了打、受了侮辱之后,常常气愤难平,但一想到“儿子打老子”这句话后,又释然如故。听到革命党进城的消息,看着未庄人惊惧的目光,“又使他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这样的许多细节描写,活画出了阿Q无比滑稽可笑,使人忍俊不禁。《孔乙己》中,那个满口“之乎者也”,用手罩住茴香豆的孔乙己,模样令人发笑。然而,无论对阿Q还是孔乙己,笑过之后,又会令人十分悲哀。因为我们从表面的“圆满里发现它的缺憾,在缺憾里也找出它的意义”。他们人性中所具有的良知和品行被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吞噬,封建制度造就了这两个社会的畸形人、多余人。鲁迅先生的这种美学趣味真正表现出幽默含义的深度和广度。
三、平常性
鲁迅先生的悲剧小说,不仅具有不带任何粉饰的真实性,而且具有显而易见的平常性。
平常性是鲁迅先生小说艺术的一惯风格,他的小说中没有英雄,没有特殊事件,没有传奇色彩。小说的主人公都是社会底层的平常人,甚至是畸形人,然而,他们的悲剧命运却令人战栗。
平常的人和事即是人所司空见惯的。正因为如此,用平常的事件表现发人深省的思想尤其难能可贵。鲁迅先生敏锐地觉察到“软刀子”割头不觉死的悲剧,现实社会如残酷的“地狱”,却“谁也看不见”,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是“吃人”的历史,人人却习以为常。他说:“中国人倘被别人用钢刀来割,是觉得痛的,还有法子想,倘是软刀子,那可真是‘割头不觉死’,一定要完。”他所讲的这个道理,完全适用于他笔下的那种死于“几乎无事的悲剧”者。他们被丑恶的社会关系、旧思想、旧文化所蚕食,却习以为常,任其摆布。《故乡》中的闰土,并没有死于大劫大难,却被官兵匪盗封建迷信剥夺了青春,榨干了血汗,泯灭了智慧。那个被封建人伦关系和礼教压迫发疯了的狂人,在疯狂状态中能够认识到整个社会吃人的本质;在“理智”明白的时候竟然顺应封建既定的秩序,做起了他的候补知府。鲁迅先生正是在这种熟视无睹的平凡现象中,发掘出了震撼人心的社会悲剧。
四、科学性
鲁迅先生是悲剧艺术大师,但不是悲观主义者。他对人为地制造团圆主义坚决反对,但不主张悲剧艺术注定要走向悲观。他的悲剧艺术具有鲜明的科学性——满怀希望,坚信未来。1930年,他在《〈浮士德与城〉后记》里说:“新的建设的理想,是一切言动的南针,倘若没有这而言破坏,例如未来派,不过是破坏的同路人,而言保存,则全然是旧社会的维持者。”尽管他的《呐喊》《彷徨》小说集写在这以前。但是,他的小说实践和悲剧观却是在这一理论的支配下完成的。
鲁迅先生的小说,尽管都用悲剧的“被毁性”大胆否定了旧制度、旧思想,“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煞的,因为希望在于将来”。所以他往往“不惜用了曲笔,在《药》中瑜儿的坟上平添一个花环”,这花环便是一种寄托,一种象征。在《故乡》中,我们还听到他凝聚着希望的独白:“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总之,鲁迅先生虽然不是美学理论家,他的美学思想并没有系统化,但他的美学实践却是无与伦比的。研究探讨鲁迅小说的美学特征,对中学语文教学不无裨益。
(作者单位:庄浪县职教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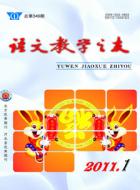
- 研究性学习与现代文阅读教学 / 邓陶钧
- 我是这样设计教学方法的 / 徐锦文
- 本体论与新课标 / 黄建恒
- 谁误读了“语文” / 明兴华
- 词语教学,不容忽视! / 刘 英
- 张扬个性 教出特色 / 蒙 遹
- 在言意关系观照下的语文素养构成论 / 张阳成
- 语文课堂教学的基础等级和发展等级 / 崔 健
- 浅谈生本教育理念下的语文教学 / 翟 霞
- 语文教学应小处做实 / 杨定凤
- 学生语文学习中泛读的缺失及对策 / 章登享
- 阅读教学的有效抓手 / 郝泽茂
- 倡导回归语文本体特点的有效学习方法 / 曹亚平
- 例谈课程改革下的语文说课 / 王立英
- 自读课文教学“三要” / 陈雪芳
- 在阅读教学中如何品味语言 / 雍自军
- 《学记》对语文教学的启示 / 黄宏欣
- 瑕也掩瑜疵斑斑 / 都自祥
- 把握古典诗歌的“情脉” / 林 爱
- 怎样运用文言文注释 / 于 庆
- 只挖一个洞 / 贾佑智
- 渡过“苦海”的方舟 / 李中华
- 《两小儿辩日》的两点教育启示 / 谢冬樱
- 误判一句 冤案无数 / 袁海霞
- 范仲淹是在“拍马屁”吗 / 高 青
- 浅谈如何提高语文试卷讲评的效率 / 王国节
- 湖光山色中的人生境界 / 陈颂善
- 《孔乙己》中的四类笑声 / 张桂成 费年成
- 新课程背景下初三语文试卷讲评课的实施策略 / 王巨鹏
- 震撼人心的悲剧 / 杜太平
- 《守财奴》中葛朗台行动描写的特点 / 赵武之 李晓奎
- 一篇调动了多种表达方式的“无韵之离骚” / 慕文俊
- 夯实“三个”基础 提高写作能力 / 王保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