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06年第2期
ID: 81716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06年第2期
ID: 81716
《寒夜》:中国现代诗化小说的经典
◇ 金立群
现在的文学理论中出现了“诗化小说”的概念。我想,诗化小说和以前常说的浪漫抒情小说还不太一样。它的独特之处,不在于优美的文辞、丰厚的抒情、浪漫的故事,而在于其文本的构建是出于一种感觉、一种情绪,将情节的安排、人物形象的塑造置于某种意境、氛围之下,并形成与中国古典诗学相通的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美学风格。也就是说,诗化小说的文本,是以个体直觉、当下感受为出发点和本体的,这就和以理性思考、意识形态、或故事言说中的趣味技巧为出发点和本体的小说形成了本质区别。小说的叙事功能被淡化,客观化的环境描写为主观化的气氛渲染所代替,意境、意象、象征、抒情成为中心,情节则为它们服务,而不是相反。个案分析是历史叙述的基础,本文正是希望通过对巴金代表作《寒夜》的分析,更好地揭示出诗化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魅力和价值。
一
中国古代即有“物不平则鸣”的说法。然而如何去“鸣”,如何对着时代、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却有不同的方式。其一是理性的方式,追求典型的塑造,力图在典型的个性中体现出背后的普遍性,以揭示某种规律和本质。如20世纪30年代的茅盾,把他十几年来参加新文化运动、参加共产党、投入北伐、脱离共产党、流亡日本等等复杂的经历与生活感受上升为理性思考,超越个体,观察社会的本质,从而创作出一系列社会剖析小说。理性的创作方式被狭隘化后往往还成为表达某种意识形态的工具。其二是纯粹形式的方式,醉心于为艺术而艺术,游戏文本,宣称文本之外一无所有,用彻底排斥现实的方式表达自我的特立独行,上世纪初的达达主义就是这样。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元小说虽然没有完全取消叙述的内容和其中包含的情感,但已将创作的本体由故事转向故事的言说方式。作家对人生、情感作本体意义上的取消正是他们表达对人生、情感之困惑的特殊方式。以上两种写作,都具有“客观化”倾向,或以客观世界为表现本体,或以客观形式为追求目标。即便是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创作,其意识形态也不再是鲜活的包含着主体之思的意识形态,而是凝固成型的凌驾于主体之上的、外在于主体的、“客观化”的意识形态。其三是感性的方式,由体验出发,将世界由一个公共空间化为主观的“为我”的世界,通过直观创造意象,直达它的终极秘密。这正是《寒夜》把握世界的方式,也是它作为一部诗化小说的最基本的条件。
《寒夜》在情节安排、场景描述上的最突出特点正如这部小说的题目,一切都在寒夜中进行。小说从寒夜开始。第一个场景就是汪文宣躲完空袭后一个人走在寒夜中空寂无人的街道上,“不由自主地向四周看了看,并没有人在他的身边”。小说又在寒夜中结束。最后一个场景是归来的曾树生离开了那个已是人去室空的家,“刚走出大门,迎面一股寒风使她打了一个冷噤”。这对曾经生活在一起,“心却隔得很远”,最终天各一方,直至阴阳两隔的夫妻就这样在小说的一头一尾遥遥相视,中间是将他们分隔开的浓厚、无边、无法穿越的寒夜:每一次家庭争吵过后汪文宣就会冲进寒夜,“又走了一条街,还是不知道应该走到哪里去”;他时常在寒夜中等待妻子回家,“街上的二更梆子响了”,“‘她’快回来了罢”;在寒夜中,他发现自己得了肺结核,“看见痰里的血丝,心中一冷”,“精神和体力似乎完全崩溃了”;在寒夜中,他收到了一份解雇通知书;在黎明前最暗最冷的寒夜中,他送别了妻子;最后他死于寒夜,“这是在夜晚八点种光景,街头锣鼓喧天,人们正在庆祝胜利,用花炮烧龙灯”。
巴金作品一般被认为所涉及的主要是制度文化层面的内容。他自己就说过“我曾说我鞭挞的是制度”。[1]但他不是像茅盾那样对制度做理性的分析和批判,而是侧重于“情绪化”、“人格化”的制度。与其说他在写制度,不如说他写的是某种制度下人物的直觉体验与心灵感受。《寒夜》的魅力正在于此。诗化小说淡化叙事功能并不一定意味着淡化叙事本身。应该说,《寒夜》和《呼兰河传》,和《边城》这样散文诗般的诗化小说有所不同,其情节性要超过它们。围绕着曾树生的走与留、去与归,围绕着汪文宣的得与失、生与死,围绕着一个普通家庭的悲与欢、聚与散,这部小说对读者是有着情节上的吸引力的。然而,这样的题材,不能说是空前绝后,为什么除了一般性的吸引力外,还给几代读者带来强烈的心灵震撼呢?这正是因为作者将整个情节与叙事纳入了寒夜,让我们置身于黑暗、寒冷之中去感觉,去体验,去茫然不知所措,去冻得发抖。一个客观的、公共的世界不是这样的,它除了寒以外还有温暖,除了夜以外还有白天。小说里的世界和这个公共空间相比是不全面的。这里没有火热的民族救亡战争,没有《风景谈》和《白杨礼赞》所暗示的另一片天地。然而问题在于这样一个所谓的客观的、公共的世界存在吗?我们只可能生活在一个具体的自我所能感知的世界里。康德认为,审美判断虽然只关个人对个别对象的感觉,却仍可假定带有普遍性。这种普遍性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2]因此正是这种“不全面”,恰恰具有审美判断的品格,恰恰创造了真实——主观的真实。特别是小说将要结尾之时,街道上破天荒出现了欢乐,洋溢着生命的喧闹,而这一切对我们的主人公汪文宣已不再有任何意义。公共的希望不是他的希望,公共的欢乐不是他的欢乐,公共的生命也不能成为他的生命,他的命运仍然是孤独和死亡。我们没有充足理由说巴金就是受到了存在主义的影响,但存在主义也不是几个哲学家的凭空发明,它植根于人类漫长历史中某种感悟的积累,是可以为人所自发体会的。在小说里,我们确实可以感到,人“除掉自己的行动总和外,什么都不是;除掉他的生命外,什么都不是”。[3]汪文宣痛苦地死于抗战胜利后的欢乐气氛中,充分说明了对于个体来说,最真实的就是他自己的处境。“除掉人的宇宙外,人的主观性宇宙外,没有别的宇宙。”[4]“寒夜”就是这样一个主观的宇宙。这部小说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向我们揭示了一次独特的人生体验——寒夜体验,它以“寒夜体验”为出发点和表现本体,显示出强烈的主观性。艾略特以其“荒原体验”揭示出现代西方人的独特生存境遇,而巴金的“寒夜体验”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中国人有着同样的意义。
二
“诗缘情”,诗源于体验,但体验也并不一定都指向诗。表现体验的形式是确立诗化小说品格的又一重要参照。小说在表现个体体验时可以有多种方法,如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那样对城市的喧嚣、混乱、贫困进行自然主义的描写和渲染,如小仲马的《茶花女》那样以充满感情色彩的叙述、对话宣泄自我的爱与痛,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那样展现大段的内心独白和意识流,直接面向体验之中的心理活动。这些都是对个体体验的表现手法。《寒夜》表现个体体验的特点在于当创作主体形成自我独特的“寒夜体验”的同时,小说也将个体体验凝炼为独特的中心意象——寒夜意象。这是《寒夜》作为诗化小说的基本特点。主要的情节、场景乃至细节均围绕着这个中心意象,为它的营建服务。它笼罩于整个城市的上空,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而是渗入到生活的每一个瞬间,成为包含着丰富个体体验的感觉和情绪。它是外化的心灵与内化的世界之间的融合。这就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推崇的“境界”:“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4]“寒夜”作为意象,类似于风,也类似于艾略特的“荒原”,都是属于那种直达生命终极之“道”,因而显现出“大道无形”的没有具体形态的意象。所以小说中直接渲染描写寒夜之寒、之黑暗的句子并不多。这有点类似于中国传统绘画中的留白手法,以画面空白周围的线条、色彩来烘托那真正的表现对象。因此,“寒夜”意象与其说是被创造出来的,不如说是被烘托出来的。《寒夜》中没有大段大段的写景和抒情,和巴金前期创作中所体现出的强烈的情感、奔腾恣肆的语言有所不同,其笔调是冷静而深沉的,采取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似乎与诗化小说的主观浓情相悖。但是在这部小说里,却恰好配上并增加了寒夜中的寒气,起到了需要的表达效果。作者一方面主要通过主观之“意”与客观之“象”的结合所形成的意象来表达自己的感情,更多地将“意”化入“象”中,另一方面又注意宕开来写,通过其它意象来烘托寒夜这一中心意象,将“此象”化入“彼象”。这同时也是为什么和《家》等作品相比,《寒夜》虽然在叙事层面上更为客观,感情上却更富于感染力的原因。
[##]
与寒夜意象相对应的是“白天”与“灯光”。也许是寒夜过于强大的缘故,即便白天来临,天也“永远是阴的,时而下小雨,时而雨停”,“可是马路始终没有全干过”,“天还是灰色,好像随时都会下雨似的”。汪文宣的眼光“茫然地向四处看”,除了“白茫茫的一片”显示出是白天而外,依然如在夜里一般,“似乎什么也看不见”。即便没有下雨,也依旧是“特别冷”、“虽然有阳光射进来,阳光却是多么的微弱”。灯光是人类反抗与超越寒夜的尝试。寒夜下的灯光却是孱弱的,如“星子似的在黑暗的街中闪光”,只能让人感到“寒意”;作者用“寥寥”、“昏暗”、“黄黄的”这一系列暗色调的形容词来修饰灯光。然而,就连这样的灯光也要常常因停电而熄灭,给寒夜让位。这时就只能点蜡烛了,“但是摇曳不定的惨黄色的烛光,给每一件东西都涂上一层忧郁的颜色”。看着烛光,汪文宣不禁要叹气:“光明,我哪里敢存这个妄想啊。”“白天”与“灯光”不但没有能够消解“寒夜”所带来的黑暗与寒冷,反而增强了“寒夜”的力量,让人更加绝望。由此可见在这部作品中,不但情节与叙事被纳入了寒夜意象的营造,就连本该作为对立意象存在的白天与灯光,也被纳入其中,起着衬托、突出中心意象的作用。在寒夜的笼罩和影响下,不但白天与灯光,就连汪文宣听惯了的老年人叫卖“炒米糖开水”的声音都染上了寒气,让他“打了一个冷噤,好像那个衰老的声音把冷风带进了被窝似的”。
就这样,寒夜超越了特定的时间概念,成为整个岁月、整个生命的统治者。在寒夜的统治下,不再有色彩,世界如同一张发黄的黑白照片。惟一的例外是红色。在小说的开始,当空袭警报解除的时候出现了两个“红亮亮”的红灯笼,家门口的门灯也发射出“暗红色”的光。那时侯,汪文宣对生活的希望还没有完全破灭,也许这惟一的亮色代表了一丝光明与希望吧。但是,接下去,我们又发现了红色,而且不断出现,是汪文宣吐的血。原来,在红色的背后是死亡,是永恒的黑暗。它同样是寒夜的一部分。
在《寒夜》的人物情节安排上,有一个原型,就是汪文宣与曾树生之间“郎病女貌”的婚姻模式,它源于中国古典小说,由“郎才女貌”演化而来,所谓“我就是那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这个原型原本反映了过去的文人士大夫顾影自怜、对月伤怀、迎风洒泪的病态审美心理,但在这部作品中却获得了新的意义。美丽而充满活力的曾树生对寒夜笼罩下的汪文宣而言意味着青春与激情。她的最终离去说明了寒夜压迫下的汪文宣已经彻底丧失了生命力,丧失了挽留青春与激情的力量。他在曾树生面前有自卑和压抑感,在健康和美丽面前更加深切地体会到自己的孱弱无力。当他用尽全身的力量在曾树生离去的那个寒夜最后一次尽做丈夫的义务,帮她拎箱子下楼时,遇到了迎上来的陈主任:“‘给我提’,另一个男人的声音说。这是年轻而有力的声音……恍惚间他觉得那个人身材魁梧,意态轩昂,比起来,自己太委琐了。”这种自卑与压抑与他对寒夜的感受具有相同性质。而曾树生面对这样一个病恹恹的丈夫,同样感到压抑:“她回头向床上看了一眼。他的脸带一种不干净的淡黄色,两颊陷入很深,呼吸声严重而急促。在他的身上她看不到任何力量和生命的痕迹。”这个丈夫和寒夜一样,让她对生活感到心寒。在传统的郎病女貌模式中,渲染的重点在双方“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痴情和体贴。然而这里,却变成了双方彼此的压抑和折磨,变成了寒夜的一个化身。看看这对郎病女貌的“才子佳人”分别的最后一幕吧:“两个人立在黑暗与寒冷的中间,听得见彼此的呼吸声。”正是在此意义上,一个传统的原型也被纳入了寒夜这个中心意象。
小说之意象不同于诗歌之意象的地方在于它并非单纯的空灵,而可以比较复杂,这是由小说在言说方式上的特点所决定的,它对意象的塑造不需要在几个字、几行诗中完成。《寒夜》中的意象表现具有复调特点,这是一个创造,主要体现在小说的第一节。汪文宣在躲空袭后一个人回家,路上想起了昨天的一场争吵。妻子离家出走。自己是不是还要像从前一样主动去找她回来?妻子会回来吗?夫妻、婆媳之间会和好吗?这个家会幸福吗?围绕这些问题,汪文宣的心中有两种声音各自说话。第一种声音是自我安慰、精神胜利、麻痹自己痛苦感觉的声音。这声音告诉他,妻子走就走,回来不回来无所谓,用不着主动去找她;也许可以让儿子帮忙,为了他们的儿子,妻子也会回家的;说不定妻子现在已经回家了,“妈说她自己会回来的。妈说她一定会回来的……说不定她们两个在一块儿躲警报。那么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在警报解除后走回家去,就可以看见她们在家里有说有笑地等着我”。第二种声音表现出他对现实的正面思索与痛苦感受,对妻子一去不返的恐惧;在他孱弱的人生中需要妻子的爱与温暖,而这种需要实际上说明了他在人生与家庭中的弱者地位。这个声音对他说,他没有胆量对妻子的出走假装无所谓,“你有胆量吗?你这个老好人”;儿子小宣并不关心妈妈,也不可能帮忙,他汪文宣是一个没有人关心的可怜虫;他不能确定妻子会不会回家,他需要妻子,“想找她回来”。这两种声音在汪文宣的心里各说各话,都有自己的逻辑与理由。先是前一种声音略占上风,以至于他把家门口不相干的一男一女误认做母亲和妻子。等到回家后他发现妻子并没回来,就“好像从梦中醒过来似的”,只剩下“茫然的”眼光,“思想很乱……纠缠在一起,解不开”。同时,汪文宣周围的环境也化为一种声调。他在夜晚的街道上走着,寒夜下的城市和他似乎并不相干,“他并没有专心听什么,也没有专心看什么”。偶尔,走过一个人,他的眼光并“没有去注意那张脸……但是他的眼睛仍然朝那个人消失的地方望着。他在望什么呢?他自己还是不知道”;偶尔又传来几句说话声:“我卖掉五封云片糕”、“我今天晚上还没有开张”、“今天晚上不晓得炸哪儿”、“昨天晚上打三更才解除”。这些声音与他内心的声音平行着,没什么关联,可是他又“忽然吃了一惊,昨天晚上……打三更!……为什么那个不认识的人要来提醒他”,他内心的声音就在这不经意间又回到昨天争吵前一家人表面上有说有笑的时刻。就是这样,一方面环境的声调与他内心的声音各自发展着,一方面外在的声调又不时在汪文宣内心两种声音的对话中间插上几句,外在声音与内在声音组成的两个声部之间时远时近,结合在统一的时空下而不发生融合,从而形成了另一重复调。正是在这样的双重复调中,寒夜意象的蕴义得到了含蓄的表现。这个双重复调展现出主观心灵与客观世界之间既关联又疏离的特殊关系。一方面,巨大的寒夜对渺小的个人是不屑一顾的,它甚至可以忽略个人的存在;个人面对着寒夜,也不可能像面对温暖的故乡家园一样纵情投入,而是会产生疏离感,就好像手碰到一块冰就马上缩回来。另一方面,个人又永远不能摆脱寒夜,而寒夜也总是会介入个人的心灵,把自己无形的触手伸进个体的灵魂。《寒夜》中的复调和一般的叙事型或心理型小说中的复调有些区别,其所要传达的主要不是构成复调的不同声部本身的内容,而是要通过这些不同声部之间的对立、平行与结合暗示某种有关人生境遇的意味,有点类似于意象叠加。这充分表现出作品浓郁的诗性特征。
三
《寒夜》由“寒夜体验”出发,构建出贯穿全篇的“寒夜意象”,使主观心灵获得了感性显现,从而使“寒夜意象”进而上升为“寒夜象征”。黑格尔认为:“象征一般是直接呈现于感性观照的一种现成的外在事物,对这种外在事物并不直接就它本身来看,而是就它所暗示的一种较为普遍的意义来看。”[5]这说明象征并不是反映以此物“象征”彼物的一种确定性联系。在西方文论语境下,它具有一种认识论上的意义:首先是针对不可言说的超验性宗教理念,后来在马拉美等象征主义大师那里是针对不可言说的彼岸世界,最后引申为针对一切不可言说的思想、情绪、体验,以至于我在上文提到的康德所说的主观的普遍性,对于这一切不可言说的无形无象之物,需要有一种感性的形象去把握,把握的方式不是明晰的直陈,而是不确定的、朦胧的暗示。因此,如传统看法那样,将寒夜视作对黑暗社会与专制制度的象征是不确切的。这样意义上的寒夜,称不上象征,只能算是比喻,而且它也无法解释小说所达到的震撼读者心灵的接受效果。寒夜象征的其实是个体的心灵,由个体对自身命运产生的所有感受、所有情绪、所有冲动以及对这命运之未来的神秘预感所共同构成的活生生的流动的心灵。
[##]
由于寒夜作为一个中心意象在小说中取得主导地位,由于小说中的情节与人物关系设置围绕这个意象所创造出的“寒夜象征”,小说在信息发送上就产生了类似于诗歌的特点,即主要不是以大的情节和人物形象来传达明确的内容,而是通过这个中心意象以及围绕之的其它意象进行暗示,传达意味。比如前文所述小说开头的那个“双重复调”对心灵与世界之关系的暗示;比如说小说在结构上安排男女主人公分别出现在第一个场景和最后一个场景,让人感觉他们似乎在一条永远无法渡过的寒夜之河两岸遥遥相望,从而领悟到他们各自的孤独与心灵之间遥远的距离,这就暗示了他们彼此的感情实质。又比如小说中经常出现男女主人公独自一人在寂静的街道走,使我们可以体会到他们内心的寂寞,他们都渴望走出寒夜,却始终无法做到。那永远阴沉沉的白天与随时都可能因停电而熄灭的灯暗示了心灵对光明的渴望在黑暗面前的脆弱和那可以随时熄灭生命之光的命运的无常。小说第一节的结尾汪文宣在极度的身心疲惫中回到家,“没有关电灯”就“沉沉地睡去了”,暗示出他对寒夜、黑暗的恐惧与抗拒。汪文宣染上的肺结核,可以说是中国小说中人物的常见病。过去的小说安排人物得肺结核是侧重于这病有一点世纪末味道的颓废唯美色彩,比较雅。而这部小说却对它进行了令人产生恐惧感的详细描写,打破了病态美。然而作家这样安排还是有他的道理。这种病的特点在于让人慢慢地走向死亡。而这也正暗示了主人公对寒夜的独特体验和对自我命运的预感:它不同于凶狠的猛兽迅速将人吞噬,而是慢慢渗入人的精神和肉体,一点一点熄灭其中燃烧的生命火焰,给人带来长期的折磨。自我经过长期痛苦的挣扎,却始终无法冲破寒夜,最后还是要死。
需要指出的是,《寒夜》所诞生的20世纪40年代,正是中国现代文学继“五四”后的又一次大反思的时代,一方面继续着“五四”以来新文学“感应世界思潮、注重人的意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又以更加成熟的心态看待传统文化,对其深层意蕴作新的探索,以期作为重塑民族文化品格的根。[6]当时以中国新诗派为代表,以西南联大为大本营的国统区大后方文化界掀起吸收西方现代文学思想、手法的又一次高潮,涌现出一批在探索民族生存境遇、挖掘个体人性内涵、综合吸纳民族的和西方的文化成果运用于创作等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度的作品。《寒夜》成为这一创作高潮中当之无愧的佼佼者。巴金早年曾留学象征主义的发源地和中心法国,深受法国文学影响。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寒夜象征”正体现了对西方象征主义诗学的创造性借鉴。但同时,又表现出和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显示出作家对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学手法的双重借鉴和融汇。巴金的创作虽然有激烈反传统的一面,但其深层却有着与传统割不断的联系。即便如《家》,也在表达冲出旧家庭束缚之强烈愿望的同时,显现出与家庭割不断的血缘联系。而且其笔法亦多受《红楼梦》的影响。《寒夜》所创造的诗性意象和诗性暗示亦表现出与中国传统诗学的契合。
意境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抒情写意类文学形象的最高范畴,是一部作品作为经典存在的依据。宗白华认为,“意境不是一个单层的平面的自然的再现”,而是“从直观感相的模写,活跃生命的传达,到最高灵境的启示,可以有三层次”,“至于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后期印象派,它们的旨趣在第三境层”。[7]以这样的视角来观照《寒夜》与寒夜象征,我们可以看出寒夜、冷寂的街道、阴沉沉的白天、昏暗的灯光、痛苦的喘气与咳嗽、吐出的鲜血等等都是以寒夜为中心的意象体系;在这些意象背后暗示出的主人公的寒冷、痛苦、寂寞、自我麻痹式的安慰与绝望这些相对具体的当下体验感受与生存状态则是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这是作品意境的第二层涵义。《寒夜》之感人肺腑、震撼人心的原因则在其中的言外之意上。巴金的作品永远针对着束缚人们心灵的无形之网。他的作品充满了作为个体的人的情绪、人格、存在与作为制度的已经生活化的“情绪、人格、存在”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这样的制度就是一张无形的网。它压抑着无形的感情。而要挣脱这无形的网,必须以同样无形的生命洪流与青春之火去冲破它、焚毁它。在他的“激流三部曲”等早期的作品中,越要挣脱,就越感到压抑,感到这张“网”的束缚令人窒息,于是最后在高潮中爆发:“挣脱”的力量压过了“束缚”的力量。而到了《寒夜》,外界的无形之网无形之黑暗最终阻滞了主人公的生命洪流,泯灭了主人公的青春之火。自我心灵在挣脱与束缚两种力量间斗争、反抗、压抑、屈服、毁灭的过程正是《寒夜》所创造出的意境的言外之意。它是具体的、静的感官印象、心理感受、生活场景这些“有”背后的“无”,是“存在的生命”背后“生命的存在”,是静的生存状态背后动的生命姿态。它无形无象又无所不在,蕴于“有”之中,是真正的本体,它超越了具体的“有”而又包容“万有”。即便我们不再面对寒夜,即便我们不再生活于寒冷、痛苦、寂寞、自我麻痹式的安慰与绝望这些相同的生存状态之中,只要我们还没有获得彻底的自由,我们的心灵就始终需要在束缚与挣脱之间选择、挣扎。这就是《寒夜》作为中国现代诗化小说的经典所带给几代读者的意义和价值,也是“寒夜象征”所最终指向的康德所说的有别于客观普遍性的“主观普遍性”。
在这个象征结构与意境中,巴金显示出了他的人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不是我们一般所理解的对小人物的同情与关怀。一个人并不是天生的懦夫,汪文宣曾树生的过去也许就是《家》里冲出家庭寻找新天地的觉慧、觉民、淑英们。是他们在束缚与挣脱间的徘徊、犹豫、软弱、动摇、崩溃这一系列心灵过程把他们自己变成了悲剧人物。“寒夜”作为他们的主观宇宙是一个必须超越的对象。“人是靠追求超越的目标才得以存在”,“我们必须提醒人除了他自己外,别无立法者;由于听任他怎样做,他就必须为自己作出决定……必须始终在自身之外寻求一个解放的……目标,人才能体现自己真正是人”。[8]这个悲剧强调行动与选择的重要,接近于存在主义,表达出人必须为他的心灵在束缚与挣脱间选择挣脱,选择超越的思想,这正是其人道主义精神的真正所在。
在《寒夜》对中西诗学的双重借鉴中,“寒夜象征”与“寒夜意境”一方面扬弃了西方象征主义诗学中“超验本体论”的超验属性,将表现本体由神秘的观念性本体世界转移为感性生命体验中当下此在的流动的心灵;另一方面又在意境风格上与中国古典诗学的相应传统有所区别。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寒夜这样一个意境从未有过如此丰富的多重意蕴,也从未与个体的生命体验有过如此紧密的交融。从《诗经》中的“?G彼小星,三五在东”,到《古诗十九首》中的“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到《短歌行》中的“月明星稀,乌鹊南飞”,到《咏怀》中的“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帏鉴明月,清风吹我衿”,到《鸟鸣涧》中的“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到《雨霖铃》中的“杨柳岸,晓风残月”等等有关寒夜的诗歌,或是把寒夜作为一个时间概念,或是重点写夜下具体的景物,或是以寒夜暗示自我的心绪。寒夜虽然有凄清幽冷之处,却与主体处于和谐状态,其普遍的审美特征是单纯、静谧、空灵、幽深。而《寒夜》中的“寒夜意境”虽然也包含了以上部分涵义,但有很大的不同,它是冷酷的、无法摆脱的,压抑着主体,与主体处于冲突之中。《寒夜》中的意象与意境营造在继承古典文学传统的同时也显示出审美风格的现代性转变,即由单纯美转向深刻美,由和谐美转向扭曲美,由亦真亦幻的空灵美转向此岸世界的真实美。
《寒夜》是中国现代诗化小说的经典,它创造了独特的“寒夜体验”,由此出发,构建作为文本中心的“寒夜意象”,并最终上升为“寒夜象征”与“寒夜意境”。然而不少文章在谈及鲁迅、废名、沈从文、冯至、汪曾祺等人小说的诗化特征与由此形成的风格脉络时,却遗忘了《寒夜》。我认为,诗化小说可以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可以说是诗的小说化,如鲁迅的《社戏》、萧红的《呼兰河传》,基本上没有什么连贯的情节,大段大段地写景、状物、造境,实际上是扩大的诗;另一类偏重在小说的诗化,一方面还保留着通常的人物、情节、矛盾冲突,同时又将它们置于一个中心意象或情绪的统率之下。《寒夜》属于后者,郁达夫的小说也是如此。沈从文则两类兼而有之。这两种类型的共同点就是都必须以生命个体的当下感受体验为出发点,由此还不同程度地包含了对现实世界的排拒与疏离。因此,研究诗化小说的意义不仅仅是对作品进行重新整合与分类,也不仅仅是单纯的研究对象的转移,它还意味着对文学的新的阐释方法和再认识。
注 释:
[1]转引自曼生:《别了,旧生活!新生活万岁!—评巴金的〈憩园〉》,《巴金作品评论集》第327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12月第1版。[2]参照朱光潜:《西方美学史》第35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11月北京第2版。[3]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煦良译,《萨特哲学论文集》第123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4]同注[3],第134页。[4]王国维:《人间词话》第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5]黑格尔:《美学》第二卷第10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1月版。[6]参见黄曼君:《民族新文学性格的重塑和再造——浅议四十年代文学现代化、民族化的历史进程》,《双子星座——鲁迅郭沫若与新文学主潮》,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7]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艺境》第7-8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8]同注[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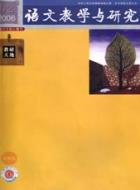
- 语文教学与语文科研 / 赵群筠 徐载梅
- 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 / 梅丽玉 江建林
- 别具一格读新诗 / 丁晓梅
- 用预设打造精彩课堂 / 蒋金涛
- 语文课堂要脚踏两只船 / 庄小兰
- 语文教学原则研究的三个误区 / 彭 豪
- 出错也可以扮靓文言文教学 / 钟旦生
- 古典诗词教学中的审美教育 / 冯爱军
- 王维山水田园诗的美学特征 / 吴清华
- 例说语言的感悟和习得 / 郑永红
- 词语锤炼规律初探 / 王国美
- 微观语感的训练与培养 / 李晓华
- 考试异化忧思录 / 邓玉阶
- 用问题教学法分析《曹刿论战》 / 李书芹
- 抓住“变”字教《故乡》 / 廖海鳌
- 以《孔乙己》为例谈小说的教学 / 李春颍
- “月亮文化”综合实践活动课案例 / 朱月君
- 我教《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 潘文富
- 考场作文升格的有效途径 / 张士文
- 中考记叙文写作的指导策略 / 贾为峥
- 考场作文形象化议论技巧 / 张爱武
- 细节描写应该注意的若干问题 / 李宗学
- 建构个性化作文评价的新体系 / 王先海
- 新课程需要怎样的语文课堂教学 / 张建杰
- 《寒夜》:中国现代诗化小说的经典 / 金立群
- 多媒体进入语文课堂后的怪现状 / 鲁伟政
- 课堂提问的琐屑化现象透视 / 徐忠祥
- 语文课堂教学中的四大流弊 / 侯凤英 陈继承
- 语文课改中的媚雅现象 / 傅宜炼 罗艳霞
- 实行互动写作的尝试 / 丁金华 王美荣
- 四步作文法实验总结 / 陈相元
- 周记式作文评语的交流功能 / 王跃华
- 架起作文讲评的立交桥 / 庞培刚
- 有效干预学生写作的心理异化 / 吴彩葵
- 作文教学应追求过程管理的效能 / 何成武
- 论文学作品中自我情愫的品味 / 高久云
- 从意象出发鉴赏诗歌 / 郭幼菊
- 体验式阅读应关注的几个前提 / 霍 铭
- 依据课文设计比较阅读的内容 / 吕嘉兴
- 在活动中让名著阅读走向纵深 / 余彩云
- 阅读教学要珍视学生的阅读初感 / 张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