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5年第9期
ID: 423134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5年第9期
ID: 423134
论“张良诗”隐逸主题的文化精神
◇ 史继东
摘要:张良被誉为汉初三杰之冠,他功成身退,善始善终的人生轨迹被后世无数诗人仰慕与咏叹。因此,以吟咏张良归隐为主题的“张良诗”代不乏陈,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这类张良诗对于张良归隐的观点大致有二:其一,认为张良旨在追求人格的自由与独立;其二,认为张良的目的在于避祸远害。其实,两种观点都融注了不同的诗人在不同的人生境况下对张良不同的认识。时至今日,张良的人格魅力仍使千载之后的我们咏叹不已。
关键词:张良诗 人格独立 避祸远害 吟咏
引言
张良,西汉初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与萧何、韩信并称为汉初三杰。“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已经成了张良的代名词。以至于宋人黄震在《黄氏日钞》中直称张良为“三杰之冠”。[1]张良作为帝王师的形象千百年来深入人心,因此在历代文人的诗集中对他的吟咏就代不乏陈。今天所能见到的吟咏张良的诗歌有近百首,而其中以张良功成身退而隐逸山林为主题的诗歌就不下30首,这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这一主题为何引起历代诗人的共鸣,他们对张良隐居的态度是否一致,有何差异,差异的原因何在,都有待进行深入的分析。下面具体进行分析,以求教于方家。
一、追求自由与独立人格
元代郭钰的《张良咏》就是将张良的归隐看做其自由独立人格的彰显。诗云:“昨日相从赤松子,今日已见淮阴死。控御天下汉业崇,不受控御真英雄。”[2]认为张良功成身退,不受任何势力的制约,追求独立的人格才是真正的英雄。在张良的人格中体现最多的是他对先秦士人优秀士风的继承和发扬。这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以匡救天下为己任。像孟子、荀子、韩非子等各派宗师莫不如此,即便是看似消极的庄子也不例外。张良虽然整日把“为韩报仇”当作自己入世的原因,但真正的“为韩报仇”却在那惊天动地的博浪沙一锥之后就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他为匡救天下而对刘邦殚精竭虑地辅佐。一直持续到汉朝的建立、全国的安定。
其二,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先秦杰出的“士”从来不屈体于王侯,而是以王侯的师友自居。张良与刘邦的关系在楚汉相争时期一直都是半宾客、半师友的关系。虽然张良认定刘邦是唯一值得辅佐的贤君,但另一方面张良又有意识地与刘邦保持着可进可退的距离,对此刘邦也是心领神会。刘邦平时说话极为粗鲁,对臣下动辄“乃父”,即便对吕后、萧何也不客气。然而对张良却非常地尊敬。通读《史记·留侯世家》中刘邦和张良的所有对话,刘邦询问前总是客气地称“子房”或“先生”。当刘邦取得天下,登上皇帝的宝座之后,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时候,士人再也没有良禽择主而事的自由,而是必须对皇帝效忠,这与张良追求独立自由的人格理想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他最终辞官归隐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后世诗人对张良的这种人格魅力多有赞赏。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李白《赠韦秘书子春二首》(之二) “徒为风尘苦,一官已白须。气同万里合,访我来琼都。披云睹青天,扪虱话良图。留侯将绮里,出处未云殊。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3]李白平生最仰慕的就是战国士风。他视天子如僚友,不走寻常的科举之路,试图以一席话感召皇帝,加卿相之位而平步青云,建功立业之后,归隐山林。这种人生理想与张良的人生轨迹是十分契合的。当时虽然已无实现之可能,但他仍然心向往之。此外还有张九龄的《商洛山行怀古》“长怀赤松意,复忆紫芝歌。避世辞轩冕,逢时解薜萝。”李商隐的《安定城楼》“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4]南宋隐逸诗人李弥逊《过留侯庙》“壮岁早从黄石计,功成却伴赤松游。当时不与人间充,应有文风静九州!”这些诗句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这种对建功立业与独立人格的追求体现了在中国古代儒道两家思想共同作用于士人内心的普遍现象。“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左思《咏史·其一》)这种人生范式是他们共同的追求。儒家提倡积极入世,希图做一番定社稷、安黎元的功业,由此设计了一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道路。而道家则蔑视功名富贵,追求精神的超脱与心灵自由。儒学这种只顾前进不讲后退的人生追求势必导致人生的由盛转衰。因此,道家哲学鼓励士人超脱逍遥,就成了对儒学思想的缓冲与弥补。所以,功成身退,既实现人的社会价值,又重视人的自然价值,也就成为士人心往神追的一种理想人生。
此外,也有诗人认为张良如陶渊明一样是“性本爱丘山”的。如陈子昂《答洛阳主人》:“平生白云志,早爱赤松游。”李德裕《余所居平泉村舍近蒙韦常侍大尹特改嘉名因诗以谢》:“未谢留侯疾,常怀仲蔚园。闲谣紫芝曲,归梦赤松村。”这些诗歌表现的是一种悠闲的佛道生活,然而,这主要是因为诗人在人生道路上遭遇到了各种挫折,故从积极进取转为遁世归隐,是以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因为,还没有任何资料表明张良天生有着纯粹的热爱山林之表现。
二、避祸远害的手段
避祸远害,在乱世与危急的环境中,保存自己的性命不受伤害,是道家黄老人生哲学的根本。而张良正是黄老哲学的化身,他用黄老哲学来进行人生的自我防护更是炉火纯青而游刃有余。
高祖十一年,张良正式向刘邦辞职归隐“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5]而这一年正月,韩信被杀;两月后,彭越被杀。因此张良借辞官隐居而避祸远害的用意就非常明显了。司马光《通鉴考异》对此评价道:“夫生之有死,譬犹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有超然而独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辨达理,足以知神仙之为虚诡矣。然其欲从赤松子游者,其智可知也……故子房托于神仙,遗弃人间。等功名于外物,置荣利而不顾,所谓‘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6]
因此,后代诗人认为张良是为了避害迫不得已隐居就非常自然了。如白居易在他政治热情高涨而仕途颇为顺利的前期对从赤松游的张良颇不以为然,曾嘲讽说:“乘舟范蠡惧,辟谷留侯饥。”(《裴侍中晋公以集贤林亭即事诗三十六韵见赠猥蒙征和才拙词繁辄广为五百言以伸酬献》) 但当他因谏捕捉盗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而得罪权贵,遭贬江州司马,真正认识到政治斗争的险恶之后,从而主动寻求归隐生活以避祸远害,唱出:“歌酒优游聊卒岁,园林萧洒可终身”(《从同州刺史改授太子少傅分司》)的诗句,最终认识到张良的睿智,充分地感受到了张良的归隐所具有的“避祸远害”的功能。唐代诗人徐寅在《招隐》中也写道:“陶景岂全轻组绶,留侯非独爱烟霞。”其中“留侯非独爱烟霞”便表明张良归隐的目的并不是纯粹为了喜爱山林与自由,而是为了避祸全身。贺铸《留侯庙下作》“岂眷万户封,仅与萧酇均,淮阴败晚节,顾亦非吾伦。愿访赤松子,逍遥云汉津。” (庆湖遗老诗集·卷三)将张良的善始善终与韩信的晚节不保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肯定了张良的人生选择。元代白朴《阳春曲·知己》说:“张良辞汉全身计,范蠡归湖远害机。”把张良和范蠡相提并论,指出张良的“辞汉归隐”“从赤松子游”和范蠡的“归湖泛舟”,虽然手段不同,但殊途同归,目的都是为了“全身”、“远害”,避祸自保。明代王恭《题张良归山图》也说张良归隐是:“如今悟得全身计,不似从前博浪沙。”清人王士祯《紫柏山下谒留侯祠》:“辟谷真从赤松隐,授书偶作帝王师。也知鸟喙逃勾践,未屑鸱夷学子皮。”张良了解刘邦猜忌功臣的心机与越王勾践一样,为了全身必须归隐远去,但他不屑于像范蠡那样改名换姓,逃亡异国(实际上也无异国可逃),而是以学仙修道的手段巧妙地避免了刘邦的猜忌,得以善终。
张良的这种选择在后世诗人眼中不光有飘逸绝俗的一面,同时也有无奈和悲情的一面。后世诗人对此体悟也很多。卢思道《春夕经行留侯墓诗》:“少小期黄石,晚年游赤松。应成羽人去,何忽掩高封。疎芜枕绝野,逦迤带斜峰。坟荒随草没,碑碎石苔浓。狙秦怀猛气,师汉挺柔容。盛烈芳千祀,深泉闭九重。夕风吟宰树,迟光落下舂。遂令怀古客,挥泪独无踪。”卢思道不再感叹张良作为帝王师如何春风得意,而是在“坟荒随草没,碑碎石苔浓”的凄凉中感叹人生的渺小与脆弱,而这感喟无疑有着鲜明的个人悲情色彩。宋代女词人朱淑真也有一首《张良》诗:“功成名遂便归休,天道分明不与留。果可人间恋驹隙,何心愿学赤松游。”更是将张良的归隐看成一种无奈之举,悲剧色彩更为浓郁。唐人费冠卿在《闲居即事》中写道:“子房仙去孔明死,更有何人解指踪”就是把自己人生际遇的困惑之感与张良的归隐结合起来,显现了作者对自己人生走向的无奈和迷茫。
结语
张良的人生历程契合了中国古代大多数文士的集体意识。对张良归隐的吟咏,表达了历代诗人们共同的生命向往,这是张良让所有吟咏者感叹不已的关键所在。从历代文士对张良归隐的吟咏中,我们看到了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张良的接受和对他完美生命轨迹的期待。他超凡的人生经历和过人的智慧,远远超越了他那个时代。一代又一代的诗人在张良身上寄托着不同的人生理想,直到今天,仍然给我们的人生以启示。
参考文献
[1]韩兆琦.史记选注集评[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2]宋嗣廉.历代吟咏《史记》人物诗歌选读[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
[3]王琦.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9.
[4]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4.
[5]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4.
[6]司马光.资治通鉴·元刊胡注本[M].北京:中华书局,1956.
【本文是陕西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汉代“汉中人物”综合研究》(项目编号:2013JK0449)阶段性成果。并受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科技创新团队资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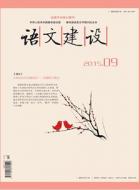
- 本真自由的诗意咏叹 / 苗珍虎
- 浅谈谢灵运山水诗的文学精神 / 赵培贝
- 基于认知语义学的词汇表征与语篇研究 / 杨俊霞
- 澳大利亚小说文学历程回眸 / 卢丙华
- 外国比较文学教学改革思路 / 张婧
- 谈新课标下语文教案特色 / 郭青
- 语文视角下“生态化”的大学传统文化教育路径 / 常晓薇 孙峰
- 论小学生情感培育中语文教学的作用 / 何芳
- 语文教学中高校学生管理能力的培育机制 / 王庆
- 妙用网络平台拓展语文教学多元化空间 / 徐志丹
- 英美文学阅读技巧对教学有效性影响 / 赵宁
- 古典文学教育对大学生思想教育的影响 / 王红玲
- 英美文学作品课堂教学设计研究 / 崔红霞
- 从安吉拉·卡特的作品看文化重塑与女性文学的创新性 / 向小蕊
- 用存在主义观点看苔丝的人生 / 郑长发
- 生活在别处 / 夏鹏铮
- 从《美国牧歌》谈英语教学设计 / 冯岩
- 普列姆昌德短篇小说结局的戏剧性与人性解读 / 苏玉仙
- 论《热爱生命》的生命主题 / 宋玮
- 论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灵魂深处的孤独 / 吴刚
- 劳伦斯诗歌中的自然生态美学思想探析 / 于晨凌
- 莫言长篇小说的主题与叙事评析 / 吕洁
- 莱辛《青草在唱歌》文本特点评论 / 乔阳
- 贾平凹小说创作中的乡土情结 / 赵勇锋
- 劳伦斯《儿子与情人》的叙事与创作结构 / 杜颖
- 《雨中的猫》中的女性主义体现 / 霍娟娟
- 重构非虚构 / 刘晓娟
- 语用学视角下《傲慢与偏见》的语言特色 / 张建华
- 论福克纳作品中的象征主义运用 / 周莹
- 托尼·莫里森小说《爵士乐》特征评析 / 孔晓丹
- 论作家戴维·洛奇小说中的喜剧特征研究 / 李晓荣
-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特点与人物塑造 / 刘英爽
- 网络文学与青年人文精神建构 / 朱晓燕
- 多元融合文学创作视角下《新格拉布街》的文学创作 / 蔡晓琳
- 论王尔德作品中的唯美主义语言表达 / 崔光婕
- 《论语》引《诗》论《诗》说 / 林莎
- 旷达与愁思的天然调和 / 卢如华
- 古希腊神话对英美文学创作的影响探微 / 莫小满
- 从宇文所安解读李白看其诗歌的跨文化接受 / 范娟娟
- 论“张良诗”隐逸主题的文化精神 / 史继东
- 节奏与声律的交融:寒山诗歌的音乐美探析 / 岳巍
- 唐代体育题材诗歌的文学性解读 / 梁娟
- 文学作品中比喻修辞格研究 / 孙静
- 从心理视点看人称指示语 / 施维
- 国际通识课程中文化因素影响下动词的比较学习 / 宋晓娟
- 从《京华烟云》的汉语助词“了”看英语的“时” / 汤君丽
- 互文顺应理论下的文学语篇表达研究 / 王海芸
- 论《安娜贝尔·李》文学语用视角探析 / 段丽娜
- 基于交际理论的应用语言学研究 / 李楠
- 英国作家戴维·洛奇小说叙事模式与语言风格 / 闫海燕
- 论钱钟书《围城》讽刺艺术的三个维度 / 周舫
- 现代汉语介词的语义功能与重要作用 / 秦岭
- 汉语介词的语用功能与结构研究 / 董晨峰
- 四行诗集《鲁拜集》的译作语言研究 / 李超
- 基于概念隐喻理论的语篇分析研究 / 赵茜
- 文学鉴赏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 / 程慧芳
- 简论大学语文教育与创新型外语人才的培养 / 张庆凯
- 英语教学中汉语语言迁移的作用与规制 / 胡敏
- 诗词鉴赏对大学生德育的提升作用探略 / 张利云
- 汉语教学方法对高校英语课堂教学的影响 / 宋平
- 汉语教学影响下的英语教学创新研究 / 杨正仁
- 汉语对日语语言文化的影响研究 / 邓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