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教学之友 2007年第8期
ID: 376233
语文教学之友 2007年第8期
ID: 376233
救赎与求索
◇ 胡华珍
“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像《祝福》这样的“旧书”,便是“不厌百回读”,可谓多读出新意,重读见深刻。在熟读深思中我捕捉到了重新解读祥林嫂人物形象及意义的两个关键词。
关键词一救赎
有关祥林嫂人物形象,一直是“反抗说”占着主导地位。的确,祥林嫂和《明天》中的单四嫂不同,虽然她们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都是活在封建社会底层的农村妇女,而且都是失子的寡妇,命运凄苦,但两人的人生态度有很大不同:单四嫂被动而麻木,只会呆坐空想;祥林嫂则非常积极、主动。其积极、主动主要表现为自我救赎,反抗只是她自我救赎的手段之一,自我救赎才是她反抗的最终目的。
祥林嫂第一次自我救赎是为免被卖从婆家出逃。第二次是再婚之日,以死相抵。这两次她都是以反抗的形式来进行自我救赎。
祥林嫂是被婆家娶进门给小她10岁左右的祥林当媳妇的,这在浙江称之为“等郎媳”或“抱郎媳”,而不同于一般人熟悉的童养媳习俗。娶“等郎媳”,是婆家出于想尽早抱孙接继的打算,也是想给家里添一份劳动力,同时也可以照看年幼的儿子。有一首民谣就唱出了“等郎媳”习俗的残酷性:“廿岁大姐十岁郎,夜夜困觉抱上床。说他夫来年太小,说他儿来不喊娘。等到郎大姐已老,等到开花叶又黄。”无论是“童养媳”还是“等郎媳”,都暴露了封建社会只重视女性的劳动能力与传宗接代功能的倾向。祥林嫂未必有过名副其实的夫妻生活体验,只是干活的工具而已,且早早成了寡妇。但祥林嫂逃出婆家的原因并非对这种劳苦的物质生活的不满,而是为了贞操节烈!认为夫妻关系永恒不变的观点,古已有之,最早见之于《礼记》“壹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为妻者即使死了丈夫也不再嫁,守住一生的贞节,称之为“节”;不管是已婚还是订婚,丈夫死时殉死,贞操将要被夺时以死相守,称之为“烈”。所以祥林嫂第一次自救为“节”,第二次自救为“烈”。从婆家出逃,再婚之日不同寻常的抵抗,就是为救自己免于成为不“节”不“烈”之人,正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通常,自救是免于自己受苦受罪受死,而祥林嫂的自救竟是为要受苦受罪甚至付出生命代价的“节”、“烈”二字!看看鲁迅先生的杂文《我之节烈观》吧:“节烈苦么?答道,很苦。男子都知道很苦,所以要表彰他。凡人都想活;烈是必死,不必说了。节妇还要活着。精神上的惨苦,也姑且弗论。单是生活一层,已是大宗的痛楚。”祥林嫂却为受苦受难的“节”、“烈”二字,绞尽脑汁、捶胸顿足、寻死觅活!不可思议么?《我之节烈观》一针见血:“只有自己不顾别人的民情,又是女应守节男子却可多妻的社会,造出如此畸形道德,而且日见精密苛酷,本也毫不足怪。但主张的是男子,上当的是女子。女子本身,何以毫无异言呢?原来‘妇者服也’,理应服事于人。教育固可不必,连开口也都犯法。他的精神,也同他体质一样,成了畸形。所以对于这畸形道德实在无甚意见……”祥林嫂的救赎心理及行为就是这种畸形道德的产物,这样的救赎注定是飞蛾扑火般的悲壮!
祥林嫂的这两次自我救赎最终并没有成功,还是“不幸”失了“节”,与第二个丈夫贺老六生了一个儿子“阿毛”。更为不幸的是,失了“节”的祥林嫂,又失去了第二个丈夫,又失去了惟一的儿子。失“节”失“烈”丧夫失子、没有了精神依托与理想守望的祥林嫂似乎应该已没有了自救的资本、能力和欲望了。但她在几乎遭遇了一个女人所有不幸的情况下依然没有消极承受生活给她的深重苦难,她选择了忏悔:向鲁镇的人们一再重复阿毛被狼吃掉的悲惨故事。“我真傻,真的,我单知道雪天是野兽在深山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她翻来覆去的絮叨带有原初性的宗教“忏悔”性质。这便是祥林嫂的第三次自我救赎。她以忏悔的方式向他人告白自己的过失,希望得到人们的原谅,借此使被击垮了的自己获得解救。可是在鲁镇,人们虽然对祥林嫂的自责与忏悔表示一点同情,但也止于听一听她的倾诉,而更多人把它作为无聊生活的一种调剂,祥林嫂的悲哀与忏悔成了“渣滓”,被人们所“唾弃”。环境的“凉薄”使祥林嫂的救赎再次“无功而返”。
不久她从鲁家雇来的短工柳妈那里听说,再婚的女人到了冥界会被两个丈夫争夺,为难的阎罗王只好用锯把这个女人锯成两半,分给他们。祥林嫂受到了更大的打击,这是她在山村里从未听说过的。但面对新的几乎是致命的灾难,祥林嫂再一次积极救赎。轮回转世、三世报应之说使原本执着于现世的祥林嫂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却也使对命运几乎要无可奈何的她,从三世报应说中又看到了救赎的希望。她听柳妈说去土地庙捐一条门槛作替身,让千人踏万人跨,可以赎罪,便哭着去求执拗的庙祝,终于得到许可,攒了一年工钱捐了门槛。这是祥林嫂第四次的救赎行为:捐门槛,赎自己这一世失“节”失“烈”剋夫剋子的“罪孽”,免得死了去受苦。此时的祥林嫂对现世已无奢望,自我救赎是为了轮回与转世。但倾尽了财力、倾注了生命的赎罪行为,结果会怎样呢?鲁迅先生在《我之节烈观》中作了回答:中国从来不许“忏悔”,女子做事一错,补过无及,只好任其羞杀。鲁迅在他晚年的一篇名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中强调“在中国君临的是礼,不是神”,在这里他想说的是:礼教不许忏悔。所以祥林嫂倾注生命的救赎行为结果被礼教之徒鲁四老爷不屑一顾:当以为已赎清了现世罪孽的祥林嫂在冬至的祭祖时节,坦然地去拿酒杯和筷子时,被鲁四老爷的太太喝止了。在鲁四老爷们眼里,祥林嫂永远是个不洁、不祥的女人,不洁是她失“节”失“烈”,不祥是她剋夫剋子。在土地庙捐一条门槛让人践踏就能赎罪的天真逻辑在现实中碰了壁,“不许赎罪”的礼教终于将祥林嫂置于无可救赎之死地。
求生不能、欲死不得的祥林嫂在她人生的末路,把她那根救赎的枯草投向了“我”:“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鲁镇的人们相信鬼,然而祥林嫂却疑惑了,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希望其有,是因为若去阴间便能见到失去的儿子;希望其无,是因为如果有“鬼”存在,必有地狱存在,那么就意味着要与死去的家人见面,而自己的身体被锯开的残酷事态将不可避免。因而“鬼”的有无,是祥林嫂在死前无论如何要搞清楚的切要问题,末路的祥林嫂还作着最后的挣扎与救赎。但“我”的模棱两可,“我”的“支吾”将这根救赎的枯草又抛还给了她。一手提着讨饭的竹篮,一手拄着开裂的竹竿,祥林嫂只能眼看着这根救赎的枯草随着雪花一起漫舞,最终粉碎在“豆一般大的黄色的灯火光”、“毕毕剥剥的鞭炮”中。
通过反抗、忏悔、赎罪的方式,祥林嫂一次又一次地进行顽强不屈的自我救赎——悲壮得令人心痛!卑贱的祥林嫂有一颗让人仰视的执著的心。
关键词二求索
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里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我在《祝福》中听到了先生“救救女人”的沉吟,这沉吟声中我又感受到了先生“我拿什么拯救你”的彷徨与求索。
祥林嫂畸形的自我救赎结果只是加快了她走向人生末路的速度。就好像一个被吊起来的人,不知道别人紧拉的绳子其实正是要把她勒死的那一根,还以为紧拉那根绳子就可以得救,殊不知结果是使自己死得更快,死得更痛。
自救不得的祥林嫂也无法得到她生存的集体的救助。鲁镇“祝福”之日的情景告诉我们:镇上的人们沉醉于各自利己的祈福之中,对祥林嫂这样孤独无依的人则缺少救赎的关心。鲁镇的宗教与道德为了自我防护而将祥林嫂这样“不洁不祥”的人无情地排除在外。
我拿什么拯救你?鲁迅先生在其《彷徨》的扉页上引用了《离骚》的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他在求索拿什么拯救这样悲苦的女人?他想唤醒她们,但他彷徨、犹疑了: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呐喊·自序》)这段话是鲁迅先生对于现状的绝望性的“确信”及对少数先觉者因觉醒而必定体验的无可挽救的苦楚的顾虑。过了激情“呐喊”期的鲁迅继而经历了“五·四”运动后新文化阵营分化的时期,原来参加过新文化运动的人,“有的退隐,有的高升,有的前进”,鲁迅当时像布不成阵的游勇那样孤独和彷徨,感到了无路可走的苦闷,但这也激发了他深沉的思考,求索的愿望:“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你看,唐朝的诗人李贺,不是困顿了一世的么?而他临死的时候,却对他的母亲说:‘阿妈,上帝造成了白玉楼,叫我做文章落成去了。’这岂非明明是一个诳,一个梦?然而一个小的和一个老的,一个死的和一个活的,死的高兴地死去,活的放心地活着。说诳和做梦,在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倒是梦。”这段话出自《呐喊》后《彷徨》前——1923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讲演《娜拉走后怎样》。所以在《彷徨》的第一篇——《祝福》开头部分,“我”面对祥林嫂所问的“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时,吞吞吐吐地回答:“也许有罢。”“那么,也就有地狱?”“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面对着这种追问,“我”含糊地支吾着迈步逃开。我想这“含糊地支吾”实在要好过激情、生硬的“没有”!因为如果唤醒了“熟睡”中的祥林嫂,告诉她有罪的是这个社会,世上也根本没有鬼神阴间却又无计可施无能为力,只会使祥林嫂毁灭得更惨烈。“含糊地支吾”虽不能救赎祥林嫂,但至少不给她悲苦的人生再添加“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无路可走的苦闷,至少还给她留着一个梦:去阴间便能见到失去的儿子。
“不要叫醒熟睡者”是痛苦的沉默,却是务实的选择,是当时的鲁迅上下求索所能达到的至高点。“不要叫醒熟睡者”表现了鲁迅与“呐喊”相应的启蒙期的结束与他自身称之为“彷徨”的新时期的开始,这时的鲁迅更冷静也更务实:“呐喊”唤醒“熟睡者”之前应该先找到让他们从“铁屋子”里出来的办法,否则就“不要去惊醒他”。其实到了晚年,鲁迅还在说“不要叫醒熟睡者”:“倘使我那八十岁的母亲,问我天国是否真有,我大约是会毫不踌蹰,答道真有的罢。”(《我要骗人》)可见,鲁迅终其一生都未能从这种顾虑中获得解脱,终其一生都在求索解救妇女的出路。
综上所述,祥林嫂这个人物形象的意义固然在于揭露了封建礼教的罪恶,但我认为更蕴藏了鲁迅先生对妇女解放问题深入而务实的思考,体现了他对如何拯救深受封建礼教毒害的祥林嫂们的有价值的求索。
掩卷而思,我感叹祥林嫂不屈的救赎,我敬仰先生不懈的求索,我敬畏会救赎会求索的民族!
(作者单位:宁波市北仑中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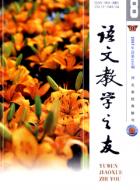
- 摆脱依赖 回归本真 / 陈子祥
- 教育不是迎合 / 张旺生
- 润物细无声 / 刘世敏
- 新课程实施中一堂好语文课的标准 / 张以民
- 课堂对话中信息流向和流量的调节 / 白花丽
- 提高农村学生语文素质的几点做法 / 吕传文
- 浅谈提纲法在背诵教学中的运用 / 贺币
- 略谈诵读体验对学生写作的促进作用 / 刘帅 张红美
- “嗟来之食”的教训 / 吴振华
- 文言文教学现代视角的切入点与文化传承的几点体会 / 林国雄
- 初中文言文教学串讲模式与探究模式比较及优化 / 陈晓桦
- 多读 多感 多悟 / 王俊杰
- 试论“读”的要义 / 施海刚
- 横看成岭侧成峰 / 王冬
- 中学语文教材英雄题材选文的分析与反思 / 曹亚平
- 理解 品味 创造 / 朱治国
- 读课文学作文 / 张俊伟
- 金龟子的“流苏”到底有什么作用 / 吴咏君
- 只是“我”的誓言吗? / 方金先
- “坐”在这里如何解释 / 邹德臣
- 含蓄的对比 远大的抱负 / 田新平
- 对《老王》中杨绛反思的反思 / 周长青
- “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应这样翻译 / 何绪宾
- 谈《风景谈》的风景美 / 代浩静
- 救赎与求索 / 胡华珍
- 杀了刘邦之后 / 文霈
- 路瓦栽——真正的大丈夫 / 温国强
- “怒发上冲冠”译句质疑 / 孙云
- 谈作文教学五“突破” / 黄丰坤
- 学生亦创造先生 / 唐群辉
- 广告语在作文教学中的应用 / 戴红燕
- 用“拇指”抒写精彩 / 王梦彩
- 2008年高考作文命题趋势及其对策 / 张正平
- 计时常识与古诗文阅读 / 高智 张 清
- 关注数量词 巧改病句 / 曹建才
- “空”字在古诗中的运用摭谈 / 成维
- 刘禅(chán)还是刘禅(shàn) / 王贵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