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教学之友 2007年第4期
ID: 359310
语文教学之友 2007年第4期
ID: 359310
《故乡》中的“三”
◇ 张伟堂 孙士兴
“长期研究数字的人会发现:数字中最神秘,最受青睐的大概要算‘三’了。在我国从许慎的《说文解字》到《淮南子·天文训》,历来注家对此都有解释。”①笔者在多年初中语文教学中,发现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领袖的鲁迅在其作品中“三”用得特别多。下面以《故乡》为例,说明大师运用“三”之精湛的艺术:
三个故乡
鲁迅的《故乡》中写了三个故乡:一个是回忆中的,一个是现实的,一个是理想中的。回忆中的故乡在作者眼中是一个带有神异色彩的美的故乡。它的美从三个方面可以感受得出来:这里有“深蓝”的天空,有“金黄”的圆月,有“碧绿”的西瓜。它是一个辽阔而鲜活的世界,这里有高远的蓝天,有一望无垠的大海,有广阔的沙地。它是一个寂静而又富有动感的世界,这里的夜是静的,大地是静的,人是静的。总之,“我”回忆中的“故乡”是一个美好的世界,是少年“我”美好心灵的反映,是少年“我”与少年闰土和谐心灵关系的产物。现实中的“故乡”是在现实社会生活的压力下,失去了精神生命力的故乡。这时的“故乡”是由三种不同的人及三种不同的精神关系构成:小说主要是通过闰土、杨二嫂与“我”的关系来反映人们之间的隔膜和苦难生活。儿时的亲密伙伴、忠厚老实的农民闰土,曾与“我”亲密无间,现在却恭敬地叫“我”“老爷”,使“我”感到“非常的悲哀”了。曾经那样美丽的杨二嫂,却怪腔怪调地说“我”“放了道台”,“有三房姨太太”,“八台的大轿”,弄得“我”“无话可说”。杨二嫂、闰土、“我”,三种不同的人及三种不同的精神关系,不仅反映了现实和过去的巨大的反差,也深刻地揭示了这种反差下的深层的意蕴。理想的故乡——“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这其中的沙地是“碧绿的”,天空是“深蓝的”,圆月是“金黄的”,这不正是小说中三代人追求的完美境界吗?总之,“第一个故乡是‘过去时’的,第二个故乡是‘现在时’的,第三个故乡是‘未来时’的”。”②
三种人物
《故乡》写了七八个人物,其中主要人物有三个:“我”、闰土和杨二嫂。“我”是一个小知识分子的形象,在文中是线索人物,起穿针引线的作用:(一)叙述者,即讲故事的人。(二)故事中的其他人物因“我”而存在。(三)“我”成为作者的代言,“我”的思想感情就是作者的主观意象。闰土是作者特意安排浓墨重写的中心人物,是纯粹的农民形象。正因如此,作者多角度对其进行了细致描写,由先前的开朗、聪明和可爱变成现实的迟钝、麻木,正如文中所说的“木偶人”。造成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是腐朽的社会制度。文中母亲和我的话就能证明:“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从闰土的话中也能体现出:“非常难。第六个孩子也会帮忙了……”这是他用血泪的语言在控诉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罪恶。这一点,不仅表现在他的物质生活上,而且在精神生活上也有体现:他向“我”家要的东西,也只有“香炉”和“烛台”罢了。闰土的前途给读者的印象是渺茫的。杨二嫂对闰土来说是个陪衬人物。“她是城镇小市民的代表。她的命运和遭遇,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的衰败、萧条和没落,揭示了社会破产的广泛性。因而,杨二嫂的形象,在更深的层面上开拓了《故乡》的主题。”③从前的杨二嫂,年青美貌,“擦着白粉,颧骨没有这么高,嘴唇也没有这么薄,而且终日坐着”,是这个小镇上出了名的“豆腐西施”。如今竟然变成了凸颧骨,薄嘴唇,“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且又尖嘴利舌的老太婆。这是多么惊人的变化。闰土和杨二嫂无疑是一把剑的双刃,在《故乡》的主题显示上,具有同等的力度。
三种生活
三种生活:即“我”辛苦辗转的生活,闰土的辛苦麻木的生活和像杨二嫂那样辛苦恣睢的生活。透视文中的“我”可以看出,虽然“我”不是鲁迅,但鲁迅的影子在文中却很浓,一生到处奔波,心情忐忑不安。闰土的生活——“非常难”,“脸上虽然刻着许多皱纹,却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他大约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只是默默的吸烟了”。而杨二嫂要想活下去,只能靠放纵自己,靠凶暴富,靠武力弱者来生活。以上三种人的生活都是在“辛苦”中残喘延息。他们的境地如此“辛苦”,不正是罪恶的社会造成的吗?
三代人
短篇小说《故乡》揭示的主题,不仅仅是对现实社会不满,也有对未来茫然的希望:不是希望于老人,而是托厚望于下一代罢了。文中三代人:杨二嫂和母亲,我和闰土,宏儿和水生等。前者是20多年前社会衰败的见证者;我们是社会腐朽的目击者和受害者;孩子们是社会希望的接班者。从人物的安排上,可以看出作者对上一辈只是轻描淡写,而把中国的前途信心百倍于后者,他们才是中国的希望和将来。正如文中所说:“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三种感情
即“我”对长辈的尊敬,对闰土的同情和对下一代人热情的关切。对长辈的尊敬,表现在“我”回故乡接走母亲及对乡邻的关心;对闰土的同情,从其性格的先后不同可以看出“我”对他境况的同情;而对下一代人是热情的关切,赋予殷切的希望,正如文中结尾所说:“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当然,不仅仅《故乡》运用“三”多,鲁迅先生其他的作品也擅长运用“三”。短篇小说《孔乙己》就是借助三个地点:酒店里,写他三次被取笑,表现其愚腐;酒店外,他与小孩嬉戏,表现其善良;丁举人家,他被辱打成残,表现其懒惰。另外,还有三种喝酒人:站着喝酒的短衣帮;坐着喝酒的富贵人;“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惟一的人”(孔乙己)。笔者在多年教学中发现,掌握鲁迅作品这些规律,抓住“三”,变化教法,进行教学,而不是墨守成规,同样会达到教学目的。
注释:
①谭英《趣文选读——数学篇》。
②《教师教学用书》第五册71页,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12。
③《语文教学之友》2006年6期《(故乡)中杨二嫂形象的主题意义》。
(作者单位:泰安岱岳区粥店中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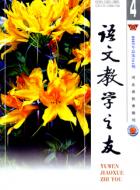
- 学会反思 / 屠 俊
- 新课标下写作教学现状的反思 / 李 琳
- 语文个性化教学探微 / 刘 方
- 优化课堂提问的几点实践 / 刘晓兰
- 浅析“精讲多练”在语文课改中的运用 / 张明伟
- 一举多得的小文段 / 储 俊
- 中学生阅读心理探究 / 詹海玲
- 教师在中小学生课外阅读中的指导作用 / 蒋军格
- 雕阑画础却分明 / 汪卫兵
- 游记散文教学的几个“切入点” / 潘进福
- 《滕王阁序》教什么 / 周巧麟 严志明
- 我教《邹忌讽齐王纳谏》 / 高颂民
- 塑造英雄 / 刘彦瑞
- 《罗布泊,消逝的仙湖》教学设计 / 范晓明
- 《故乡》中的“三” / 张伟堂 孙士兴
- 赏读《孔乙己》处处见匠心 / 陈维国
- 见证 参与 同情 / 祁俊来
- 此处怎能用逗号 / 牛玉霞
- 《过秦论》《鸿门宴》词句解释的几个问题 / 张 洁
- 《鸿门宴》教学札记二则 / 丁玉波
- 《谏太宗十思疏》主旨之辨 / 董 鸥
- 情采兼备 披文入理 / 石有平
- 《逍遥游》不宜作为高中讲读课文 / 赵继全
- 《苏武传》注释商补四则 / 孙富中
- 高语教材语病二例 / 张 翔
- 谈语文教材中插图的作用 / 王鹤森
- 怎样分析语文试卷 / 赵林瑶
- 在高考作文中展示语文综合素养 / 陈玉兵
- “三化”让你的高考作文“亮”起来 / 蔡 麟
- 你为什么会丢分 / 张国东
- 从中考命题看作文教学的走向 / 赵 莹
- 养情:写作前的必要准备 / 周志良
- 用活动提升学生写作水平 / 范美芬
- 善换角度 别有洞天 / 胥照方
- 怎样使作文语言个性化 / 杨海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