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9年第4期
ID: 135807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9年第4期
ID: 135807
语文知识教学的审视与反思
◇ 曹建召
主持人简介:王荣生,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学科教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执行主持简介:胡根林,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博士,上海市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评议论文]周庆元、黄耀红《语文知识教学的现状审视与观念批判》,原载《福建论坛》2008年第2期。
[原文提要]理解语文知识的内涵存在课程与教学两种不同视角。现代语文知识主要通过移植与引进、选择与创造而形成。从现代知识观的角度审视,目前占主导的语文知识观以追求客观、普遍与价值中立为表征,是典型的工具主义知识观。这种知识观所遵从的自然科学范式,往往湮没了语文知识的人文特性。
上世纪末关于语文教学“误尽苍生”的讨论中,“语文知识”系统、繁琐,以至于“变得比数学都精确”成了重点批判的对象。这也直接导致新课程标准提出“不刻意追求系统与完整”的要求。由此,关于语文知识教学的问题再度成为人们争论的热点。面对当前“语文知识”在教学与实践中的尴尬,反观百年语文学科发展,语文教学从没有知识,到逐步引入知识,建构语文知识体系,再到淡化知识,以至于目前没有有用的知识可教。对语文知识的现状进行合理的审视和反思是必要的。周庆元、黄耀红的论文从语文知识的源头入手,即知识产生的本源进行分析,提出了三个问题:语文课程到底要由谁来选择知识?怎样选择知识?什么样的知识最有价值?
一、谁来选择知识
课程开发者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科知识的取舍,不同历史阶段进入到教育决策层的教育研究者的经历、知识背景都会影响到知识的构成。“语文课程中的知识、权力关系,突出反映在选文及其阐释上。但语文知识的选择,也能折射出选择主体的价值倾向。例如,语言学家同文学家、文论家选择建构的语文知识,肯定有不同的偏好。同样是语言学家或文学家,所持的语言观、文学观不一样,构建的语文知识也会大相径庭。”①论文认为,知识的生产者可以这样来描述:由课程决策者、研究者与优秀实践者组成的课程研究共同体,他们从社会发展和个体成长的需求出发,根据集体创造的课程方案,从整个人类文化的知识谱系中精心选择和组织那些切合语文课程与语文教学的一部分知识,使之进入语文课程和教学,成为特定的“语文知识”。考察语文知识的生产者,主要有:学科专家、语文课程专家、教师和其他人员。其中学科专家和语文课程专家是语文知识的主要生产者,语文教育史上如叶圣陶、朱自清、吕叔湘、张志公等,在语言、文学等学术领域有一定的研究,同时又参与到学校语文学科的建设中来,使文章学知识、文学知识和语言学知识也构成了语文学科的主要知识内容。相比较而言,目前我们的语文教材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主要从编写队伍的构成来说,人员组成比较单一,以课程与教学专家为主体或学科教学专家为主体的教材编写,由于受编写者的视角所限,不可能把最鲜活、最具生命力的知识吸收进来。
二、怎样选择知识
由于语文学科缺少一个上位的“语文学”,故不可能像数学、物理学科一样直接从相关学科中选择知识,语文知识的生产则必然就涉及到组织的选择、重组、创生等。作者在文章中指出“现代语文知识来自于知识的移植与引进。在20世纪初中西文化冲突、激荡、 碰撞、交融的背景下,以现代面目出现的现代汉语、文学史、文学理论、文章读写理论是语文知识的主要提供者。中国现代学校制度在清末民初时期从西方移植而来。”引入与借鉴成为语文生产的一种方式。如第一部系统的文言语法著作《马氏文通》,就是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马建忠摆脱传统文字、音韵、训诂等传统“小学”研究的束缚,积极从西学中借鉴,进而探索汉语知识体系,著成《马氏文通》。全书系统模仿西方传统语法,同时也注重汉语实际。如词类系统,除了名字、代字、静字、动字、状字、介字、连字、叹字之外,增加了助字(语气词)。《马氏文通》的创作,体现了一种典型的借鉴式知识生产方式。我们认为,语文知识生产除此之外还应有:传统知识的继承,学术知识的选择,经验知识的总结和缄默知识的显现等方式。多渠道、多路径的知识生产,才有可能激活语文知识的源头活水,知识生产如果仅仅依靠几个专家凭自己的研究兴趣进行选择,这种生产方式还需要引起人们的思考。
三、什么样的知识最有价值
判断一种知识是否有价值自然涉及到知识观的问题。知识观是人们对知识的来源、性质、类型、价值、获得方式方法等的看法或态度。其实,我们是在讨论:我们现存的语文知识是谁的知识?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知识?这些知识为什么会受到质疑?是知识的问题,还是知识生产者的问题抑或是知识生产路径的问题?这都涉及到知识观的问题。人们对于语文知识的争论,与其说是语文知识的问题,倒不如说是由于人们对语文知识的不同认识造成的。文章指出:从本质上说,语文课程知识不是“自然科学”而是凸显个体性、隐喻性与价值多元性的“人文科学”。作为人文知识的教材决不同于理科教材中的“知识单元”,它是一个个独特的个性世界,是作者反思社会人生的深刻记录,是对于人生意义的体验、思考与表达,它引导人们通过语言的中介,进入一个象征与隐喻的意义世界。
不难看出,作者秉承的语文知识观超越了传统知识观所认定的客观性、普遍性和价值中立性的知识表征,而建立了个人的、隐形的、甚至是缄默的知识特征,显现出后现代知识观的特征。从后现代知识观出发,课程实施不仅仅是教育学专家、课程专家的专利,也不是行政部门的特权,而是由课程实施的两大主体——教师和学生一同建构、共同参与的活动。这种课程实施是一种实践取向的范式,是开放、互动、生成、发展的,是随着教育活动双主体的互动交往而不断展开、调整,不断发现、探索的,而不是固定、僵化的。②
上世纪50年代英国著名物理化学家和哲学家波兰尼在《人的研究》一书中写道:“人类有两种知识,通常所说的知识是用书面文字或地图、数学公式来表述的,这只是知识的一种形式,还有一种知识是不能系统表述的,例如我们有关自己行为的某种知识,如果我们将前一种知识称为显性知识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将后一种知识称为缄默知识”③。关注不可言说的知识,关注缄默知识成为当前知识研究的一个新的视域。知识观的变化必然引发语文知识内容的变迁。对于“最有价值语文”的回答,必须基于一定知识观的基础上,才能给予回答。如何开发教师、学生的隐性知识,如何让隐性知识显性化,如何积极利用隐性的教育价值成了教育的新问题。在语文学科中,如何开发一线教师的缄默知识,扩大知识生产者的构成,明确知识生产者的责任,多角度地开发语文学科教学内容知识,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评议论文]荣维东《开发科学有效的语文知识体系——以加利福尼亚语文教材〈文学:读者的选择〉为例》,原载《语文建设》,2008年第9期。
[原文提要]通过对加利福尼亚语文教材《文学:读者的选择》小说单元知识的分析发现,语文课程和教材不但可以拥有丰富的知识,还可以拥有系统而完整的知识。检视与思考我国的语文知识状况,必须经过继承、引进、整理和改造,才能完善我国的语文课程知识。
荣维东的这篇文章属于典型的借鉴性论文,论文通过对加利福尼亚语文教材中小说知识的分析,给我们的语文教学提出了严峻而又现实的问题:我们的语文教学不是知识教得太多,而是本来就没有什么知识可教。章熊先生说:“我越来越感到现行的中学语文知识体系需要改造,它们基本上是19世纪后期形成的,已经陈旧。”④韩雪屏认为“重要的不是如何教的问题,而是教什么的问题。”“不结实的知识概念体系难以支撑起高大的教育理念的框架。华美的理念外衣将终究覆盖不住苍白虚弱的躯体。多年来,关于语文教育的研究,更多的是在观念层面上运转,而没有真正触及语文教育改革的实质——知识的除旧布新。”⑤孙绍振指出“语文教育界关于文学的‘概念’至少落后二十年到五十年”⑥。王荣生在《新课标与“语文教学内容”》一书中更是集中描绘了当下语文知识的现状:语文课程与教学场上来回奔跑的基本上就一直是这些“超龄运动员”。在中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中,小说,除了被拧干的“人物、情节、环境”这三个概念,事实上已没有多少知识可以教了⑦。那么在语文知识的开发问题上,我们做了什么?需要怎么来做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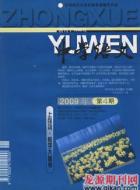
- 语文教育家顾黄初先生告别仪式在上海举行 / 徐林祥
- 烟花三月谢扬州 / 王松泉
- 并不遥远的记忆 / 高 潮
- 千万莫把佳作分析变成屠解文本 / 傅婷婷
- 油菜花的怀念 / 张正耀
- 民族命运的深沉咏 / 李兴茂
- 论如何打开文学作品的意义之门 / 王 飞
- 回忆恩师顾黄初 / 孙慧玲
- 《你听,多美》作文讲评课堂实录 / 顾小兵
- 语文教学设计的新意与规范问题 / 成 龙
- 论树立批判意识 / 王卫东 姚美娟
- 使动:课堂教学的关键词 / 林忠港
- 任务驱动教学法在阅读教学中的运用 / 吴蔚萍
- 尊重语 / 陈菊飞
- 确立目 / 周 鸾
- 新课标下作文写作要求的淡化 / 王玉行
- 让语文教育实现对生命的成全 / 甘玲珑
- 语文课外阅读指导探步 / 宣其燕
- 浅谈新课程背景下的个性化作文教学 / 刘冬梅
- 删繁就简求本色 / 李新平
- 议论文事例论据展现方式例说 / 李思衡
- 病人别里科夫 / 赵晓非
- 孔子的教育之道(四) / 韦志成
- 这是一道风景 / 史绍典
- 关于树的诗文赏析(二) / 孙绍振
- 语文知识教学的审视与反思 / 曹建召
- 纯是一片至性语 / 李志良
- 对语文教育本质的追寻 / 张玉英
- 错综:诗美的语言选择 / 邓嗣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