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9年第4期
ID: 135810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9年第4期
ID: 135810
对语文教育本质的追寻
◇ 张玉英
严密的逻辑推理、严谨的学术品格、大胆的批判精神使李海林成为20世纪末21世纪初最富有理性、充满思辨的语文教育专家之一。他主张语文课就是言语课,言语活动是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因此语文实际上就是人的一种语文生活,而语文教育,在本质上,就是一种语文生活教育。人性的发展有三个层面,即工具智慧、情意智慧和言语智慧,人的语文生活需要的正是这种言语智慧,语文教学的真正独特价值,就在言语智慧教育上。这种所谓的言语智慧的心理表现就是语感。语文教育通过语感这条途径,实现着言语智慧教育的目的,从而实现语文教育的人类学价值和目标。“语文生活化”、“言语智慧”、“语感”这三个基本范畴,就构成了李海林言语教学论的理论核心。
一、语文课堂教学生活化
语文学习的内容是言语,语文学习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李海林认为,言语能力是积淀的产物,而积淀有两个心理学前提,一个是主体的亲历性,学生主体必须“真实的”参与言语过程,也就是学生必须有真实发生过的言语内化心理过程;一个是环境的“真实性”,语文教学必须为主体的“真实”的言语活动提供同样“真实”的言语环境。这两者都要求“真实”的言语活动,那么最真实的言语活动在哪里呢?他说在生活中。
正如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所说: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没有生活做中心的学校是死学校;没有生活做中心的书本是死书本。可见,生活是学生进行有效学习的基础,更是关键。但教学和生活还是有区别的,我们不能将语文课堂搬到社会生活中,也不能将社会生活都搬到语文教学中,因此,语文教学生活化就成为一条实现教学和生活连接的途径。
语文教学生活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教学内容贴近生活,一是教学策略取法生活。
李海林把语文教学生活化是作为一种教学策略提出来的。他在《言语教学论》中指出:“生活化”不同于把语文课堂搬到社会,而是把生活中的某些要素“引入”课堂,从而实现课堂内与课堂外的沟通,变课堂为言语交际的场景和处所,变讲授型课堂为交际型课堂,变知识型课堂为言语应用型课堂。
而且,李海林对“引入”作了进一步的说明:这种“引入”分为两种,一种是“事件性引入”,一种是“功能性引入”。
所谓的“事件性引入”,就是直接将社会生活中即时发生的事件与课堂内的语文教学事件联系起来,语文教学课堂成为社会环境系统的一个组织部分,从而赋予语文教学课堂以社会真实环境的性质。我们来看李海林的一个教学片段(选自《中国当代诗四首》的课堂实录):
师:前几天我正在备课,看到一则广告借用了韩东的《山民》里的意境。我放给你们看看。
(录像机放中央电视台关于移动电话的一则广告,情节大致是一个孩子问父亲大山的那边是什么,父亲说是山;孩子又问那座山的那边是什么,父亲仍回答是山。若干年后,孩子长大了,走出了大山,来到了海边,用手机拨通父亲的电话,告诉父亲自己见到了大海,并请父亲听大海的声音。)
师:这是一则移动电话的广告,广告做得蛮好,那好在哪里呢?——我觉得就好在有点诗意。我们一起来学习韩东的《山民》。
李海林运用生活中的一个移动电话广告的引入来营造一个生活化的教学环境,将遥远的山民与我们的生活进行了连接,封闭落后的山民与广告中的父亲形象不谋而合,语文课堂的探究、对话、交流也就不再那么遥不可及,言不及义,学生可以就广告中的父亲来解读山民形象。
所谓“功能性引入”,就是根据言语交际的功能需要,转变课堂教学事件的功能性质,使课堂教学事件变成言语交际事件,从而创造出一种言语交际环境。这类的例子很多,钱梦龙老师的《巧用教学挂图》,李明珍老师的《当一次“导演”》,汪兆龙老师的《第一次配音》……在这里,学生由被动的学习者变为有特定“角色要求”的活动者。在这种“角色要求”的规范下,学生带着特定的、具体的言语任务,朝着特定的、具体的言语目标,开展特定的、具体的言语活动。
这两种参照社会生活的存在方式的“引入”,不仅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活泼教学形式,更重要的、对语文教学更具有本质意义的,是它们创造了“真实的”言语交际环境,使学生的言语活动更加有效。
正如王升先生所说:“不管目的指向什么,我们不得不承认,对学生来说,教学就是一种此在的生活方式。我们必须从学生现实生活的角度去设计现时的教学,这样教学就会充满生活的情趣和生命的活力。”
二、言语智慧
李海林言语教学论的基本命题是重新确立语文教学论的语言学基础,变以“语言”为主体的本体论为以“言语”为主体的本体论。既然语文教学的本质对象是言语,那么,言语的本质也就决定着语文课的性质。言语的本质是什么?李海林认为言语的本质在语言和思想的组合;既不在语言也不在思想,而在二者的组合上。这一点从根本上使以言语为本体的言语教学论超越了二元论的笼罩而获得崭新的起点。李维鼎先生曾特别的指出:“言语是什么?作为行为,是言与意的转换。作为作品,是言与意的统一体,即转换后的成品。言与意的关系决定着言语的性质。”
因此语文课的本质属性也应该是不在语言上,也不在思想上,而在二者的关系上。那么,在语文课中,语言与思想二者关系的着眼点在哪里呢,即语言与思想是通过什么进行转换的?这是语言学上要讨论的问题,更是语文学上要讨论的问题,它将为我们的语文教学提供一个可以从外部操控、运行的现实的切入点。
李海林从心理语言学的角度将这个中间环节称之为“内部言语”,这是人特有的一种心理智慧,由于这种智慧的对象是言语,所以我们就将之称为言语智慧。当然这种言语智慧是通过“思想—内部言语—外部言语”的生成过程实现的。
语文课程的客体是言语作品,语文课程的价值意义在于:人通过对言语作品的活动实现人的现实的生成。这种对言语作品的活动不是别的,就是言语实践。既然言语实践的人性追求是言语智慧,言语作品即言与意的统一体的最终价值也就指向了言语智慧。李海林通过上面的一番推论得出,语文教育是以言语为对象的人性智慧教育,也就是说,语文教育就是言语智慧教育。
语文教育=言语智慧教育(即语文=言语=言语运用),可以说是李海林语文教育思想的理论核心,通过对它们的论证,李海林完成了对语文工具论的批判,重建了语文的本体论。
在他之前,人们总是把眼光放在语言知识教育上,或者是语言文化教育上。语言知识教育论的语文课程观是学语言,语言文化教育论的语文课程观是学文化。它们都不是学言语,前者实际上把语文的本质属性定位在工具性上,后者把语文的本质属性定位在人文性上。
李海林突破了这个巢臼,将语文的本体由“语言”转向了“言语”,超越了语言观下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的二元论,建立起言语观下的“言语智慧论”,站在一个新的视角为我们的语文教学指出了一条新的探索之路。
三、语感教学
“语文即言语”是一种广义的语言学命题,对语文教学来说,它还过于抽象,还不是语文教学本体的实在规定,还少了点语文教学研究所要求的实践“操作性”。
语文=言语=言语运用,是李海林对语文教育=言语智慧教育的语文学解读,但是当语文指向言语或者言语智慧时总还有着浓浓的语言学色彩,而当语文指向言语运用的时候就指向了语文学,并将语文教学推向了实践。
李海林在《言语教学论》中对言语智慧进行了心理学的分析,他认为,从心理学意义上,言语智慧是言语知觉、言语记忆、言语思维、言语感情、言语个性等方面的统合,心理统合的成果就是语感。语感作为言语智慧的心理机制的客观存在,言语智慧的操作过程就是语感,即言语智慧形成=语感养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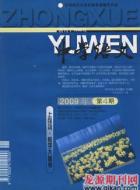
- 语文教育家顾黄初先生告别仪式在上海举行 / 徐林祥
- 烟花三月谢扬州 / 王松泉
- 并不遥远的记忆 / 高 潮
- 千万莫把佳作分析变成屠解文本 / 傅婷婷
- 油菜花的怀念 / 张正耀
- 民族命运的深沉咏 / 李兴茂
- 论如何打开文学作品的意义之门 / 王 飞
- 回忆恩师顾黄初 / 孙慧玲
- 《你听,多美》作文讲评课堂实录 / 顾小兵
- 语文教学设计的新意与规范问题 / 成 龙
- 论树立批判意识 / 王卫东 姚美娟
- 使动:课堂教学的关键词 / 林忠港
- 任务驱动教学法在阅读教学中的运用 / 吴蔚萍
- 尊重语 / 陈菊飞
- 确立目 / 周 鸾
- 新课标下作文写作要求的淡化 / 王玉行
- 让语文教育实现对生命的成全 / 甘玲珑
- 语文课外阅读指导探步 / 宣其燕
- 浅谈新课程背景下的个性化作文教学 / 刘冬梅
- 删繁就简求本色 / 李新平
- 议论文事例论据展现方式例说 / 李思衡
- 病人别里科夫 / 赵晓非
- 孔子的教育之道(四) / 韦志成
- 这是一道风景 / 史绍典
- 关于树的诗文赏析(二) / 孙绍振
- 语文知识教学的审视与反思 / 曹建召
- 纯是一片至性语 / 李志良
- 对语文教育本质的追寻 / 张玉英
- 错综:诗美的语言选择 / 邓嗣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