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06年第7期
ID: 81514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06年第7期
ID: 81514
文学教育应多些自我设难
◇ 余岱宗
从事文学教育工作,经常碰到的一个难题是,任何一种文学理论的大概念,总是与具体而微的文学阅读感受无法非常熨帖地、严丝合缝地融合一处,这一点都不奇怪。文学理论的种种概念,是从浩瀚的文学作品中抽象出来的。有了概念,方能互相交流,读者A才可能与读者B、C、D分享阅读文学作品的喜悦、忧伤或愤怒。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一书第20节提出的“一个鉴赏判断所要求的必然性的条件是共通感的观念”,所谓“共通感的观念”,就文学教育而言,就是文学教育者与被教育者需要拥有彼此都可理解的术语、概念。
但是,这个“共通感的观念”,通常并没有办法穷尽具体的文学作品,或者说,某一“共通感的观念”,只能阐释作品的某一方面特征,甚至是某种与其它作品共有的特征。比如,应用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的一个理论术语,说王熙凤是一位“圆形人物”,这是对的,但被教育者会觉得很不过瘾。为什么呢?王熙凤的确是个八面玲珑的“圆形人物”,但这个“圆形人物”与薛宝钗或者宋江这样的“圆形人物”区别在哪里呢?这就需要新的概念引入,才能区分“圆形人物”之间的区别,才可能比较充分地解读王熙凤的特殊性。
但是,如此一来,哪怕发现、创作了比“圆形人物”更次一级的理论术语以分析王熙凤形象的特殊性,还是面临着概念大于形象的危险,因为一个概念如果仅仅适用于王熙凤,这个概念未免太狭窄了。所以,诠释王熙凤,总是在一个概念之下,尽量地再引入专门属于王熙凤的某一概念,如此一来,对于王熙凤的形象的解读便在诠释的链条上一路滑行。如果诠释之后,还要再对诠释进行更细致的诠释,没完没了,这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做到。但是,追求对文学形象独异性的解释,这样的动机和努力并不能放弃。
那么,剖析文学形象或意境的独特魅力,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思路贯彻到文学教育之中?笔者以为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自我设难。通过自我设难,通过形象、情节、语言、意境的比照,才可能发现某个作家或作品的独异性——自我设难的目的在于定位。事实上,伟大的、丰富的、多义的文学形象,是难以言尽的,但难以言尽不等于放弃解析,难以言尽更需要不断地比照。第一次说王熙凤的形象是“圆形人物”的人,就是拿扁平人物与圆形人物进行比较,这样的发现是相当具有创新性的,因为这样的论断,将性格的丰富多面与否作为审美判断的重要指标。然而,今天如果还拘泥于这样的判断,那么命名就太粗略了。或者说,第一次使用“圆形人物”这个概念来阐释王熙凤,我们说这样的命名是有眼光的。然而,第二次,第三次,第N次再说王熙凤是一个“圆形人物”,恐怕就意味着阐释者的无能了。文学的解读,不可能不照顾到历史语境,文学的比照同样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比照。
进一步的解读者,如果说出王熙凤这个“圆形人物”其“圆形”之中,其实包含着某中偏执,她的多面性之中内含着难以遏止的贪欲强迫症,她的“圆形”是表面的,她的内心里亦有突出的“扁平”特征,她的多面性,依然是被某种欲望的固执性主导着,进而推导出所谓的“圆形人物”的多面性中的固执性,那么,研究者便找到了“圆形人物”的非圆形特征。这就是说你已经不满足于福斯特所言的“圆形人物”这个概念的内涵,开始自我设难,力图挣脱某种概念的束缚。假如你进一步发现,圆形人物的内在的固执性是常态而非变态,各种各样的圆形人物的内心中都具有某中固执性,那么,你就从例外的发现跨入了寻求新的理论建设的阶段,从边缘的发现走向中心的建构。
为什么文学教育中的教育者的自我设难应该是一种常规手段而非偶一为之的特别方法呢?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理论,总是尽力抽象、概括某种现象或某种存在。这就是说凡是理论总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理论缺乏普遍性,不能适用于一定范围,就不是理论了。但是,这一普遍性遭遇特殊性时,我们应该如何处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呢?我们说“天鹅都是白的”,这样的判断其实就是一种理论推断。但是,这个理论是有前提条件的,只要发现有一只天鹅是黑的,这个理论就被推翻了。我们就应当说“绝大多数的天鹅是白的,但也有少量的天鹅是黑的”。如果我们发现了除了白的、黑的天鹅之外,还有其它颜色的天鹅,关于天鹅颜色非黑即白的理论又要修正。可见,任何理论,都要处于不断地被检测,被“试错”的过程中。
实践的意义,不仅在于检验真理,更在于修正理论,修正“真理”。因此,从事文学教育,也要抱着一种不断检测理论的可行性的态度,不断地去“寻找例外”。“寻找例外”就是教育者自我设难。自我设难是澄清问题的捷径。
再者,自我设难,是文学教育设定、贯彻逻辑性的内在要求。自我设难,意味着不断为文学教育者的立论做出辩护,辩护的目的在于维护论点的正确性。让初始的论点跨越一个又一个“障碍”,让与初始论点有可能发生冲突的观点和论据纳入你的论证框架之内。第一,这能澄清表面上可能对你的观点造成不利因素的观点论据,让你的立论更站得住脚;第二、如果自我设难的确无法使得不利于你的观点论据“臣服”,反而君临于你的初始观点之上,即反对性的观点论据显得更有力,那么,这就意味着你该拓宽、修正甚至根本性地改变你的初始观点,那么,这个“自我设难”的“难”就不是思路的障碍点,更是让你思考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弹跳点;第三,自我设难,通常是问题的逐步的显山露水,是一个问题接着另一个问题的环环相扣,所以,自我设难,就是自我对话,是一个相关、相对,特别是相反的立论在思维的行进中不断被审视、被辨析、被吸纳入思考的范围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以有利于自我论点的论据来证明自我的正确,相反,与潜在的对手对话,与可能的冲突的观点商榷,才可能真正让自我的立论站得住脚。虽然,自我设难,并不是要求论者都一定要推翻所有现成的概念,另起炉灶——毕竟,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所谓的“范式转变”(paradigm shift)需要积累,而不可能单单靠自我设难就能实现。但是,自我设难的存在,至少表明你的文学教育理念不是完全依靠直觉,而是进入一个逻辑辨析的过程。在这个逻辑辨析的过程中,自我设难就是检验你的观点是否恰当,能在何种时间范围和空间范围内适用,是否恰到好处地推断出你关于某个形象或某个意象的特点呢。自我设难,是防范性的进攻,或者说是在进攻过程中的积极防范。即论者应预期性极强的发现自我论点可能存在的漏洞,通过自我设难,明确地排除观点中不利于自己的论据,或者将表面上不利于自我的论据通过理论上的论证证明这样的论据恰恰会进一步证明自我观点的正确。
比如,青年学者孙勇进在《祸水话题》一文中提出《水浒传》中的妇女观念是典型的男性中心思想这一论点。以为水浒世界里的女性,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妖女,一类是魔女,一类是无面目女性。妖女是那些美而不好的女性,如毒死武大郎的潘金莲,私通裴如海的潘巧云,私通管家并陷害卢俊义的贾氏,给宋江带绿头巾的阎婆惜,卖俏行凶的白秀英,陷害史进的妓女李瑞兰,等等,等等,这些女人大都薄有姿色,但一个个全都是桃红陷阱,不知陷翻了多少好汉。魔女是“好”而不美的女性。说“好”,是指可以进入好汉级别,能在水泊梁山大寨中坐一把交椅,说“不美”,是其女性的生理特征和心理特征一概全无。水浒世界里就出现了两个此方面的典范:一个是母夜叉孙二娘,一个是母大虫顾大嫂。除此以外,还有一大批无面目女性。如为赔偿损失而嫁给霹雳火秦明的花荣的妹子,人们或许可以从她的文秀的哥哥花荣来推断,她大概容貌和品德都不错,说不定还是上选,但这也仅仅是推测而已,实情如何,不得而知。单是如此分析《水浒传》中的女性,似乎已经全面。但自我设难接踵而来:《水浒》里也不见得就没像样的女人吧?比如林冲的娘子可说美而又贤,扈三娘漂亮而又英武,再有那个被鲁智深救了的金翠莲心肠也不坏,知道感恩图报,这又怎么说?
[##]
论者道:“金翠莲是不坏,但她地位低下,她的幸福(而且还只是做人外室的幸福)全出于好汉的恩赐,属于卑微的众生阶层,毫无独立人格可言”,“林冲娘子的确是美而又贤,但她的花容玉貌却是惹祸的根由,夏志清先生认为林冲发配上路前写下休书是“下意识地责备妻子为他带来这许多麻烦”,这也许是一种过度诠释,但将林冲故事放在水浒世界这一大“语境”来看,说林冲娘子的美貌客观上给好汉林冲带来了麻烦,也还是说得通的”,而“扈三娘英武而又漂亮”,这都没问题,但水浒世界赋予她的命运却大成问题。扈三娘原是扈家庄千金小姐,她的原许配对象祝彪也年轻勇武,她原本的人生命运,套用一句现代的文艺词儿来说,充满了玫瑰色。谁知造化弄人,三庄联防竟会被各个击破,祝家庄主满门尽灭,她本人被俘,一门老幼又被李逵两把板斧砍瓜切菜般杀了个一干二净,只跑了哥哥扈成。身遭如此灭家惨痛,却又被梁山二寨主宋江做主,许配给了她的手下败将猥琐不堪的王矮虎。这样的论述似乎已经比较周密地阐述了女性在《水浒传》中的地位了,但还没完,紧接着问题又来了:也许会有哪位朋友说,《水浒传》轻鄙女性,是因为中国古代女性的地位一向很低,素有轻视女性的文化传统。但这话也只说对了一半,中国古代现实社会中的女性地位低,并不必然导致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地位低,恰恰相反,文学世界里照样可以有很多光彩照人的女性。的确,中国文学从《诗经》、《楚辞》起,就一直待女性不薄,在文学世界里出现了许多可敬、可爱甚至可崇拜的女性,如《西厢记》,如《牡丹亭》,如《桃花扇》,如才子佳人小说,如《红楼梦》,尤其是《红楼梦》中的钗、黛、湘云等更是不知颠倒了多少男性。即使是文学作品中金戈铁马的尚武的世界,仍可以有女性大显身手,例如代父从军的花木兰,例如杨家将系列故事里的杨门女将,可说占尽风头,无限风光。所以,此处的再次自我设难,将《水浒传》中的妇女观的特殊性放在整个古代中国文学的历史语境中来考察,将问题引向深入。或者说,前面的设难是小说文本内部的微观定位,而这个问题的设难则是将文本放在宏观环境中定位。最后,文章得出结论,以为《水浒传》对妇女的态度是特殊社会群体或阶层(游民)的价值观和人生理想的体现。但到此层次,论证还未完成,论者为了更显严密,还特别交代:“这种排斥女性的英雄故事的格局后来出现了重大转变。清代出来个文康发愿要写一部书,既有《水浒传》的侠烈故事,又有《红楼梦》的悱恻情缘,于是女侠十三妹便在《儿女英雄传》中出笼了。这一恋爱加武侠的变局对后来的武侠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后的武侠小说包括当今风靡海内外华人文化圈的新派武侠小说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蕙质兰心、魅力足以颠倒众生的女侠形象,描画英雄侠骨的同时讲说起缠绵故事,让现代读者大过其瘾。”
通过对中心问题的设难,环环相扣地带动出水浒女性的各个方面问题,使这些问题在一个逻辑链条上得以自洽的呈现。可见,自我设难,即教育者通过对初始问题的层层设疑,最终将问题引导到一个更开阔更深入的层面上。
文学教育,往往容易在印象式的叙述中涌现出不少闪亮的观点,但印象式的吉光片羽,如果无法形成一个自圆其说的逻辑链条,则导致文学教育观点的混杂,无法以明晰的逻辑线索去探讨一个问题。长期以印象式而非问题探讨的方式从事文学教育,则可能使被教育者误解,以为文学教育不过是一个关系松散的观点的罗列或单靠个人才情的印象评点。甚至以为文学教育是维护个人感受的主观性的同时取消了文学教育过程中的逻辑性。
事实上,提倡文学教育过程中的自我设难,是希望文学教育工作者能多以问题研究的方式去探讨文学领域中的诸种问题。
探讨文学问题,善于自我设难,不但是为了避免文学教育过程如天女散花般漫无边际,还迫使文学教育者多思考问题并不断拓宽自我的文学视野。
但一个文学教育工作者在课堂上向学生讲授海明威的“冰山原理”,告诉学生叙事的语言一定要简约剔透,真正的艺术只给世人看到冰山的一角,冰山的八分之七在水下深藏,而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那么,作为文学教育工作者,你同时还告诉被教育者海明威的简约风格可以导向深刻,那么,如果把人物的情绪和思想完全呈现裸露状态,是不是就无法引发读者的心灵震荡呢?事实上,俄罗斯伟大的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最精彩的部分往往是酣畅淋漓的对话。比如,《罪与罚》中拉思科尔尼柯夫与波费利的三次谈话,《白痴》中梅思金公爵与叶班钦将军夫人及三位女儿的初次谈话;伊波利特欲自杀前在众人面前宣读他的声明及其议论的场景;梅思金在叶班钦将军家的一次聚会上的谈话;《群魔》中基里洛夫分别与斯塔夫罗金、与彼得·韦尔霍尔斯基的两次谈话;沙托夫与斯塔夫罗金的谈话;希加廖夫等人在维尔金斯基家一次聚会上的发言;彼得·韦尔霍文斯基与斯塔夫罗金的一次路上交谈;《少年》主人公与其同学的谈话、与其父亲的多次谈话;《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佐西马长老、佩西神父、米乌索夫、伊凡·卡拉马佐夫等在修道院里的一次聚谈。可以认为陀斯妥耶夫斯基完全破坏了海明威的“对话”小于“潜对话”的冰山原则,然而,这不妨碍我们领略这位文学大师思想的澎湃与深邃。相反,陀斯妥耶夫斯基第一次在世界文学历史上塑造了众多各自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的人物,而自我意识的高度外化让其小说呈现出思想狂欢的酣畅淋漓。
如果一位文学教师能够在讲海明威的时候提及陀斯妥耶夫斯基,或者在阐述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时候联系海明威,或者,在论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对话体”的时候,还向被教育者提示托尔斯泰的小说是怎样由于巴赫金的取舍被“贬为”与“对话体”相对的“独白型”,等等等等。那么,通过比照研究的辨析定位,将比单单靠对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的特点描述或归纳,产生更持久的影响力。
因此,文学教育工作者,如果善于在提出问题的时候非难自我的观点,无形间便拓宽了被教育者的视野,从而不断地把被教育者引向一个更深入,更广博的文学境界。文学教育工作者不同于作家,作家可以固执地坚持一己的审美立场,而文学教育工作者则要向被教育者提供尽可能开阔的文学视野,引入尽可能多样的文学趣味和文学景象。文学教育者的自我设难,既是向被教育者展示教育者的思维的连贯和严密,同时为教育接受者提供一幅幅开阔而非狭隘的文学“地形图”。
文学教育者多一些自我设难,把教育者一次次将自我“逼”向初始论点的反面,这当然不是意味着没有立场,相反,自我设难就是一种不断对话的立场,一种反思自我文学观念的立场,一种创新冲动时时萌动的立场。
自我设难将让文学教育者将自我置于一个反复审视自我、琢磨问题、推敲观点、转换思路、拓宽视野的境地。所以,一个善于自我设难的文学教育者,其教育目标,则是将被教育者从被动的接受者角色塑造成积极的对话者,将被灌输者转变为思考者,将线性的思维启迪为辩证的思维。
文学教育,需要丰富多样的感性判断甚至是天马行空的想象,但文学教育的过程不是捣糨糊,而是要将丰富多样的感性进入一个不失文学趣味的理性化秩序。感性只有在理性的秩序中才能得以保存,得以深刻。尖锐的敏感、汹涌的情思,毕竟需要概念化的反复辨析过程才可能得以定格;光辉艳丽或庸俗粗糙、金刚怒目或低吟浅唱的文学形象,毕竟需要以理性化问题化的方式得以秩序的呈现。自我设难作为一种思维方式,让重要的审美在思维中得以逗留、品味、推敲,使接受者的心灵得以敞开,感受并触摸到审美的意义所在,这样的审美讨论才可能真正留存在听者和观者的心中。一位心理学家说:“教育就是你把所学到的内容忘光了以后剩下的那点东西。”也许,多一点自我设难的审美话题能够让遗忘的速度减缓,多一些自我设难的文学探讨能够让文学的意义在接受者的心灵中获得永久的滋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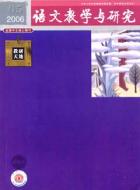
- 语文学法指导策略谈 / 王苏生 孟 湘
- 文言文背诵的规律与方法 / 张 联
- 初中语文探究性学习的指导方法 / 沈春萍
- 建设开放而有活力的语文课程 / 王碧峰
- 祥林嫂与阿Q谁更痛苦 / 黄彩萍
- 语文新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 章建红
- 论语文课堂的亲和力 / 葛明霞
- 新教材“课外必背古诗词”教学探索 / 白秦敏
- 语文课堂教学细节初探 / 程 萍
- 影响语文教学过程的原因及调节对策 / 孙元明
- 在玩中学语文 / 武宏伟
- 非预设性语文教学形态的课堂策略 / 时剑波
- 文言文翻译中的信与达 / 王厚军
- 文章中的比喻用途探微 / 张其富
- 科技阅读文的解题技巧 / 林 勇
- 高考语文复习与教材的关系 / 孙开虎 白成林
- 考场作文需要念好“三字经” / 蒋金涛
- 如何辨别筛选文中的信息 / 王 帆
- 《背影》是一首圣爱之歌 / 李文强 张立花
- 《陋室铭》主人的人格魅力 / 黄宝法
- 《师说》中的两个“师”字 / 聂正才
- 《我与地坛》的人生感悟 / 刘 谦
- 《失街亭》中马谡心理透视 / 李新华
- 《阿长与〈山海经〉》的文本细读 / 彭林虹
- 《废墟》的结构和语言 / 张鹏振
- 语文课本:尚须充分开发的沃土 / 郭志明
- 话题作文的应试策略 / 杨建军
- 语文新课程四大关系反思 / 王荣林
- 语文教学的四度 / 周红阳
- 《说“木叶”》微型教案 / 李克难
- 《三峡》教学实录 / 徐道生 王 凯
- 《孔子世家》研究性学习报告 / 许典祥
- 文学教育应多些自我设难 / 余岱宗
- 我的作文教学心得 / 罗 林
- 作文的标题艺术新探 / 黄海兵
- 话题作文的十大亮点 / 闫军平
- 写作创新与作文取材 / 黄丽芳
- 论人文环境下的作文教学 / 陈洪友
- 徐江关于语文教学的错误观点举隅 / 蓝瑞平
- 高中语文阅读教学存在的问题 / 刘颖异
- 论症候式阅读 / 李定青
- 个性化阅读教学要培养三种意识 / 许方雄 苏一鸣
- 构建科学文本的阅读图式 / 陈红军 董水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