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06年第7期
ID: 81520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06年第7期
ID: 81520
徐江关于语文教学的错误观点举隅
◇ 蓝瑞平
在其《中学语文“无效教学”批判》一文的诸多谬误受到严肃批评之后,徐江先生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思想观念、认识角度和学术态度等诸多方面存在的种种缺陷和偏激,又抛出了他以为更加得志的《改造解读思维:从无效到有效》一文(见《人民教育》2006年6期),用近乎鸣冤喊屈的语气和故意搬起石头砸自己的头的方式,说笔者将他“上纲上线”定性为语文的“罪人”。这一招十分滑稽——简直就是民间所言的端起大便盆往自己头上扣!笔者发表在《人民教育》2005年23期上的原话是:“中学语文教学也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和艺术,它包含着‘文学’,但又不仅仅是文学。如果谁想要仅仅立足于大学文学院的基点,对内容庞杂,过程繁杂,地位重要万众瞩目的中学语文教学随意地评头论足,而且又总是谬论‘多多’,那只能成为中学语文教学的罪人罢了。”不知道徐江为什么就自愿地把“罪人”的帽子给自己戴上了。
假如徐江先生的逻辑思维还比较清晰的话,断然不会将“罪人”的“帽子”就自己“戴上”了。这难道不是在强辞夺“理”,指鹿为马么?
当然,徐江先生的《改造解读思维:从无效到有效》一文终于比他的《中学语文“无效教学”批判》一文显得理智了些,在叫屈之后终于来了一句“我批的是中学语文‘无效教学’,而不是‘无效的中学语文’”。这比之《中学语文“无效教学”批判》一文来说,毕竟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为此,笔者必须祝贺徐先生。
然而,徐江终归是徐江,他终归不肯放弃他粗暴地强加给中学语文教学中存在的某些不足或缺失的罪名——“无效教学”。
关于中学语文教学中是否存在“无效教学”这一问题,白亚芳老师的文章已经作了回答,明确告诉徐江同志“中学语文教学‘无效教学’根本不存在”,而徐江充耳不闻。
张定远先生曾说:“中学语文教学肯定存在缺点不足,但成绩是主要的。认为语文‘误尽苍生’、中学语文教学‘无效’的人,其观点是错误的,他至少不太了解中学语文教学的性质、任务、现状。”徐江会信么?难。中学语文教学这么大一项工程,能没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么?但如果对这些“问题”采取和善的态度、帮助的态度,而不是呵斥的态度、夸大其辞的态度,都在“教书育人”的中学教师们,有谁会不接受呢?
早在1978年,吕叔湘先生就曾批评过中学语文教学“少、慢、差、费”,那不能不说是严厉的,但吕老他的态度多么和善啊,他始终没有说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哪一个方面“无效”,因此没有一个人不接受吕老的批评,而且从此不断地改进自己的工作,不断地为中学语文教学的伟大工程添砖加瓦。
二十七八年过去了,中学语文教学虽然仍然存在很多问题甚至错误,但无疑较之二十几年前大进了几步。也就在这时,徐江先生却不以为然了,视中学语文教学的主要成绩如空气,容不下中学语文教学中必然会存在的种种缺失(这也好比徐江从读小学到中学,从读中学到大学,从读大学到当大学写作课教师这一漫长过程中会写一些错别的字、会说一些错误的话一样),极为粗暴地将中学语文教学中存在的一些缺失打入“无效教学”的天牢,而且欲将宣判其死刑。这难道不是强辞夺理、指鹿为马么?
徐江先生还用“其实,蓝先生根本就没有明白我的文章之所指。我批的是中学语文‘无效教学’,而不是‘无效的中学语文’。蓝先生却回避这个本质论题,曲解别人的论点,制造一个对立面,这是以诡辩的方式拒绝批评。他的文章不值得再驳,我想再谈造成“无效教学”的原因以及如何改进并走向“有效教学”这样近乎小学生思维层次且十分粗鲁的语言来替其《中学语文“无效教学”批判》一文的错误言论辨解,可笔者与广大语文教师从来都承认我们工作中的不足,从来都是善待别人的批评(比如上述文字中一系列陈述),但徐江硬是要说笔者“曲解别人的论点,制造一个对立面,……以诡辩的方式拒绝批评”。这难道还不能说明徐江先生其文其人的强辞夺理、指鹿为马么?
然而“辞”是“辞”,“理”是“理”,鹿是鹿,马是马。不足、问题、缺点、错误毕竟各有各的性质,它们都与“无效”有别。可是徐江先生——总在其文章中喜欢标榜他自己的东西为“哲学式”(如“下面我就前边的问题作哲学式回答——重讲学习《游褒禅山记》的意义是什么”)的徐江先生,居然就把中学语文教学中的种种不足统统地宣判为“无效教学”,实在有点滑天下之大稽,难道徐江先生真的对“无效”的含义不解么?难道这就是欲在中国二十一世纪所向风靡的徐氏“哲学”么?
徐江在其“反思错误的解读”的论述中说:“中学语文教学之所以出现“无效”或者说“低效”甚至是“负效”现象,第一个原因就是语文老师解读思维活动层次低到文本解读水准线以下。以错误的解读引导学生,这怎么能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呢?”然后举了《谈骨气》一文的解读例子,随之抛出他的“命题”——“既然举这样三个例子“充分”证明“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那么我举三十个、三百个汪精卫之流的事例不就更充分更有力地证明“我们中国人是没有骨气的”吗?这个命题对吗?
笔者认为:徐江所言的“低效”可信,“无效”“负效”言之无理,即便是徐文例说的关于《谈骨气》的“简单”解读,对于初中学生的阅读解读来说,也不可能是无效的,能把文章读成那样子也就达到了“相应”的要求了,“无效”、“负效”从何说起呢?难道非得按照徐文后面所言的“哲学化解读”、“取独步解读”才是“正确”的“有效”“高效”“正效”的解读么?非也。笔者一直认为徐江虽然有一定的研究能力和想象能力,但基本不懂得中学语文及其教学,这从他对《谈骨气》这篇定在初中段的语文课文的常规解读及其缺失理性的批评指责就可以得以进一步证实:
1.“中学语文教学之所以出现“无效”或者说“低效”甚至是“负效”现象,第一个原因就是语文老师解读思维活动层次低到文本解读水准线以下”之说,说明徐江对初中学生的接受能力、理解能力、思维水平都不了解,而总用他自己的接受能力、理解能力、思维水平等同于学生,强加给学生,这无异于对牛弹琴,曲高和寡。徐江先生哟,为什么总要以你“独个”的“能力”来要求初中学生呢,莫非徐先生在当初读中学时就真正具备了“哲学式解读”能力了么?即便是你当年已经如是,那也只因你是神童,现实也不可能让所有初中学生都一下子达到你的“天才”的能力。初中生就是初中生,在初中一年级能导引学生读出“三个事例证明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这一层面的蕴味来就很不错了。因此,徐江先生对语文教师的指责“第一个原因”就是在强辞夺理,就是要指鹿为马,其言“以错误的解读引导学生,这怎么能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呢”,是粗暴无理的。
2.徐文说:“至今人们在讲吴晗先生《谈骨气》一文时,通通都是简单地说文章的中心论点是‘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文章使用‘文天祥不降元’、‘闻一多不怕暗杀拍案怒斥反动当局’、‘一个穷人宁可饿死不食嗟来之食’,三个例子‘证明’了‘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这说明徐江先生对当今的初中语文教学实践不了解,言而无理。《谈骨气》作为名篇。徐江文中所言的“解读”是一种,但实际教学中决不仅此一种。教师们往往根据自己学生的实际,从自己钻研原文得到的感悟立足,结合教学的目的、要求去施教,不同的教者就有不同的思路;甚至同一个教者在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教这篇文章时,也决不会如徐江先生所言的“通通都是简单地说文章的中心论点是‘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之类的一种教法,这是实事。即便是一个刚走上教学工作岗位的新教师,他也决不会如徐文所言“简单”得“通通”,这也是事实。可是徐江先生就是不肯承认这些事实,不尊重这样的事实,硬是要用“通通”、“简单”之类的独撰来丑化事实。这难道不是强辞夺理,指鹿为马么?
[##]
3.徐文又说:“然而语文界面对我这样的问题却缄口不答……”这说明徐文的作者不仅指鹿为马,而且还“不可一世”。“语文界”对他的“问题”真的“缄口不答”么?只要徐先生翻看有关杂志,上网查查,就会知道其言其论是多么的不顾事实,多么的自以为是。而徐文所谓的“那么我举三十个、三百个汪精卫之流的事例不就更充分更有力地证明‘我们中国人是没有骨气的’吗”的“命题”,应该是徐先生的思维混乱到了低于初中后进学生的水平,用近乎“扯蛋”的逻辑来推销兜售自己的“命题”所致。汪精卫之所以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而遗臭万年,并不是因为他有没有“骨气”,而是因为他是“汉奸”。难道徐先生不明白“没有骨气”与“汉奸”的含义相差几许么?这可是小学生都知道的啊。因此,徐江先生的命题不仅荒谬,而且无聊之极。笔者不妨也来一个“命题”:既然徐江先生并不是“语文”的“罪人”,现在实际也没有人说他是“罪人”,但徐先生把“罪人”的帽子给自己戴上了,那么他就是十足的罪人了。徐先生也清醒地明白自己“命题”的荒谬和无聊,那么他为什么要采用荒谬无聊的“命题”来诘问“语文界”,而且当面撒谎地说“语文界面对我这样的问题却缄口不答”呢?这难道不是徐江先生强辞夺理,指鹿为马的铁的事实?
4.徐文还说:“之所以出现这种错解《谈骨气》的现象,其根源就在于语文老师头脑中论说文的写作理论基本上是错误的。”说明徐江之“唯我独尊”、“老子天下第一”到了极致,已无可救药。
徐文所述的关于《谈骨气》的“通通”、“简单”真的是“错解”吗?不是!那只是一种比较朴实但却忠于文本,虽无花招但却可以帮助学生理解文意及其手法的基本解读,可决不是所谓的“错解”,“错”在何处呢?难道让学生明白三个典型的例子,意在以一当万地阐述“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这一要义对于初中学生来说不必要、不重要、不需要吗?难道吴晗先生写作此文不是要告诉天下人“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这个民族的精髓吗?何错之有?可惜搞大学写作教学的的徐江先生居然不能够承认《谈骨气》文本最实际真实的要义,硬是要把自己的那一套包装推销得那么至高无上。然而推销就推销吧,为什么非要否定事实而故意地“创造”奇迹般“哲学式解读”之类来吓唬人呢?而徐文的“根源就在于语文老师头脑中论说文的写作理论基本上是错误的”一说,真是狂上了天,狂入了地!难道徐先生下文缺乏理性,缺少严密性的“阐述”就是真理?徐先生有没有想过:假如你几句话就断定了“语文老师头脑中论说文的写作理论基本上是错误的”一说可以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的话,那么你的“定论”为什么没有成为语文教师们的“写作理论”呢?也许徐先生要说自己的“宏论”正如《宽容序言》里的那位勇敢的先驱者的先知先觉,而整个语文界的思想都是守旧老人般的罪孽。但果真是这样的吗?事实呢?你的所谓“论证”呢?难道其下文中的“这副山一样的重担强加在这小小的微弱的三个个体身躯之上,这怎么能让人服气呢”“他不会以三个小小的个体来论证‘中国人如何如何’的”之类简单式臆断式草率式的“阐述”能“论证”徐先生果真手握天下唯一的“真理”?由此可见,徐先生之于语文教师头脑中的写作理论的否定也好,徐先生要迫不及待地推销的“创新性的论证”也好,无不证明徐文的草率之极:强辞夺理,指鹿为马。
5.徐文说:“《谈骨气》的中心论点不是‘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这篇文章应该这样理解:吴晗就是在阐述什么是骨气,怎样做才算有骨气。”“人们原来的传统解读硬是把他们不能承担的责任:‘证明’‘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这副山一样的重担强加在这小小的微弱的三个个体身躯之上,这怎么能让人服气呢?他不会以三个小小的个体来论证‘中国人如何如何’的”,这再一次说明徐江行文观点的偏激以及学术理性的缺失。
首先,徐文所言《谈骨气》的中心论点不是“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这一否决的理论依据和事实根据都不充分,显得很草率,不能让人信服。其次,徐文下面的“这篇文章应该这样理解:吴晗就是在阐述什么是骨气,怎样做才算有骨气”之说,仅仅只能说是徐江先生个人的解读,不应该把它作为唯一正确的解读来强行替代他人的解读;如果徐先生一定要把自己的“个性”解读作为否定其它解读的屠龙宝刀,而且认为这才是真理的话,那么笔者也可以臆造一个诸如“徐江的观点根本就不能自圆其说,仅仅是在胡搅蛮缠”之类的观点来作为倚天宝剑,将徐先生的“屠龙宝刀”斩断;这时徐先生也许就能尝到被否定的滋味了。再次,徐文中“人们原来的传统解读硬是把他们不能承担的责任:‘证明’‘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这副山一样的重担强加在这小小的微弱的三个个体身躯之上,这怎么能让人服气呢?他不会以三个小小的个体来论证‘中国人如何如何’的”之说,不但不能证明(或“论证”)其否定“传统解读”的观点,而且还显得十分荒诞,“中国人是有骨气的”它怎么就成了“山一样的重担”了呢?谁又把它“强加”给“三个个体身躯”了呢?除了徐先生之外谁会用“小小的微弱的三个个体身躯”、“三个小小的个体”之类的粗鲁的低俗的语言来形容文天祥、闻一多和那个有骨气的古代穷人呢?连文天祥这样的历史名人、闻一多这样的现代英烈都变成了徐先生笔下的“小小的”、“微弱的”个体了,那谁才是“大大的”、“强壮”的群体呢?徐先生及其理论?笔者十分理解徐先生在学术方面欲登峰造极的宝贵精神,笔者十分理解徐先生永远认为自己观点正确无误的执著心态,但笔者决不赞同徐先生对文天祥、闻一多等古今英烈那气负天地的精神的贬斥,他们人格的崇高,精神的伟岸,足以证明“中国人是有骨气的”,顶天立地的,不可怀疑不容否定的。这是一切读过《谈骨气》以及熟知他们事迹的人的共识,否则,吴晗先生就不会在其文章中用极简练的笔墨来描述之而彰显“中国人的骨气了”。而“骨气”就是骨气,又怎么就成了“山一样的重担”呢?比喻能形象说理,但不贴切的比喻会让人头晕目眩,甚至让人肉麻。比如可以说“在大学阅读教学过程中引入‘哲学化解读’思维可能是给学子们提供了一盏夜行山路的破灯”,但不能说“在初中阅读教学过程中强行要求学生运用‘哲学化解读’思路好像是给学生喂狗粪”(虽然形象生动但欠缺文明)。因此,徐江先生关于“小小的微弱的三个个体身躯”“三个小小的个体”之类的表述也有强辞夺理,指鹿为马之嫌。
6.徐文所罗列的“哲学化解读”,“取独步解读”的提法及其阐述,放在南开大学徐江先生所教的班级实施,笔者将无话可说,那是徐先生的权力;但如果要将其硬塞给中学阅读教学,不是笔者要拒绝真理,而是徐先生自认为巧不可阶的“真理”并非货真价实的东西,真用它们于实际教学中不但会导致“缘木求鱼”的后果,而且会误人子弟。但徐先生却将其作为所谓中学语文教学“从无效到有效”的“改造解读思维”的灵丹妙药来包装,来宣传,来推销,这更说明徐先生对中学语文教学中的阅读教学的任务、目的、作用等问题的了解基本处于文盲状态而又非要说自己懂得许多而指鹿为马不可。
笔者之所以认定徐江先生总把他自己的理论自封到“巧不可阶”的地步,其理由如是:
1.徐文在“走向有思维的新解读”(这是个实实在在的病句)部分的开头说:“蓝先生在文中‘提醒’我,中学,语文有其特定性,不要把大学文学院特定的‘教学内容、教学目标、教学任务’‘强加’在中学头上。我以为蓝先生所谓中学语文的‘特定性’恰恰就是前边两种层次的‘无思维性解读’”,不知道徐江先生的“以为蓝先生所谓中学语文的‘特定性’恰恰就是前边两种层次的‘无思维性解读’”中的“恰恰就是前边两种层次的‘无思维性解读’”的判断、推论的依据何在,难道徐先生真的就不能领会“特定性”是指中学语文在其具体学段的特定任务、目标、作用吗?这是几十年来的《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以及新颁的《中学语文课程标准》中规定的,是许多专家、学者的集体成果,是中学语文教师们应该遵照的原则,怎么就成了徐先生所言的“无思维解读”呢?徐先生所言的“有思维解读”既然那么高妙,怎么就读不懂笔者的“特定性”的含义而将其“指鹿为马”呢?
[##]
2.徐先生所谓的“哲学化解读”,就其目前的操作性来说,还是一种有待求证其是否可行、是否科学、是否有效,可徐先生却十分着急地就把其作为“有效教学”的方法抛了出来,其“阐述”也不过只将他自个这个“小小的个体”对《我的空中楼阁》的一种解读罗列了出来,并且没有得到广大高中语文教师的认可,也并没有在为数不少但必须是足够的高中学生中实验推广验证其“有效性”和“科学性”,怎么就成了“从无效到有效”、“比讲什么‘回归自然’、‘亲近自然’不是更有思维性吗”的大方****了呢?
3.徐文所言的“比较式解读”,早已有之,古已有之,罗列于自己的囊中很有贪天之功为己有之嫌。
4.徐文中所述“屋作为一种‘物’,它的物的因素就是供人栖息,是人类的栖居所。当人在大地上建造了一个栖居之所的时候,他就不再是一个流浪者,他就有了一个根,有了一个与大地建立联系的根,一个扎到大地里的根:这就使作为动物的人类在自然界里像植物一样或者说获得了一种神圣的更自然的植物天性。所以,小屋的‘屋性’,就是作为动物的人类与大自然相关联的‘根性’”之类的“解读”,算是什么样的“哲学化解读”呢?即使不是瓮天蠡海,简直就是一个醉酒者的梦呓之语,虽然也是一种语言,但就是让人不明白——不是读者的“解读”水平低到了高中学生的水平以下,而是醉酒者的梦呓之语表述得断断续续,很有些“外星人”的“味道”,却还要大言不惭地自封为“哲学化解读”。就这一点说,梦呓者真的懂得“哲学”么?还“哲学化解读”呢!如此之“哲学化解读”,居然还要硬扯上德国美学理论家阿多诺、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们垫背,真有点狐假虎威。
5.徐文中的“取独步解读”不但是徐先生杜撰、生造出来的令人哑然失笑的“徐江式取独”解读法,不但字面上听觉上晦涩咬口,而且其之下的“而其他常规内容则予以舍弃”、“我将这种诠释名之为规定性诠释法”之类的表述都显得十分轻率、浮躁、滑稽,这种“解读”何以能帮助中学生“有效”阅读呢?能不使莘莘学子们昏迷不醒就不错了。徐先生啊,真会强辞夺理、指鹿为马哟!还仿程颐“善学者要不为文字所梏。故文义虽解错而道理可通行者,不害也”而后同样,我也可以说:“善文者要不为文字所梏,故词义虽独解而道理可通行者,不害也”呢!
综上所述,徐江先生《改造解读思维:从无效到有效》中宣传的“从无效到有效”,只不过是水中月雾中花罢了。然而徐先生却自封诸如此类的粗浅东西为“哲学化解读”,实在可笑之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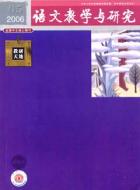
- 语文学法指导策略谈 / 王苏生 孟 湘
- 文言文背诵的规律与方法 / 张 联
- 初中语文探究性学习的指导方法 / 沈春萍
- 建设开放而有活力的语文课程 / 王碧峰
- 祥林嫂与阿Q谁更痛苦 / 黄彩萍
- 语文新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 章建红
- 论语文课堂的亲和力 / 葛明霞
- 新教材“课外必背古诗词”教学探索 / 白秦敏
- 语文课堂教学细节初探 / 程 萍
- 影响语文教学过程的原因及调节对策 / 孙元明
- 在玩中学语文 / 武宏伟
- 非预设性语文教学形态的课堂策略 / 时剑波
- 文言文翻译中的信与达 / 王厚军
- 文章中的比喻用途探微 / 张其富
- 科技阅读文的解题技巧 / 林 勇
- 高考语文复习与教材的关系 / 孙开虎 白成林
- 考场作文需要念好“三字经” / 蒋金涛
- 如何辨别筛选文中的信息 / 王 帆
- 《背影》是一首圣爱之歌 / 李文强 张立花
- 《陋室铭》主人的人格魅力 / 黄宝法
- 《师说》中的两个“师”字 / 聂正才
- 《我与地坛》的人生感悟 / 刘 谦
- 《失街亭》中马谡心理透视 / 李新华
- 《阿长与〈山海经〉》的文本细读 / 彭林虹
- 《废墟》的结构和语言 / 张鹏振
- 语文课本:尚须充分开发的沃土 / 郭志明
- 话题作文的应试策略 / 杨建军
- 语文新课程四大关系反思 / 王荣林
- 语文教学的四度 / 周红阳
- 《说“木叶”》微型教案 / 李克难
- 《三峡》教学实录 / 徐道生 王 凯
- 《孔子世家》研究性学习报告 / 许典祥
- 文学教育应多些自我设难 / 余岱宗
- 我的作文教学心得 / 罗 林
- 作文的标题艺术新探 / 黄海兵
- 话题作文的十大亮点 / 闫军平
- 写作创新与作文取材 / 黄丽芳
- 论人文环境下的作文教学 / 陈洪友
- 徐江关于语文教学的错误观点举隅 / 蓝瑞平
- 高中语文阅读教学存在的问题 / 刘颖异
- 论症候式阅读 / 李定青
- 个性化阅读教学要培养三种意识 / 许方雄 苏一鸣
- 构建科学文本的阅读图式 / 陈红军 董水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