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06年第7期
ID: 81522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06年第7期
ID: 81522
论症候式阅读
◇ 李定青
传统的批评认为作品的意义是确在的,它是作者有意无意地植入叙述的内容和形式之中的,正所谓“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因此批评家可以通过知人论世的方式来以意逆志,发掘了作者本意(志)也就达成了批评的基本目的。20世纪以来文学批评发生了巨大变化,四五十年代盛行于美国的新批评派认为文本本身是意义的存在方式,也是批评家捕捉意义的唯一根据。意义是确在的,但仅仅存在于由语词构筑的文本之中,其他观点只不过是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而已,它不是混淆了诗和诗的来源就是混淆了诗和诗的结果。
症候式阅读从根本上颠覆了文本具有确定意义的观念,它认为作品的意义并不是稳定存在的,在一定压力之下文本意义会迅速分解具有不同的指向,作品的内容、形式及其结合方式之中必然存在缺陷,阅读文本如同检查病人不能放掉那些反常之处,批评就是寻找社会文化形态与叙述意指过程之间的差距,通过对这种差距的确认来凸现现存社会文化形态的边界与局限以抵制认同实现超越。那么社会文化形态(主要是意识形态)与叙述意指过程之间的差距是如何产生的呢?症候式阅读认为意识形态先于文本而存在,但在文本虚构过程中被解构与重组,有些被遗漏,有些没有公开表达,有些在文本中变异的存在,从而形成了零散化的文本意识形态,这种文本内在的矛盾冲突使得文本中出现了大量的沉默、不在场和空白。文学文本对意识形态的定形过程相当复杂,意识形态原材料进入文学文本之后无法被完全吸收到一个单一化的原则体系之中自圆其说,这时文学叙述就撑破了意识形态,用马歇雷的话来说就是叙述用意识形态来挑战意识形态。
例如《三国演义》受正统观念影响竭力尊刘抑曹,除了把曹操刻画成乱世奸雄作为反衬之外,还在叙述中反复申明刘皇叔仁义。可是在那种“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残酷斗争中,刘备是如何求得生存并逐步发展起来的呢?如果仅仅靠王道仁政他会比陶谦孔融更早被消灭。该书第十九回:
方操送宫下楼时,布告玄德曰:“公为坐上客,布为阶下囚,何不发一言而相宽乎?”玄德点头。及操上楼来,布叫曰:“明公所患,不过于布;布今已服矣,公为大将,布副之,天下不难定也。”操回顾玄德曰:“何如?”玄德答曰:“公不见丁建阳董卓之事乎?”布目视玄德曰:“是儿最无信者!”操令牵下楼缢之。布回顾玄德曰:“大耳儿不记辕门射戟时耶?”
显然吕布是个有勇无谋,见利忘义的小人。惩治这样一个触犯纲常的人是作者与读者共享的正统意识形态所认可的行为。刘备借刀杀人表面上冠冕堂皇是因为吕布不忠不义咎由自取,而实质上掩盖了他趁机削弱潜在对手曹操的自私动机,如若不然以曹操的谋略加之吕布的骁勇恐怕将来更难对付。同样是这个刘备,在封徐州牧时还信誓旦旦不杀吕布——“兄勿忧,刘备誓不为此不义之事。”那时的吕布虽早已臭名昭著,却还有利用价值可以掩护徐州。但当吕布表示愿意臣服曹操并帮助他完成霸业时,对刘备来说,他已成了重要威胁不得不除。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刻画的仁德忠厚的刘备被文本中老谋深算的刘备颠覆了,正统的忠孝仁义被文本中的权谋诈术瓦解了。下面分别论述症候式阅读的主要理论主张。
1
在《读〈资本论〉》序言中,阿尔都塞明确区分了两种阅读行为方式:无辜的阅读(i ocent reading)与有罪的阅读(guilty reading)。所谓无辜的阅读,是指日常生活经验层面上那种理想化的直接阅读,对象自然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读者通过细致的阅读看到作者所表达的全部内容,阅读过程尽量保持对象的原貌不附加任何外来因素。在阿尔都塞看来,无辜的阅读纯粹是一种天真的理论假设,任何人的阅读都是在一定的语境中完成的,阅读行为主体绝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在一定知识背景、生活阅历、心理定势中负载了自己主观投射的人。任何人都无法一劳永逸的直接穿透文本穷尽对象达到最终的认识,每一次阅读都只是在一定理论背景支配下产生出来的一定层次上的认知结果,每个阅读主体都裹挟着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独特语境。在这个意义上,阿尔都塞明确提出所有阅读都有主体附加(理论先在),不可能是完全“无辜”的。这一思想与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的探照灯理论中提出的“假设先于观察”有着某种家族相似性。如同科学观察活动一样,在文学阅读活动中同样不存在超然的完全客观中立的主体,主题必然有某种理论先在和心理期待。即使面对同一对象,由于认知结构不同、理论背景不同也会出现迥然不同的阐释。例如太阳东升西落是有目共睹的,可是却有地心说、日心说两种解释。面对同一文本,同样也会出现不同的阐释。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假设先于阅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尔都塞坦承症候式阅读是一种有罪的阅读。
症候式阅读承认阅读活动中主体理论先在的影响是无所不在的,可以说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直接阅读。按照皮亚杰的说法,阅读活动决不是简单的刺激——反应过程,任何文本对阅读主体的刺激都需经过主体过滤同化由先在的认知图式处理之后才会作出反应。阅读均受制于主体的理论先在和“成见”,这是症候式阅读批评主体论的第一要义。
那么批评主体要遵循哪些规范呢?那些个体才有资格成为批评主体呢?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我们需结合阿尔都塞反人道主义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学说的理论。阿尔都塞认为在任何情况下个人都是他们所处于的社会结构的创造物,以致他们的意图与其说被当作社会实践的原因,不如说被当作社会实践的结果。不仅个人的主观意愿是“被动”的,而且个人的身份也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通过召唤质询等手段塑造出来的,是这套装置作用的结果。阿尔都塞革命性的刷新了意识形态的定义: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真实的生存境遇间想象性关系的表征。在他看来,人是意识形态的动物。对人、人类社会而言,意识形态必不可少无所不在。人与世界并不是一种主客观的封闭型双向关系,人的主体屈从于一系列对世界的代表系统,人生活在自己的意识形态之中,意识形态是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他永远不会终结。阿尔都塞说:“意识形态既不是胡言乱语,也不是历史的寄生赘瘤,它是历史的社会生活的一种基本结构。”它具有两方面的社会功能:一是主体建构;二是作为国家的统治机器。阿尔都塞认为个人如同拉康描述的处于镜像阶段前的婴儿一样原本并没有关于自身同一性的意识。这时个人没有成为主体,还只是具体的在那里生存的个体。正是意识形态召唤个体使之成为社会的人,成为共同体的成员。伴随着这一过程一整套规约内化为主体对自己的要求,不再是强制性的外在规范。例如《阿Q正传》中这样写道:
阿Q本来也是正人,我们虽然不知道他曾经蒙什么明师指授过,但他对于“男女之大防”却历来非常严;也很有排斥异端——如小尼姑假洋鬼子之类——的正气。……阿Q的耳朵里,本来早听到过革命党这一句话,今年又亲眼见过杀掉革命党。但他有一种不知从哪里来的意见,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
相对于个人来说,意识形态总是具有先在性的。正统的封建思想驱使并诱导着阿Q在既定的正人/异端二元结构中做出选择,当阿Q认同了正人这一主体位置之后,也就随即认同了特定意识形态中不证自明的公理“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这样,个人就被悄无声息的顺利安置到意识形态预先设定的位置上充当了某种固定的角色,而且主体自身对这种不由自主的安排毫无察觉并非被外在力量所强制。
批评主体也毫无例外地处于特定的意识形态之中受其遮蔽,不能把意识形态视为外在于主体的对立存在。对文本进行症候式阅读的批评主体应当反思自身的意识形态幻象,时刻警惕批评活动中的屈从(subject)——对意识形态召唤的认同,获得一定的超越性批评距离。
[##]
只有获得超越性批评距离才能从意识形态之下解蔽,这是症候式阅读批评主体论的另一重要观点。从这一立场出发,阿尔都塞学派的理论家们认为大众是无法揭露意识形态使作品呈现意义的。“与文本出现的同时,必然要出现文本解释者。例如,有巫辞就得有祭司,有经文就得有牧师,有法律就得有律师,同样有艺术作品就得有批评家。解释者的定义就排除了每个人都能成为解释者的可能。”只有经过严格的训练达到一定的理论素养才能练就穿透意识形态迷障的火眼金睛。批评主体对于个人真实的生存境遇要有切肤之痛,这样才能打破意识形态幻象所营造的虚假幸福感。
2
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中提出:“单纯的字面上的阅读在论证中只能看到文本的连续性。只有采用‘症候读法’才能使这些空白显示出来,才能从已说出的文字中辨别出沉默的话语,这种沉默的话语,由于突现在语词的话语中,因而使文字叙述出现了空白,也就是说丧失了它的严格性或者说它的表达能力达到了极限。”在这里阿尔都塞区别了文本中蕴涵的两种话语:沉默的话语(the discourse of the silence)和语词的话语(verbal discourse)。症候式阅读从理论主张到操作方式都建立在对这两种话语的区分之上,可以说发掘由沉默的话语构筑的隐性文本并进行深度阅读是症候式阅读的存在前提。
和以往的统一性、总体性的文本观念不同,症候式阅读认为文本在物质上是不完整的、异质的和扩散的。文本不是自足的,而是必须由某种缺失相伴,否则就不可能存在。要了解一部作品,就必须把这种缺失考虑在内。作品正是由它缺失的东西、由它的不完整性来说明的,批评的功能就是把这种缺失的东西揭示出来。症候式阅读认为显在层面的线形阅读为了追求外在的统一性忽略了文本中固有的各种悖逆、含混、反常、空白和疑难,而这些被人遗弃的症候恰恰对于理解文本的真正含义具有关键作用,它们甚至比语词的话语具有更高的价值。文本绝不像它貌似的那样简单。只有保持超越性批评距离用一种构形的目光(informed gaze)审视文本才能把隐蔽在理所当然的表层叙述之下的空白和沉默发掘出来。这种构形的目光是主体参与文本重构的重要标志,也是隐性文本得以呈现的关键因素。
蓝棣之对众所周知的《毛选》的阅读就包含了这种构形的目光,他发现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对鲁迅有多种称谓,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圣人、急先锋、党外布尔什维克、民族英雄、方向、旗手、主将等等;但是他从未说鲁迅是政治家,联系到高尔基、柳亚子都曾被毛泽东称赞为政治家,毛泽东对鲁迅称谓上的这一空白是耐人寻味的。早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毛泽东就不支持鲁迅的看法而是认为“国防文学”这一口号更合适。后来,与鲁迅过从甚密的胡风、冯雪峰、巴金、萧军、丁玲、瞿秋白都受到毛泽东严厉的批评。尤其是在影响深远的纲领性文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明确提出杂文时代在根据地已经成为过去,鲁迅所用的冷嘲热讽、隐晦曲折不再必要了,文艺创作要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通过对这些隐性文本的阅读,蓝棣之认为毛泽东眼中的鲁迅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方向,而在民主革命已经完成的根据地所需要的则是“俯首甘为孺子牛”。在人民当家作主的解放区,杂文时代甚至鲁迅创作都已经成为过去。解放后,毛泽东曾说鲁迅要是不死,大约会做个文联主席。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眼中作为“现代中国的圣人”、“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的鲁迅只属于五四以来的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他的时代就一去不复返了。
从隐性文本的阅读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对鲁迅的高度评价从来都只是在新民主主义的框架内进行的,解放后的文艺思想与之也是一脉相承的。在新阶段里,工农兵方向才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心,国统区的创作方法、创作题材逐渐退出文艺界并成为历次批判的目标也就不足为奇了。
3
随着斯大林式教条主义在欧洲的破产,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本化的趋势愈演愈烈。作为一名坚定的党内哲学家,阿尔都塞认为这只不过是又一次的意识形态狂热,因此他大声疾呼保卫马克思。在他看来,保卫马克思的正确途径是回到马克思,但这并不是还原,不是回到马克思的个别观点和词句,而是回到马克思的深层理论框架——他所发现的新问题及解答途径。只有找到马克思的深层理论框架才能看到马克思没有看到的东西,实现对马克思的继承和发展。他所标举的症候式阅读实质上是一种生产性阅读,其目的就在于发掘隐含于文本中的理论框架。这种阅读不局限于旧的问题和视阈,而是在新的理论框架中的视阈突现。这里的生产特指阅读活动中认识的生产,生产就意味着把隐匿的东西表现出来。
马歇雷吸收了阿尔都塞的症候式阅读并将之应用于文学批评。他认为传统批评在性质和功能上有三大谬误:经验主义谬误、规范谬误和阐释谬误。经验主义谬误是指批评满足于清晰再现作品使之易于接受。这样的批评活动是寄生在文学创作之上的,缺乏独立的品格,其价值充其量不过是文学接受的催化剂,帮助消费活动的完成。形形色色的印象批评大都属于这一类。规范谬误是指批评以立法者自居用一套先在的往往是陈旧的标准去衡量鲜活的文学创作,合乎标准的誉为佳作,不合标准的斥为异端。这种批评对于累积艺术程式有一定意义,然而操持不当便容易削足适履,束缚文艺的发展。它以仲裁者的面貌出现,与文学场域内外的权力关系往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十七世纪法兰西学院的文学批评就属于典型的规范谬误。四十名院士对文艺问题进行表决,他们的决议具有律法的权威,人们必须谨遵无违。高乃依的《熙德》尽管在大众中广受欢迎,但由于违反了法兰西学院制订的义法仍然受到了严厉的指责。阐释谬误则在于先验性的假定一部作品中包含一个真理,批评的使命就是千方百计的找出这个既定真理。这是一种把所有文学作品寓言化的幼稚做法。《盲人摸象》讲了克服认识片面性的重要,刻舟求剑讲了不要用静止的眼光看问题,那么《红楼梦》讲了什么呢?排满?色空?才子佳人?阶级斗争……马歇雷认为,批评是一门严肃的科学,所以症候式阅读不把作品看作已知的东西,而是当成等待探索的对象,它不是依据先在的规范来检验作品做出品级的鉴定,而是在认识和它的对象间保持一段超越性距离;它的目的不是揭示文本内蕴藏的唯一真理或意义,而是探讨不在场的,让沉默说话。
意识形态在现实中像个人的生存体验一样自然,只有进入文学文本之后经过文学形式的重塑才暴露出其内在的矛盾与断裂,但文学只能使我们感到它的存在,只有批评这样一门科学才能使我们真正认识它。批评本质上是一种理论认识的生产,它把我们在文学中感觉到的意识形态的矛盾和界限呈现出来作为认识的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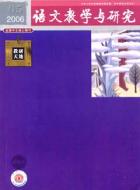
- 语文学法指导策略谈 / 王苏生 孟 湘
- 文言文背诵的规律与方法 / 张 联
- 初中语文探究性学习的指导方法 / 沈春萍
- 建设开放而有活力的语文课程 / 王碧峰
- 祥林嫂与阿Q谁更痛苦 / 黄彩萍
- 语文新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 章建红
- 论语文课堂的亲和力 / 葛明霞
- 新教材“课外必背古诗词”教学探索 / 白秦敏
- 语文课堂教学细节初探 / 程 萍
- 影响语文教学过程的原因及调节对策 / 孙元明
- 在玩中学语文 / 武宏伟
- 非预设性语文教学形态的课堂策略 / 时剑波
- 文言文翻译中的信与达 / 王厚军
- 文章中的比喻用途探微 / 张其富
- 科技阅读文的解题技巧 / 林 勇
- 高考语文复习与教材的关系 / 孙开虎 白成林
- 考场作文需要念好“三字经” / 蒋金涛
- 如何辨别筛选文中的信息 / 王 帆
- 《背影》是一首圣爱之歌 / 李文强 张立花
- 《陋室铭》主人的人格魅力 / 黄宝法
- 《师说》中的两个“师”字 / 聂正才
- 《我与地坛》的人生感悟 / 刘 谦
- 《失街亭》中马谡心理透视 / 李新华
- 《阿长与〈山海经〉》的文本细读 / 彭林虹
- 《废墟》的结构和语言 / 张鹏振
- 语文课本:尚须充分开发的沃土 / 郭志明
- 话题作文的应试策略 / 杨建军
- 语文新课程四大关系反思 / 王荣林
- 语文教学的四度 / 周红阳
- 《说“木叶”》微型教案 / 李克难
- 《三峡》教学实录 / 徐道生 王 凯
- 《孔子世家》研究性学习报告 / 许典祥
- 文学教育应多些自我设难 / 余岱宗
- 我的作文教学心得 / 罗 林
- 作文的标题艺术新探 / 黄海兵
- 话题作文的十大亮点 / 闫军平
- 写作创新与作文取材 / 黄丽芳
- 论人文环境下的作文教学 / 陈洪友
- 徐江关于语文教学的错误观点举隅 / 蓝瑞平
- 高中语文阅读教学存在的问题 / 刘颖异
- 论症候式阅读 / 李定青
- 个性化阅读教学要培养三种意识 / 许方雄 苏一鸣
- 构建科学文本的阅读图式 / 陈红军 董水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