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学 2005年第1期
ID: 78566
中学语文教学 2005年第1期
ID: 78566
笔谈《作文大革命》
◇ 陈金明 苏立康等
编者按:近日读到一本好书,书名叫做《作文大革命》(福建文艺音像出版社)。说是好书,倒不在“大革命”三字,而在于这是一个很有创意的策划,是以电视节目的形式展现了十位当代著名作家、学者与学生、教师有关写作问题的对话,并且有现场作文和点评。下面这组文章,算是该书的一个引读吧。
一部高品位有特色的好书
全国中语会理事长 陈金明
《作文大革命》这部书是由巢宗祺、谢冕、孙绍振、曹文轩、叶永烈、北村、张晓风、高洪波、梁小斌和江浩共十位当代作家和大学教授撰写的,说的都是作文教学的事。在我所见到的有关作文教学的著作中,有这样强大阵容的作家群体出面为改进作文教学出谋划策还不多见。作文教学改革,除了需要业内同仁的思索与探究,还需要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关注与点拨。从这一点说,本书的策划者做了一件好事,它为读者编出了这样一部高品位、有特色的好书。“积力之举”无往不胜,是语文教学希望之所在。
改革开放以来,中学作文教学有成绩,但问题也还不少。在我看来,一是有相当多的学生怕作文;二是不少学生作文说的不是心里话。为此,本书作者像话家常一样,对作文教学提了好多建议,诸如中学生主体意识、个性化写作、想像力的张扬以及世界观质量的提升等等,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在这里,有的是亲身的体验而不是僵化的条条;有的是心灵的沟通而不是生硬的说教。因而读起来使人感到分外亲切。
教学生作文,教师自身的写作水平至关重要。有位教师深情地说:“我若要求学生把文章写生动,那我自己首先必须写出生动的文章。”这几位作家让人信服的地方,就是不仅说出了道理,而且在现场写出了高质量的文章。著名语文教育家叶圣陶生前曾多次谈到语文教师写下水文,要经常练笔,不断提高写作能力。实践表明,教师只有自身追求人生价值,创造人生辉煌,才能有效地带动学生走向成功的彼岸。
要更多地关心教师教育
北京教育学院教授 苏立康
巢宗祺、孙绍振两位先生在《作文大革命》中都谈到学生对语文学习缺乏兴趣,尤其是对写作文感到困难的问题。分析其原因,孙先生认为是指导思想不对头,巢先生则主要谈了课程的问题——课程的“大一统”的模式,把语文教学管“死”了,完全忽视了学生的多样化、个性化的发展。然而这些问题已经存在几十年,不是近年来才有的。因此客观地说,受上述两种影响最深的是我们现在从教的教师们,因为他们正是几年前、十几年前的大、中、小学校的学生。我们到学校去听课,常发现老教师和年轻教师在教学理念上并无太大差异。不管什么时候,无论怎样改革,都要通过一线的老师们去实现。因此,我们必须关注教师教育的问题。
举个例子说,几年前,我读到一位小学二年级学生的作文,题目是“春天的小雨”,全文如下:
春天来了,有时候小雨沙沙的下起来。
雨中的人们都穿着雨衣、雨鞋,还有的打着雨伞。
雨中的天空,无数的小雨点从阴沉的天上落下来。大地到处湿漉漉的,田野里麦苗喝足了水,好像笑着说:“谢谢你,小雨!”
我想,大自然真丰富啊!不过,未来的世界一定比现在更美丽,更丰富。
这篇小学二年级学生的习作是写得不错的,但是有明显的不足:语言的毛病在其次,主要问题是最后一段来得太突兀。从前面三小段里,实在找不出这一段的根据。于是我带着这个问题,请教了小学语文老师。不只一位老师告诉我:老师要求学生写作文要写出“意义”来。这恐怕就是问题所在了。看起来老师对这篇作文本身的意义——小作者对春雨的喜爱——并不认同;小作者只好顺应老师去说那些老师认为是“有意义”的话,那自然不是孩子“自己”的话,甚至不是这个年龄的孩子的话。
这个问题看起来好像就是作文的问题,其实不然。当老师告诉学生“应当说这些话”的同时,也就告诉了学生“应当这样想”。这样的教育如果经常化,久而久之,学生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学生个性的发展,恐怕就要大打折扣了。
这里丝毫没有责怪老师的意思。我只是想说,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不容忽视。巢先生、孙先生是从比较高的立足点来谈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要通过多种渠道,也要经历一个相当的过程。
参读朱光潜
首都师大文学院教授 饶杰腾
最近,重温朱光潜先生写给青年朋友关于学习写作的若干文章,又细心地读了谢冕、曹文轩等几位作家与中学生谈作文的现场实录。虽然二者相隔数十年,但放在一起思考既有意义又有意思。
关于文学的修养,朱先生说:
学文学第一件要事是多玩索名家作品,其次是自己多练习写作,如此才能亲自尝出甘苦,逐渐养成一种纯正的趣味,学得一副文学家体验人情物态的眼光和同情。到了这步,文学的修养就大体算成功了。如果不在这上面做功夫,读完任何数量的讨论文学的书籍,也无济于事。(《谈文学•序》)
对此,谢冕论及阅读,强调要“在感知中再创造”。接着作了深入的阐述:
……这种能力怎么来的?再创造的能力是从小养成还是天生的?不是天生的。那怎么培养?一个是阅读别人的作品,一个是自己写作的经验,还要有人生经验的积累,大概就这几个方面。你写作了以后知道创作的甘苦。你有了写作的经验、体验,才能够知道作家这个地方写得好,不然你不知道它好在什么地方。你自己亲身实践以后,你就胜出别人一筹,仅仅是阅读不写作,往往像蜻蜓点水,不会深入。(《从时代性和创造性出发》)
至于初学写作的时候,曹文轩指出,不要一根筋地光想着去创造,去创新。他认为“模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同时,告诫中学生:“不要以为这样做没有用,过去有些方法还是有一定用处的。一件事坚持了那么多年,总有一定的道理的,不要一个早上就把它全部否定掉。”对于模仿,他说:
这就像学画一样,学画要从素描开始,不能一出手就是名画,这不可能,必须从素描开始。甚至要一直强调,就是说你已经会画名画了,你的画已经价值连城了,你仍然要有一个素描心态。(《模仿、素描心态与耐心》)
在练习写作上,基本道理是相通的。上世纪20年代,朱光潜先生留英期间,写《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曾题为《给一个中学生的十二封信》。其一谈及初学作文,认为应该认清路径,而这种路径是不能指点的:
学文如学画,学画可临帖,又可写生。在这两条路中间,写生自然较为重要。可是临帖也不可一笔勾销,笔法和意境在初学时总须从临帖中领会。从前中国文人学文大半全用临帖法。每人总须读过几百篇或几千篇名著,揣摩呻吟,至能背诵,然后执笔为文,手腕自然纯熟。……许多第一流作者起初都经过模仿的阶段。
读书只是一步预备的工夫,真正学作文,还要特别注意写生。(《谈作文》)
谢冕等与中学生谈作文的实录,收在《中国顶级作家引领作文大革命》一书中。饱尝创作甘苦的作家,而且是“中国顶级”的,来“引领”作文“革命”,而且是“大革命”,该是难能可贵的。我想,我们要从作家们与中学生之间真诚、切实的对话中去揣摩、体会其中的奥妙。倘若能参读朱光潜先生80年前《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与40年前《谈文学》两部富有生命力的论著,或能收到相得益彰的效果。
解读作文之道
著名特级教师 陶伯英
《作文大革命》中的叶永烈专辑不仅有叶老师写的参加高考作文的心得和对学生作文情真意切的指导,而且还收入了叶老师的4篇高考作文。这是十分难得、十分宝贵的作文辅导专辑。
叶老师针对学生作文的实际情况,谈了15个具体问题,涉及到怎样写好高考作文,怎样对待作文,怎样提高作文水平等方面,对每个问题都结合自己的写作事例来谈,既具体又深刻,在像面对面地话家常的交谈中,诠释了作文之道,使人深受教益。叶老师语重心长地说:“写好作文不光是为了高考,其实能够清楚地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是做任何工作都需要的。”我想,这“能够清楚地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是很关紧要的,作文就是要写出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真情实感,而不是去说大话、套话、假话。教育部制订的《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能不拘形式地写下见闻、感受和想像,有意识地丰富自己的见闻,珍视个人的独特感受。”这是对学生作文的必然要求,学生如能按《课程标准》的要求,照叶老师的教导认真去实践,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心得、自己的见解、自己真挚的感情去写,就能写出有个性特点备受称赞的好文章。
[##]
北村专辑谈的话题是《作文技能的训练》,北村老师指出:“培养写作能力,其实就是培养一种思维能力。”这话说得非常中肯,写作能力的提高是离不开思维的。抓住了思维,也就抓住了根本。因为思维是在表象、概念基础上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等认识活动的过程,思维贯穿写作活动始终。从根本上说,一个人的表达能力是他的思维能力的表现。培养表达能力,首要的事情还是提高思维能力。明确这个问题,对作文技能的训练是很重要的。北村老师在谈作文内容的问题时,举了一个初二学生作文的例子,称赞这篇作文写得好,有开拓性思维。他深刻指出,搞写作的人要培养自己的思维习惯,要认识思维方面的三个层面。他在谈将素材变成题材的问题时,讲了自己写《周渔的火车》的实例。他还说,写作的思维建立起来,我们写作的整个广度、高度就扩展了很多,写作的东西自然就丰富起来,深刻起来。专辑附有福州王立根老师对北村老师写的《爱是幸福的安慰》的评述文章,王老师说:“如果我们平时能够注意训练自己思维的话,能够像北村老师这样灵活的思维,写文章能够放开去想,想清楚再写,多想几个为什么,运用逆向思维、扩散性思维,最后用集中的思维,把这扩散性思维的点点都连在一条线上,变成一个面,那么这文章就出来了,这就是写作的秘密。”这话说得在理。
文章之道在“心”里
中语会创新写作专题研究组组长 赵明
近日读了《作文大革命》这本书,感觉很有意思。其中给我印象很深的是著名台湾作家张晓风女士和著名诗人、儿童文学家高洪波先生的谈话。
张晓风女士说:“写文章要有同情心”;“有了同情心,才有写作的冲动。”她以自己创作的《不朽的失眠》为例,来说明“同情心”怎样促成了一篇小说的诞生。她认为,“这个世界也需要像张继那样的人,为伤心人说出一些话来,在一个安静的失眠的夜晚。”这便有了那首传诵千古的优美而略显孤寂的《枫桥夜泊》。令张继感叹不已的不只是个人的遭遇,而是由己及人,同情于像他一样的落榜者。张晓风深深地理解张继的心情,并且能够体谅他,同情他,于是才有了创作《不朽的失眠》的冲动。张继落榜而有《枫桥夜泊》传世,张晓风同情张继而作《不朽的失眠》,这其中的道理就在一个人的“心”里,在因同情而滋生的浓浓的情感里。过去,我们在课堂上给学生讲《不朽的失眠》,往往部分注意到作者高超的艺术手法和丰富的想像力,很佩服她能把一首小诗演绎成一篇有血有肉有情节有形象的小说,却不大关注创作的冲动来自何方,为什么而写作?原来,《不朽的失眠》不光是“同情”之作,还是励志之作。为文之道正在“心”里。张晓风被选在现行语文教材里的另一篇作品《行道树》,同样充满了同情心和责任心。一列立在城市的飞尘里的行道树,甘愿披一身抖不落的烟尘,在春天勤生绿叶,在夏日献出浓荫。这就是作者笔下的“忧愁而快乐的行道树”,或者是作者精神楷模的化身。
高洪波先生也把“心”看得很重。他在谈话中引用了当年冰心先生写给他的一句话:“有了爱便有了一切。”他告诉在座的同学:“一定要先有爱,有对人的一种同情,爱就有了一切”,认为爱“是我们的文学,我们的诗歌,我们的电影、音乐,很多很多种艺术的大前提。”可见,爱心对于写作是何等的重要!同情心,爱心,都是一种人文关怀,是一种境界,是做人和作文的根本。正是有一颗这样的“心”,高洪波才写出了像《太阳》《苹果》那样的好诗,倾注了对盲童的关爱、同情和尊重。
爱心是需要培育、熏陶和滋养的。除了道德的教育,生活的历练之外,文学的熏陶和滋养也是非常重要的。张晓风主张“用古典里的营养去壮大自己的生命”。从《诗经》《离骚》到唐诗、《红楼梦》,无不是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惟其如此,才会有深刻的暴露和无情的鞭挞,才会有真诚的赞美和纵情的讴歌。张晓风做到了这一点,所以才会有像《不朽的失眠》这样的作品产生,才会被评论界誉为“不忘情于古典而纵身现代”的女作家。
学诗与尊重个性思考
浙江海宁中学教师 章景曙
很少有人给中学生谈诗与作文的关系。诗人梁小斌却在书中就自己的诗作《我热爱秋天的风光》作了生动的解读,并联系中学生的作文谈了一些颇为切实而深刻的见解。他认为读诗不要忘记它的写作背景,背景不应很大,可以具体些、小些。当年诗人还是一个知青在农村劳动时,虽然身处大自然,却没有诗意产生;到了离开前夕,他去田埂走走时,灵感才随着情感的波动突然而至。这就告诉中学生写文章与写诗一样同样应来自真情实感,并有自己独特的思考。诸如“秋天的风光是比人类存在更古老的风光”“一条被太阳翻晒过的河流在我身躯上流淌”“我有一颗种子已经被遗忘,让河流把我洗黑”……这样的句子在一般中学生的作文中很少出现,有些语文教师也会认为这是病句,但实际上正是这样的一些句子充孕着丰富的诗意。想到贝特森在《英语与美语》中说的一句:“一首诗中的时代特征不应去诗人那儿寻找,而应去诗的语言中寻找。我相信,真正的诗歌史是语言的变化史,诗歌正是从这种不断变化的语言中产生的。”梁小斌从形象思维、画面感、蒙太奇、咏叹调、色彩几个方面开启并拓展学生的思维,然后提出句是训练语言的重要方法。
当前中学生作文忽视文句锻造、缺少文采,使思想的表述显得苍白乏力,梁先生从诗的语言角度着重分析、激发学生的想像力和创造力,无疑很有针对性。
江浩先生则以非洲荒原上的角马群被两三只不及角马腿肚子高的豺狗所击溃的话题,让学生各抒己见。学生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是活跃灵动的,且各有特点。一位学生说:角马不像卡尔维《树上的男爵》中的男爵一样,躲到树上、气球上,最后消失在空中。它们没有逃避,该怎么活就怎么活,该怎么延续就怎么延续,照样勇往直前。“于是面对竞争我们所需要的就是面对,用我们的双手来改变世界。”这位同学的思索有思辨的深度,而且在表述上有一定技巧。
为此,江浩先生提出“从技巧上说,思索可以从反面开始”的建议。他认为有很多历史上的东西,真正戕害了我们未来青年的思维。因此,要勇敢地否定、淘汰、埋葬、踢掉、扔掉旧的知识。他认为,教师在指导学生审题、立意、选材的过程中往往搬弄着许多自己从过去的课堂上学到的程式化的东西,把自己形成的心理定势、思维格式强加给学生。他以自己的作品《哀歌》为例,告诉学生应如何对待兽性,对待狼性,他对劳动模范当着全村人的面把狼活活剥皮的做法给予否定与批判。这种“从反面开始”的思索是发人深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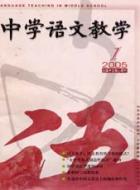
- 张扬文学教育的个性 / 高万祥
- 欲与窗外风景试比高 / 马 ?
-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 王小波
- 鲁迅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 王富仁
- 渗透课改新理念 / 刘 华
- 古代诗歌鉴赏试题例说 / 赵大鹏
- 发展性语文学习评价观的建构 / 曹明海 张曙光
- 写作:请读部好书打底子 / 高天友
- 何需突围爱情? / 王 君
- 如何写创新作文 / 尤志心
- 笔谈《作文大革命》 / 陈金明 苏立康等
- 替林黛玉写一则进贾府日记 / 赵克明
- 语言教学反面例证三则 / 汪大昌
- 怎一个“巧”了得 / 毛恩波
- 变抽象为形象化知识为实践 / 曹春山
- 给人启发的争鸣 / 汪兆龙
- “《智取生辰纲》暗线说”质疑 / 陆精康
- 高中语文课本文言文教材释义指误 / 高 峰
- 一堂作文指导课 / 杨朝中
- 我们选择坚强地生活 / 葛江海
- 那一只纸船 / 梁吴芬
- 教教材与用教材教 / 张玉新
- 听课杂感 / 史绍典
- 寻找课文的最佳突破口 / 黄玉峰
- 语文教学需要诵读 / 陈树元 许焕杰
- 让美读引领语文课走向高境界 / 刘占泉
- 课例二:诵读: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 周选杰
- 课例一:品味文 / 周海燕
- 陈日亮先生的贺信(节选) / 佚名
- “墨池水暖”永相随 / 顾黄初
- 章熊先生的发言 / 佚名
- 章熊语文教育思想研讨会在京隆重召开 / 雨 丝
- 张志公先生与中语会的创建 / 陈金明
- 新课程理念下语文课怎么“讲” / 吴春林
- “无中生有式创造性阅读”批判 / 李海林
- 方法也要传授 / 谢金梅
- 混乱的“能力利益”模型 / 马豫星
- “语文素养”模型的冷思考 / 喻 玲
- 语文教育模式的变革非同小可 / 余应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