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教学之友 2007年第11期
ID: 359499
语文教学之友 2007年第11期
ID: 359499
高语第三册古诗文译注商榷
◇ 陆宗成
文言文译注的原则是信、达、雅。笔者在执教、教研时发现,现行人教版高语第三册文言文的某些译注有悖以上原则,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信而不达”、“达而未雅”、“雅而未信”等问题。现不揣浅陋,择几例试析之。
1.及既上,苍山负雪,明烛天南。(姚鼐《登泰山记》)
“苍山负雪,明烛天南”,课本译注:“青山上覆盖着白雪,(雪)光照亮了南面的天空。负,背。烛,照。”此译注中将“明”处理为“光”,不对。查《古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和《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明”均无“光”义项。“明”的本义是“明亮,光明”,“东方明矣,朝既昌矣”(《诗经·齐风·鸡鸣》)“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孟子·尽心上》)中的“明”用的就是本义。“明烛天南”中的“明”用的正是本义,“明烛”是倒装,还原即为“烛明”,意即“照亮”。所以,“苍山负雪,明烛天南”宜译注为:“青山上覆盖着白雪,(雪光)照亮了南面的天空。负,背。明,明亮,亮。烛,照。”
2.是以蓼洲周公,忠义暴于朝廷,赠谥美显。(张溥《五人墓碑记》)
“赠谥美显”,课本译注:“指崇祯皇帝赠周顺昌为太常卿,谥为忠介。美显,美好而光荣。”此译注中将“美显”处理为“美好而光荣”,不妥。其实,“赠谥美显”是“合叙”,要分开来理解,而且次序上又有错综,分开来说,就是“赠显谥美”。《广雅·释言》:“赠,称也。”王念孙《广雅疏证》:“‘赠’之为言‘称’也。”对死者追封爵位也叫“赠”,崇祯皇帝曾经赠周顺昌为太常卿,谥为“忠介”。所以,“赠谥美显”宜译注为:“封赠显耀,谥号美好。美,美好。显,显耀。崇祯皇帝曾经赠周顺昌为太常卿,谥为忠介。”
3.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而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归有光《项脊轩志》)
“偃仰啸歌”,课本译注:“偃仰,俯仰,这里指安居,休息,形容生活悠然自得。啸歌,长啸或吟唱。这是显示豪放自若。啸,口里发出长而清越的声音。”此译注欠妥。前面讲“借书满架”,后面讲生活上“悠然自得”、“豪放自若”,意思明显脱节。考查“偃仰啸歌”后面的句子,不难发现,“万籁有声”是“冥然兀坐”所闻,而“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是“庭阶寂寂”所致,那么,“偃仰啸歌”定是“借书满架”而生。“偃仰”、“啸歌”紧承“借书满架”,当状读书之体态以及读书之声音。古人读书,有摇头吟诵(歌咏)之习。所以,“偃仰啸歌”宜译注为:“偃仰,俯仰,这里指摇头。啸歌,长啸或吟唱,这里指歌咏。”
4.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欧阳修《伶官传序》)
“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课本译注:“虽然说是天命,难道不是由于人事吗?古人常把王朝的盛衰归之于天命,欧阳修没有否定这种传统说法,但重视人事(主要指政治上的得失)的作用。”此译注中将“人事”等同于现代汉语的人事,不对。在现代汉语中,“人事”是一个名词。而在古汉语中,“人事”是两个词,“人”是名词,“事”是动词,就是“做,为”。 “人事”,不妨译成“人为”。所以,“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宜译注为:“虽然说是天命,难道不是人为吗?事,做,为。古人常把王朝的盛衰归之于天命,欧阳修没有否定这种传统说法,但重视人为的作用。”
5.古人云:“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此言得之。(苏洵《六国论》)
“此言得之”,课本译注:“这话对了。得,适宜、得当。之,指上面说的道理。”此译注将“得”处理为“适宜、得当”,不对。如果将“得”释为“适宜,得当”的话,那么“得”就是形容词,不可带宾语“之”。既然将“之”释为“指上面说的道理”,那么“得”就应该是动词,否则不合语法。其实,从语境看,“得”就是“得到”,可以翻译为“说中”、“说出”等。所以,“此言得之”宜译注为:“这话说出了上面说的道理。得,得到,说出。之,指上面说的道理。”
6.向使三国各爱其地,齐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将犹在,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苏洵《六国论》)
“当”,课本译注:“通‘倘’,如果。”此译注断章取义,不对。如果单独看“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这两个分句,将“当”释为“如果”,说得过去,但如果联系整个句子来看,却不对。这段引文整个是一个条件复句,“向使”领起条件分句,直到“良将犹在”,“则”引起推导结果分句,直到“或未易量”。在结果分句中,“胜负之数,存亡之理”是主语部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是谓语部分。因此,“当”是“应当”之义,“相较”是“相当”、“差不多”的意思。所以,“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宜译注为:“应当跟秦国差不多,也许难以估计谁胜谁败谁存谁亡。当,应当。相较,相当,差不多。”
7.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耶?(苏洵《六国论》)
“互丧”,课本译注:“彼此(都)灭亡。互,交互,由此及彼、由彼及此。”此译注将“互”释为“交互,由此及彼、由彼及此”,不妥。六国灭亡是有次序的,并没有混杂在一起“交互”灭亡。“互”在古代有两义:一指交错、交替;一指挂肉的架子。《周礼·地官·牛人》:“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郑玄注:“互,所以挂肉也。”因其能连接两个事物,所以其引申为“一个承接一个”之义。“互相”强调的是共时层面的交互性,而“承接”强调的是历时层面的延续性。引文“互”字正用“承接”义,非“交互”义。所以,“互丧”宜译注为:“相继灭亡。互,承接、相继。”
8.摄提贞于孟陬兮,唯庚寅吾以降。(屈原《离骚》)
此句课本译注为:“摄提那年正当孟陬啊,就在庚寅那天我降生。摄提,星名,指寅年。孟陬,指正月。庚寅,指庚寅日。屈原诞生于寅年正月庚寅日。降,降生。”此译注将“摄提”释为“星名,指寅年”,不准确。这里使用的是太岁纪年法。古人根据岁星(木星)在天体中运行的规律来纪年,木星大体是十二年绕天一周,由于它是由西向东运行,与十二辰的方向、顺序正好相反,故古人又设想出一个假岁星叫做太岁,让它与真岁星背道而驰,这样就和十二辰的方向、顺序一致,这种用来纪年的方法就叫“太岁纪年法”。古人又取了“摄提格”、“单阏”、“执徐”等十二个太岁年名作为“太岁在寅(卯、辰)”等十二个年份的名称,屈原即诞生于“太岁在寅”年。所以,“摄提”宜译注为:“即摄提格,太岁年名,相当于寅年。”
9.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姜夔《扬州慢》)
“清角吹寒”,课本译注:“凄清的戍角在寒气中吹着。当时扬州有宋兵戍守。”此译注欠佳,未能很好地揭示词句的真意。《宋词选》将此句注为:“凄清的号角吹来了寒意。”这样理解要精确得多。号角本身并无感情可言,吹出来的声音无所谓寒暖。但是,处在金兵压城、宋军常常闻风溃逃、城市随时被包围和攻陷的情况下,人民的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处在这样境遇下的人们,听到戍卒的号角,只能感到胆战心寒。所以“吹来了寒意”,恰到好处地描绘了当时扬州的萧条、冷落和词人的悲凉心情。(《唐宋词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版1748页)对此句的分析也可为佐证:“‘清角吹寒’四字,‘寒’字下得很妙,寒意本来是天气给人的触觉感受,但作者不言天寒,而说‘吹寒’,把角声的凄清与天气联系在一起,把产生寒的自然方面的原因抽去,突出人为的感情色彩,似乎是号角声把寒意散布在这座空城里。”
10.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姜夔《扬州慢》)
“杜郎俊赏”,课本译注:“杜牧善于游赏。俊赏,卓越的鉴赏力。”此译注将“俊赏”处理为“卓越的鉴赏力”,不妥。“俊赏”,即“俊赏者”,名词性词组作谓语。“俊”,《说文解字》:“材过千人也。”“俊赏”,最会欣赏。如钟嵘《诗品序》:“近彭城刘士章,俊赏之士。”“俊赏者”,即“最会欣赏的人”。所以,“杜郎俊赏”宜译注为:“杜牧是最会赏景的人。俊赏,既‘俊赏者’。”
11.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封狼居胥”,课本译注:“汉朝霍去病追击匈奴至狼居胥山(在现在内蒙古自治区西北部),封山(筑土为坛以祭山神,纪念胜利)而还。”此译注将“封山”释为“祭山神”,不妥。“封”与“禅”都是古代祭祀的专用名称。“封”,专指筑土为坛以祭天;“禅”专指筑土为坛以祭地。《辞源》(修订本)注为:“封,筑土为坛祭天,报天之功。”《古代汉语常用字字典》(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71页)“封”(2)条下注云:“古代帝王在泰山上筑坛祭天的一种迷信活动。《史记·秦始皇本纪》:‘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可见,“封山”是“祭天”而不是“祭山神”。“封山”不是动宾式合成词,而是“封于山”的省略,这里的“山”当理解为封的地点,而不是封的对象。所以,“封狼居胥”宜译注为:“汉朝霍去病追击匈奴至狼居胥山(在现在内蒙古自治区西北部),在山上筑土为坛祭天后才返回。封,指筑土为坛祭天。”
(作者单位:天柱县第二中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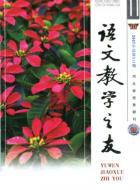
- 寻求语文教学的“本然” / 郭治锋
- “妄谈”语文教改 / 赵秀菊
- 语文教育的“一个中心”“两个层面” / 姚江红
- 同课异构:繁荣下的隐忧 / 王 侠
- 试谈提高语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 张淑霞
- 享受语文的意蕴美 / 冯效国
- 下定义也不失为一种教学过程和方法 / 苏发元
- 让初中生写些课后记 / 徐益明
- 论语文课堂中粉笔板书的作用 / 吕内巧
- 唤醒学生的生命意识 / 朱益群
- 新课标对语文知识的误解 / 邵怀领
- “自选动作”与“规范动作”的结合 / 黄克恭 尹继东
- 由教师懂诗说开去 / 张 敏
- 浅谈中学诗歌的意境教学 / 刘经德
- 让学生饱览“方塘”美景 / 薛 成
- 在信息技术与复原活字印刷术的整合中教学《活板》 / 侯 冰
- “一朵流星”之我见 / 李 瑞
- 《陋室铭》教学“三读” / 宁克兵
- 彭家木≠彭加木 / 刘万想 翟 霞
- 曹刿的取胜之道 / 徐长清
- 返璞归真平添几多韵味 / 温应朝
- 《荷花淀》改写 / 赵爱东
- 高语第三册古诗文译注商榷 / 陆宗成
- 《项链》教学点滴 / 吴昌宝
- 小处见大 笔曲意深 / 于 扬
- 巾帼风采胜须眉 / 王 英
- 高三作文教学的思考与实践 / 覃克良 李兆丹
- 学校作文:成人主宰的世界 / 肖连珠
- 用比喻照亮文章 / 王正龙
- 日记评语体式探微 / 杨育云
- 以词解句 由表及里 / 刘鹏红
- 再析杜十娘的悲剧形象 / 吕言侠
- 《逍遥游》亦可为高中讲读课文 / 李政林
- 浅析《现代汉语词典》对“差点儿”释义的疏漏 / 蔡焕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