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教学之友 2007年第11期
ID: 359479
语文教学之友 2007年第11期
ID: 359479
语文教育的“一个中心”“两个层面”
◇ 姚江红
新课标明确了语文教育的“一个中心”:培养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这一点已经成为语文教育界的共识。
语文课程的性质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对此,巢宗琪先生作了注解:“‘工具性’着眼于语文课程培养学生语文能力的实用功能和课程实践性的特点;‘人文性’着眼于语文课程对学生的思想感情的熏陶感染和文化功能和课程所具有的人文学科的特点。”①有人据此认为,语文教育包括语言教育和文学教育,语言教育体现的是工具性,文学教育体现的是人文性。
语文教育是语言教育还是文学教育的问题,其实质是对语文教材的处理问题,是对课文的处理问题,具体又落实在文体的分类上。
文体的分类研究源远流长。“五四”以后,文体的二分法日趋一致,研究者们以是否虚构和使用典型化手段为标准,把文学作品和文章分开。文学作品一般分为小说、散文、诗歌、剧本,文章则分为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和应用文。
现行语文教材文体分类正是基于此。
一、关于语言教育
“语文本体乃语言。”而“基础教育阶段设置语文科的主要价值取向在于培养和提高母语基本的读写听说能力,教会学生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是它的特有任务、专有任务乃至根本任务,而并非要培养什么作家、诗人”。②据此可知,语文教育最基本的任务是进行语言教育。具体到教学上,“我以为语言教育要做到科学、系统的汉语知识与典范的汉语言作品双管齐下,并使之相得益彰。科学、系统的汉语知识能使学生对汉语有一个较为全面、深入的理性认识,并为培养准确、灵敏的语感打下必要的基础”。③
语文教育主要是培养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而人的能力是存在个体差异的,因此,语文教育也不可能培养出一群具有相同语言能力的“标准”个体,而只能培养一群在语言能力上有着层次差别的人,实际教学所达成的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有的学生难以写出有文采的文章,对有丰富言语义的句子感到无从理解,而有的学生对此却得心应手。
二、关于文学教育
首先对什么是文学教育要有一个清晰的界定。须引起注意的是,“文学教育”是个有歧义的概念,目前至少有三种内涵:一种是在语文教育视野中的文学教育;另一种是审美意义上的文学教育(即文学课),以及文学创作意义上的文学教育。譬如:“让学生受到美的熏陶,培养自觉的审美意识和高尚的审美情趣,培养审美感知和审美创造的能力。”(新课标语)爱因斯坦说:“文学艺术的最大价值就在于能够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这些论述都是立足于后两种意义上的文学教育。
显然,我们在这里要探讨的是语文教育视野中的文学教育。在这一特定视野中,文学教育是作为语言教育的特殊形式,即通过作为语言运用典范的文学作品而进行的语言教育。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文学作品的教学绝不等于文学课。为了完成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培养读、写、听、说等语文能力,在语文教学中须力避把语文课上成文学课,坚持把文学作品当作普通文章教的原则。”④这里的“文学课”显然是指文学欣赏课。
语文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对于大多数受教育者来说,接受语文教育是为了今后能适应社会生活,提高基本的语文运用能力,因此语文教材中的文学作品,首先应将其作为语言运用的例子加以对待。这是将文学作品选入中学语文教材的出发点,只可惜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忘记了当初是怎样一个开始。当然,这样做还应该有一个前提,即“必须服从语言教育的需要”。⑤
有人担心“把文学作品作为传授语言学知识和训练听说读写能力的工具和范例,其实是消解了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本质特征和意义,文学的审美意义没有得到强调”⑥,“因为文学教育的核心是对人的生活、人的命运进而对人的生命体验最后落实到对人之为人的人性、人情、人道的感受与感悟,这与以正确理解与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知识、能力为旨归的语言教育毕竟是两回事”。
其实,不管对文学教育的功用进行怎样动人的描述,虽然文学作品和普通文章是文体的两大类别,但在运用语言文字来表达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态度方面,二者又具有同一性。从学生角度来说,他们上语文课,其实不是去“学”文,而是主要“用”这一篇文里的东西,或借选文所讲的东西、或由选文所讲的东西触发,去从事一些与选文有关的语文活动。也就是说,不在于学习“写什么”而在于学习 “怎么写”。“写什么”毕竟是有限的,而“怎么写”却可以让学生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能从容应对语言运用的各种问题。这就要求“语文教师根据文体的这一共性,把文学作品当作普通文章来教,这也与文章阅读的基本法则相符合”。⑦
对此,叶至善在《文章例话》的《重印后记》中就明确指出:“在讲文学作品的时候……主要讲如何理解,如何体会,如何从中学习一般的写作方法,而不谈什么文艺创作。”⑧
叶圣陶在《文章例话》中还作出了示范。他引导我们从小说中学习事件的记叙和景物的描写,从剧本中学习人物的对话,从诗歌中学习情境的真切和语言的精彩。例如他选读《社戏》时,就特别注重其开头部分,他写道:“为的拿它作为例子,说明写文章的一种方法。”例如,《社戏》中写作者第一回看戏时的情形:“几个红的绿的在我眼前一闪烁,便又看见戏台下满是许多头。”用叶老的话来说,这是一种“依看着听着的当时的感觉写”的方法。教师应当运用这段描写的文字作“例子”,教给学生掌握这种依据当时当地感觉写事物的方法。这样,便是把小说当作记叙文“例子”教学了。⑨
有人曾把文学教育比作青少年身上的“通灵宝玉”(王尚文语),但实际上真正能获得这种灵性的毕竟是少数。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语文课带给他们的教益主要还是掌握了基本的语言运用能力。具体地说,就是听说读写的能力。而从学生将来的发展来看,大多数人还是成为普通劳动者,成为作家、诗人的毕竟是少数。因此,从务实的角度考虑,语文教育首先要立足于培养学生的基本语言运用能力,以免事与愿违:期望“鱼”和“熊掌”兼得,结果却是两头落空。长期以来,我国的语文教育确实存在贪多求全的思想,其结果是“少慢差费”。
联系当前语文教学的实际,我们不难发现,“文学教育为主导的语文教育带有明显的贵族化教育的痕迹,因为以文学教育为主导的语文教育虽有其正面作用——有助于个体修养的提高,但也有其负面作用——为日后少数人所使用的教得很多,为日后多数人所使用的教得很少”。⑩这里的“少数人”即前述之培养“作家、诗人”。
其实,要进行文学欣赏或文学创作意义上的文学教育,现行的语文新课标已经为此提供了充裕的实施空间,通过选修课程就可以满足部分爱好文学的学生个性化的发展需求。这样既实现了全面的语文课程教学目标,又兼顾到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需要,体现了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
“学语文就是学语言(包括语言的形式及其承载的内容),其最重要的媒介与载体便是言语作品,文学作品当然是一类重要的言语作品。” 因此有人提出,“把文学作品当作普通文章教的原则”。这与新课标相符,也与学生语文学习的实际相适应。
显然,文学作品只是“一类”言语作品,此外还包括非文学作品的文章。在语文教育界还存在一种倾向:一讲到人文性,似乎只有通过文学作品才能达成,以致形成文学化的教学倾向。固然,文学作品教学对于培养学生人文精神来说确实是它的擅长,但不能因此就认为在其他非文学作品的文章中不存在人文精神的因子。例如,在应用文中我们可以体会简洁之美、效率意识;通过议论文,我们能体验到哲理之美,思维的严密;一些说明文又让我们领略了人类伟大的创造精神等等。这些都是人文性的成分。
文学作品在语文教育中的价值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作为经典“例子”(叶圣陶语)言语作品的价值;一是满足人情感、道德等需要的审美价值,或可称为工具价值和人文价值。
因此,语文教育应立足于“一个中心”,即以培养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为中心;两个层面,即语言教育的大众化层面,及部分学生的文学欣赏(审美)或文学创作的个性化发展层面。
参考文献:
①巢宗琪《关于语文课程性质与基本理念的对话》,《语文建设》2002(7)。
②屠锦红《关于“文学教育”的几点意见》,《语文教学之友》2006(3)。
③⑤王尚文《语文课程的复合性》,《课程·教材·教法》2006(12)。
④⑦⑧⑨曾祥芹《文章学与语文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⑥胡俊国《对建国以来文学教育论争的清理》,《教育评论》2004(12)。
⑩邰启扬、金盛华《语文教育新思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单位:衢州学院中文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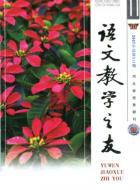
- 寻求语文教学的“本然” / 郭治锋
- “妄谈”语文教改 / 赵秀菊
- 语文教育的“一个中心”“两个层面” / 姚江红
- 同课异构:繁荣下的隐忧 / 王 侠
- 试谈提高语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 张淑霞
- 享受语文的意蕴美 / 冯效国
- 下定义也不失为一种教学过程和方法 / 苏发元
- 让初中生写些课后记 / 徐益明
- 论语文课堂中粉笔板书的作用 / 吕内巧
- 唤醒学生的生命意识 / 朱益群
- 新课标对语文知识的误解 / 邵怀领
- “自选动作”与“规范动作”的结合 / 黄克恭 尹继东
- 由教师懂诗说开去 / 张 敏
- 浅谈中学诗歌的意境教学 / 刘经德
- 让学生饱览“方塘”美景 / 薛 成
- 在信息技术与复原活字印刷术的整合中教学《活板》 / 侯 冰
- “一朵流星”之我见 / 李 瑞
- 《陋室铭》教学“三读” / 宁克兵
- 彭家木≠彭加木 / 刘万想 翟 霞
- 曹刿的取胜之道 / 徐长清
- 返璞归真平添几多韵味 / 温应朝
- 《荷花淀》改写 / 赵爱东
- 高语第三册古诗文译注商榷 / 陆宗成
- 《项链》教学点滴 / 吴昌宝
- 小处见大 笔曲意深 / 于 扬
- 巾帼风采胜须眉 / 王 英
- 高三作文教学的思考与实践 / 覃克良 李兆丹
- 学校作文:成人主宰的世界 / 肖连珠
- 用比喻照亮文章 / 王正龙
- 日记评语体式探微 / 杨育云
- 以词解句 由表及里 / 刘鹏红
- 再析杜十娘的悲剧形象 / 吕言侠
- 《逍遥游》亦可为高中讲读课文 / 李政林
- 浅析《现代汉语词典》对“差点儿”释义的疏漏 / 蔡焕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