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大语文论坛 2013年第3期
ID: 354862
中学语文·大语文论坛 2013年第3期
ID: 354862
辛弃疾词中的豪雄悲壮之气探源
◇ 杨建平
打开《稼轩长短句》,就似有一股强劲的狂风袭来,又似站到了汹涌东去的大江之畔,亲临萧萧易水的送别场面,又如远观火山爆发的惊心动魄,又象进入练兵的教场、鏖战的沙场。
这种逼人之势、动人之力首先表现在他的词很有力度。“岭头一片青山,可能埋没凌云气?”用“凌云气”来说明辛词的特异和特长之处是极恰当的。这种豪壮之气很有力度,就象伏流千里遇隙激射的清泉,又象密云不雨时的电光。
辛弃疾词中的豪壮之气,还在于他的词很有韧劲。前人所说的“稼轩风”,就是他野鹤闲云般的萧洒风神和壮心不改的英雄本色相融合形成超乎作品情理之上,又流贯于其中的内外在结合的力度,使读者感发激动的冲力。辛词的逼人之势,动人之力在于韧劲,不是骤起骤去的山洪,不是忽开忽谢的娇花弱瓣,而是岁寒不凋的常绿松柏,每一首词都象醉酒一样有持久不衰的后劲。
然而辛词的“凌云气”从何而来?为何而来?下面想从社会环境、创作主体、前人影响及地域文化等几方面进行初步探讨。
一、社会与心灵撞击的火花
辛弃疾所处的南宋时代是一个剑与火、血与泪的时代。“靖康之变”后,女真人入主中原,进行大规模掳掠,汴京被焚烧。农村的惨象也是空前的:“两河之民,更百战之后,田野三时之务,所至一空,祖宗七世之遗,厥存无几。”在这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收复失地,救亡图存,统一中原,成为当时社会生活的主旋律,时代精神的最强音,震撼着每一个大宋子民的心灵。作为一个家乡沦陷,决策南归,以身许国的抗金志士,辛弃疾更是深深地感受到这国破家亡的切肤之痛,坚定不移地以统一大业为己任。南北纷争的混乱局面,匡扶王室,廓清中原的斗争需要,为人们施展才华大展宏图创造了一个广阔的天地。辛弃疾作为有志之士,在这风云变幻的时代就选定了“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这一理想目标。
辛弃疾词中诸多情绪的根源与他的家庭教养也是密切相关的。辛弃疾的祖父辛赞虽屈仕于金朝,却常怀国仇家恨,对辛进行形势教育,并带他赴燕山视察,培养他的军事识略。“每退食,辄引臣辈登高望远,指画江山,思投笔而起,以纾君父不共戴天之愤。”他的幼小心灵已深深打上驱逐敌人、洗耻去辱的烙印,决心为收复祖国山河的鲲鹏之志而献身。
起义南渡,托身南方,可他万万没想到,被认为是“归正人”,始终不被朝廷信任。何况,“剩水残山无态度”的朝廷也根本没有恢复之心。他痛感国破家亡之苦,深抱“忠而见疑”之怨,盼望恢复的心就自然更加强烈了。“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有志报国,无路请缨,性本刚毅,心求奋进可总受阻,抑制与反抑制相冲突,炽烈的心肠遇到了重闸大网般的沉闷现实。本有桀骜不驯之气的辛弃疾当然满肚子的怨愤之气,喷射出来,化为词间的浩然之气。看他的《摸鱼儿淳熙已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为赋》,这首千古名作,下阙借陈皇后与汉武帝故事以抒发壮志难酬的感慨。辛弃疾以甫逾弱冠之年,即举兵抗金杀敌归朝,陈述恢复大计,本想独当一面,施展才华。哪知南归二十年,才做了一个管钱谷之事的转运副使。此次迁官,仍是副使,怎不使他大失所望呢?当时国势危殆,使他担忧;有志之士不能进用,使他愤慨,但作为“归正人”许多情况不能直言,就用迂回曲折,含蓄地抒发自己的“不平之鸣”。所以下阙遂抒发怨愤之情“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朝廷腐败无能,小人当道误国,鸿鹄之志难以施展,壮志难酬。“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情意沉痛,刚柔相济,豪壮之气纸上奔腾。总之,辛弃疾处在危难时代,加上良好的家庭教养,幼时就有“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湖沙”、“他年要补天西北”的远大志向。他志在报国却偏又遇到的是腐败的朝廷,无能的统治者。壮志难酬,“负管乐之才,不能尽展其用”理想与现实的反差,一腔忠愤,无处发泄。“故其慷慨悲歌,抑郁无聊之气,一寄于其词。”
二、创作主体灵魂的升华
辛弃疾是以武人的形象出现在词坛上的,他目睹国家的危机、民族的灾难,亲自体验了国破家亡的切肤之痛,立志“整顿乾坤”“少年横槊,气凭陵,酒圣诗豪余章”。他既不热衷功名,也不追求富贵,而是寻找起事的时机。1162年,年仅22岁的辛弃疾热血沸腾,怀着杀敌报国的强烈愿望,起义并智斩叛徒张安国南归。“壮岁旌旗拥万夫”的英雄壮举,在以后的记忆中常常闪现。他的豪杰之词也正是这种壮举英概的真实掠影。
单凭一腔热血是不能铸就千古文字的。更重要的是“平生塞北江南”的丰富阅历,再经过富厚才学的烹炼,故言来理直气壮,自然雄健,而英气内敛,萦纡辞际,吐属又复沉郁。况且学识广博,总结反思历史,对现实问题的认识要深刻,更有卓见。[汉宫春]写:“谁念我,新凉灯火一编太史公书。”透露了他带着现实问题读史思考的信息,难怪他的词写得理得词顺,情挚气充。再者书读得饱,可以驰骋于神话传说,经史百官,随着撷取典故,慨叹历史沧桑。他早年的壮阔生活、驱逐敌人的理想在他南渡之后就化作了永远的泡影了。“辛稼轩当弱宋未造,负管乐之才,不能尽展其用,一腔忠愤无处发泄……,故其悲歌慷慨,抑郁无聊之气,一寄于其词。”他的词中情感发自肺腑,是“集义所生”,正气所凝,是他灵魂的颤音,是他生命的歌唱。
看他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这首慷慨沉郁的悲歌,唱出了词人赤心报国的雄心壮志和沸腾的激情,表达了词人怀才不遇,请缨无路的愤懑怨恨和无限痛苦。1174年,登上建康城西的赏心亭,眺望祖国的壮丽河山,浩浩荡荡的长江随着词人的目光流向遥远的天际,无边的秋色,空寂苍凉,一片渺茫。那江水无限的壮景怎不使人热血沸腾?那廖落苍凉的秋色又怎能不让词人悲慨高歌,潸然泪下?家乡沦陷,国家残破,而一个独自徘徊于赏心亭上已够悲伤了。何况又是落日楼头,断鸿声里。他多想手持锐利的吴钩,驰骋疆场,可他不被重用,英雄无用武之地。“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表现他怀才不遇、壮志难酬、年华虚度的愤慨和苦痛,吴钩看了,栏杆拍遍,胸怀报国大志,耻于归隐谋私,可谓豪矣!但愁恨郁积,落日渐鸿,又不为人知,惜年华如水,洒英雄之泪,又何其沉痛悲壮矣!这种主体人格的势能,一片青山怎能埋没!
辛弃疾一生壮志不展,更有一腔怨愤之气,但他始终高悬“补天裂”的理想,对自己不降志、不卑身;对敌人和投降派不宽恕、不妥协,到处碰壁,气越积越厚,越积越深,发泻为词。鸿鹄之志和他的不幸遭遇的极大反差,历史的兴亡之感和眼前的家国之恨,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和英雄末路的悲慨,进退两难的处境,象电位的高低差异造成高压电流,象水位悬殊形成的瀑布倾泻。
总之,辛弃疾是用全部的生命在创作,那豪壮之气是他全部人格释放的势能,是创作主体灵魂的升华。
三、屈子灵魂的闪光
辛弃疾词中的“龙腾虎掷”之气,除社会及个人因素之外,还有屈原对他的巨大影响。
看他的《蝶恋花》:“九蜿芳菲兰佩好。空谷无人,自怨蛾眉巧。宝琴冷冷千古调,朱丝弦断知音少。冉冉年华吾自老。水满汀洲,何处寻芳草?唤起湘累歌未了,石龙舞罢松风晓。”
他那坚韧执着往而不返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屈子“亦余心之行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那么相似。辛弃疾虽有过人才干,却备受朝廷当权的主和派的排挤和嫉妒,长期投置闲处,无用武之地,而且知音难觅,无人理解自己。不如意的处境使他想到了“萧条异代不同时”的千古知音屈原。所以开头就化用屈原《离骚》诗意表达与自己相类的幽怨之怀。《离骚》云:“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又云:“纫秋兰以为佩”。作者也满怀深情地来撷兰花为佩以示自己“出污泥而不染”的高洁操守。《离骚》云:“众女嫉余之娥眉兮,滛涿余以善淫。”作者也自怨“娥眉巧”而招嫉。屈原、辛弃疾同样生活在一种国家不幸,小人当道的黑暗时代。在那种环境中,“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不向恶势力屈服必遭打击和非难。本片末句化用岳飞《小重山》“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表达怨抑之情。
看下去,词人大醉之中唤起屈子来一起唱歌,人正无同调,只得求之子冥冥之中的千古冤魂。这愤溢着几多悲壮。他在《水调歌头》中:“余既滋兰九畹,又树蕙之百亩,秋菊更餐英。”前二句径用屈原句,后一句化用“朝饮木兰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引用屈原诗,意以屈原的高尚洁操自况,决不肯随波逐流与投降派同流合污,沆瀣一气。即而化用一典就更明显。《楚辞·渔父》中说,屈子放逐“游于江潭”,“形容枯槁”,渔人问他为何到这种田地,屈原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可以看出他对屈原的人格是极为推崇的。
辛弃疾英雄无用武之地,壮志难酬的愤恨,志报难伸的怨抑,又不能直言。但由于有了屈原,辛弃疾的眼光高远,气吞环瀛。辛与屈一样有搏击长空的鸿鹄之志,而对统治者“剩水残山无态度”胸中的郁闷之气,欲退不忍的心情无处外泻。浪漫的想象成了唯一理想境界。“左手把青霓,右手挟明月”;“十里张春波,一棹归来,只做个五湖范蠡,是则是,一般异扁舟,争知道他家有个西子。”“鹏北海,凤朝阳,又携书剑路茫茫。明年此日青云上,却笑人间举子忙。”“看垂天云翼,九万里风下,与造物同游。”古到今,今到古,现实与想象之间,为自己开辟了一个随意驱遣,自由驰骋的心灵空间,使人感到,气贯天地,囊括古今,并吞八荒的气魄。真是:“其词之体,如张乐洞庭之野,无首无尾,又如春云浮空,卷舒起灭,随所变态,无非可观,无他,意不在作词,而其气之所充,蓄之所发,词自不能不尔也。”
四、南北文化交融的结晶
金人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民族性格粗旷豪爽。女真人立国专尚武功,金主完颜亮的《鹊桥仙》词可见一斑:“停朽不举,停歌不发。等候银蟾出海。不知何处片云来,做许大通天障礙。蚌髯燃断,星眸睁裂,惟银剑锋不快。一挥挥断紫云腰。仔细看嫦娥仪态。”读他的词那凶狠残酷的狰狞面目就活脱脱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也难怪史官修《实录》:诬其淫毒狠鸷,遗臭无穷。
再看海陵王已述怀诗:“蛟龙潜匿隐沧波,且与虾蟆作混合。等待一朝头角就,撼摇霹雳震山河?”可说是不够雅驯,不合于意象传统,但又确乎抒怀佳作,有撼人心魄的艺术力量。这是汉文化对女真文化的融化。同时,他们也给汉人以巨大影响。金源立国即久,狂放野逸的审美态度,为更多的文人所有,又逢时代风云振荡,社会转折时期,容易激发更为自觉的文化态度。辛弃疾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国度,女真人对他的心灵撼振是很大的。他的一些篇章,就突出地带有“深裘大马”的北方“霸蛮”之气,别人望月而胡思,对月而徬徨,他却说:“斫去桂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况且,金代词人多为汉人,吴激、蔡松年、蔡珪等大宋遗民流落中原,或哀微钦二帝之北猎,或感伤山河之残破,或悲叹久留金国不得归。吴激的《人月园》:“南朝千古伤心地,犹唱后庭花,旧时王谢。堂前燕子,飞向谁家。”还有蔡松年的《鹧鸪天》、蔡珪的《江城子》等这种凄凉婉转、渴望祖国统一、盼望宋朝廷早日北代中原,恢复家园的大宋子民们的哀泣狂吟。每每都猛烈地敲击着辛弃疾幼小的心灵。正如他的词那样强烈地摇撼着后世危难时代的人们一样。他的心中也就涌起一种洗耻去辱、报效国家的强烈欲望。他的“壮岁旌旗拥万夫“也就不足为怪了。
可以看出南北文化的融合铸就了一位有豪雄之气不太雅驯的人物。决策南归之后的他本想以“了却君王天下事”为己任。可他被置闲处英雄无用武之地。“池水凝新碧,欗花驻老江。有人独奇画桥东。手把一支杨柳系东风。鹊伴游丝随。蜂黏蕊空。秋千庭院小簾栊。多少闲情闲绪雨声中。”这是南宋人吴潜的《南歌子》,报国无门空自怨,有“经天纬地之才,安邦定国之志”可向谁说呢?由于朝廷腐败,小人当道,有志之士不能进用,壮志难酬,志报难伸之怨愤一寄于词。辛弃疾到南宋不久就深深地为这种词所撼动,并把词作为自己发泄郁闷之气的载体。看他的《摸鱼儿》、《菩萨蛮》等,他的悲壮之气在词中喷涌,这也是南北文化在他身上的第二次结晶。当然,他的悲壮是豪雄的悲壮,很有力度和韧劲。总之,南北文化的交融使辛弃疾的词有了独特的豪壮之气。
总之,辛弃疾对人不理解自己的怨愤之情,对人主体精神崇扬的阳刚之气,遗世独立追求理想的急切焦灼之心,反思人生而有的凄楚悲壮之感,相互纠缠,此消彼长,形成一种多指向的独大的感情冲击波,上下回荡于“词人制造的那个艺术空间,确有充塞宇宙,包举天下之势。今天我们不能不叹息于辛弃疾是用全部的生命在创作。那种豪雄悲壮之气是他全部人格释放的势能,是主体灵魂发出的光辉,就如屈原之于《离骚》。也正是这样,从辛弃疾词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屈的灵魂,因而也是不朽的灵魂。他把自己的人格和理想精神的闪光化为不朽的词章,赢得了“千秋万岁名”。同时,这种气是中华民族尊严,特别是危难时代不屈不挠的民族尊严的升华,它体现了民族脊梁,在国家危难时,“宁可玉碎,不甘瓦全”,誓死为国家民族利益而不顾个人安危的桀骜之气。这是民族精神的闪光。
作者单位:河南淮滨高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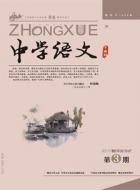
- 新课程标准下语文实现三维教学目标之路 / 杨军
- 高一语文教学的尴尬与出路 / 邢照允
- 教学评价——亮出精彩课堂 / 李淑鹏
- 浅谈构建高中语文高效课堂的策略 / 田斌
- 浅谈提高中学语文课堂教学效率的策略 / 杜开车
- 让语文课堂富有“磁性”的几点思考 / 蒋红霞
- 如何让高中生亲近语文 / 谢立琼
- 关于语文综合实践教学的策略与方法的探究 / 冯德海
- 谈文学的审美教育功能 / 许宏安
- 优化教学课堂追求诗意语文 / 牛予许
- 初中语文自学质疑模块教学策略研究 / 徐秀亮
- 读写评一体化教学尝试的研究 / 韩艳敏
- 浅谈古代传记类散文对学生的写作指导意义 / 甄志军
- 活用课本素材引导作文教学 / 张宇
- 激趣 动情 晓理 / 单乐红
- 浅析小说中环境描写的作用 / 于光宇
- 浅议文言文教学的问题 / 束莉
- 让议论文分析说理走向深入 / 朱志刚
- 人文和工具并重 阅读与表达齐驱 / 赵明发
- 诗歌教学中的整合策略探索 / 丛菊红 许建华
- 语文教学——推开影视鉴赏这扇窗 / 朱晓荔
- 新课标下农村高中课外阅读现状的反思与构想 / 朱小明
- 新课改下诗词教学策略研究 / 孙开虎
- 选择恰当的教学方法有效提高学生的作文水平 / 唐雪华
- 语文教学慎用多媒体 / 王权
- 怎样变换方式评改学生作文 / 张仕海
- 中学微作文教学初探 / 陈正燕
- 重视教学设计打造高效课堂 / 张金平
- 鲁镇到底有几个“坏人” / 李宁
- 例谈课文核心知识的确定:《师说》的文本分析 / 杨金华
- 谈林冲性格的双重性及其转变 / 董继锋
- 《金岳霖先生》课例及点评 / 李小丽/执教 陈智峰/点评
- 课堂教学要警惕“泛语文化”现象 / 姚文奎 桑进林
- 美丽的生命与生命的美丽 / 邓学东
- 《十三岁的际遇》教学设计 / 徐乙文
- 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 / 梁珍莲
- 高中语文鉴赏性阅读教学探究 / 陈伟海
- 古诗文欣赏选修课教学策略及方法 / 徐敬东
- 强化作文教学的主体意识 / 王洪琴
- 例谈古今结合训练,培养学生作文真情流露 / 王智毅
- 中学语文作文批改方法探究 / 白延海
- “巧”设情境之窗,叩响灵动“活”门 / 金文娟
- 让文言文教学更接近生命本真 / 李运梅
- 如何创设高中语文课堂问题情境 / 赵杰
- 善拓趣境为古诗文教学添双翼 / 何昔
- 诗词教学的关键——激发兴趣 / 董琴
- 速查语病的十大秘诀 / 薛峰
- 记忆方法交流平台 / 李薇 胡文勇
- 提高小说教学效率方法一得 / 胡永生
- 文言补白,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 任方菊
- 用任务引领写作,以写作带动阅读 / 温彩芳
- 以学生为本,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 孙晓芬
- 作文教学必须与阅读教学紧密结合 / 谭水花
- 以简驭繁,回归自然本色 / 王建伟
- 课堂提问的有效性 / 臧夏
- 语文课堂教学如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 饶耀东
- 也谈如何提高初中语文朗读教学效果 / 龚鸣
- 阅读“方向标” / 金友珍
- 牵线搭桥,为自主阅读插上飞翔的翅膀 / 黄桂英
- 品楼台旷远处的人生情怀 / 李双鹤
- 浅谈古诗鉴赏中的意象和意境 / 李云侠
- 苏轼词中的人格美 / 宋保印
- 辛弃疾词中的豪雄悲壮之气探源 / 杨建平
- 也谈“诗从对面飞来”的妙处 / 高红青
- “以景结情”的美学内涵 / 柳志福
- “以乐景写哀”辨 / 陈良锦
- 中年郁达夫闲适情结探究 / 石志美
- 借得东风三万里(上) / 高岩
- 生命礼赞 / 张建岭
- 让语文课堂充满快乐人情味 / 张钦辉
- 千磨万击还坚劲 任尔东西南北风 / 朱彦明
- 高考语言运用板块复习备考略谈 / 黎静萍
- 水无常形器有形 文无定式思有式 / 黄充良
- 再说审题的“三重门” / 林春泉
- 提炼——高三教材梳理复习的新视角 / 师玲 涂军
- 走出语文复习的误区 / 姚爱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