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0年第1期
ID: 136119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0年第1期
ID: 136119
回归阅读原点:呼唤“保守”的个性解读
◇ 陈连林
新课程改革大力提倡个性化阅读教学。语文新课程标准强调:“注重个性化的阅读,充分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知识积累,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获得独特的感受和体验。”“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不能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
但是在具体教学实践中,笔者也看到了个性化阅读的“泛滥”和“无节制”。任何听过由不同的语文教师教授同一篇课文的人,都会震惊:这些课实际是作为个体的教师凭自己个人的语文知识(亚里士多德称之为“臆断”)在从事教学;学生在学的,完全是由不同语文教师随意择取或任意制造的不同东西。现实中,我们对那些在教学中往往是不自觉的、即兴的、无理据或者仅以“我以为”的个人性反应为理据的教学内容,从来没有作学理的审查,从来没有验证它们与目标达成的关联。
笔者认为:个性化阅读需要“保守”解读文本,这种“保守”乃是比喻义,其实就是从文本内容出发,进行有文字依据、有语言依据的解读,而非天马行空的貌似深奥的“无厘头”“个性化”解读。
一、回归文字:“思想”与“文字”之间的偏向
个性阅读教学当然离不开语言文字的揣摩,我们所要反对的是把文字仅仅当作工具,或者借助文字讲述与语文无关的话题,譬如把语文课上成政治课、历史课、伦理课、哲学课等。我们所要的是回到文字本身,揣摩隐含在文字背后的文本意思。也就是真正体现“以字悟道”的传统道路上,也许这就是“保守”的个性解读要义所在。
以诗歌教学为例,在以前的教学中往往注重挖掘诗歌的“思想”,不错,很多诗歌是有其深刻的思想内涵的。但是,如果一味的“个性化”阅读下去,会走入牵强附会的误区。以“思想性”为背景的“深度”是作者和读者的共同幻想,我们也习惯了阅读要求的“思想深刻”。
其实文本深度是一个幻觉,我们对于诗歌要求太多,而且很多时候远离了诗歌本身的承载。如果换一种角度和思路,从作品的文字本身进入,打开思想的坚壳,我们把生命感觉和灵魂放进去,就会触及诗歌内在的血肉,尽管一开始我们并不适应。
以思想为唯一视角的传统的解读诗歌方式,非常容易滑入非诗的阅读轨道,把现实世界的生活规律和科学研究中的纯粹逻辑、抽象思维规律,等同于诗歌自身的规律。这种阅读期待是排斥“诗性”的。奥·帕斯曾经说道:“与宗教正统观念的审查相比,某些唯科学的理解更为滑稽……某些教授不懂得这些诗篇的模糊性,它们在神圣与平凡、心灵与情感、精神与肉体之间不停地徘徊。这种模糊……出现在所有伟大的神秘文本中……他们必须重新学习把诗当做诗的文本而不是社会的或心理分析的文献来阅读。”
在教学海子的诗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太多的老师是从作品的外部进入的,非常注重所谓的“思想性”,最后所分析出来的绝望、厌世等说法相当一部分根据是来自诗人的生活,尤其是海子两个月后的自杀事件。这种推果及因的方式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作为文学鉴赏而言,最后会把审美事件变成社会学事件来研究,而诗歌也变成了社会学和心理学材料,与真正的个性解读已经没有关系。最后,只剩下思想在作品外围尴尬地微笑。
“思想”变成外在的游离的“思想”,因为它与作品的文字没有关系。
从文字出发,围绕“从明天开始”、“粮食”、“亲人”、“灿烂前程”等词语剖析,有位教师提出了海子心灵的四重撕裂:
一是表层情绪与深层情绪的撕裂。
二是“今天”与“明天”之间的撕裂。
三是海子与亲人之间情感的撕裂。
四是光明与黑暗之间的撕裂。
从表层上看,《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描绘的是纯然一派春暖花开的明媚景致,但它实际展现的并非春天的现实图景,而是一幅处于生命关头诗人的心灵图景,其中交织着光明与黑暗,二者在搏杀、在撕裂。
每一首成功的诗歌,都是一次对世界全新的发现与命名。但作为阅读教学,我们所能做的首要任务是服从文字,在文字中寻觅真正的阅读“真理”,而不是我们根据自己的阅读经验去生硬地解读。
所以,“保守”的个性解读是倡导解读从文本的文字出发,服从审美的需要,而非道德的评判需要;否则会离个性化阅读的道路越来越远。
二、回归情感:“有效背景”与“无效背景”之间的抉择
在阅读教学中,我们在面对具体文本时,通常会引用作品背景帮助理解文本内容,但在倡导个性化阅读的今天,我们需要区别“有效背景”与“无效背景”。如果机械、盲目地利用背景,往往会对作品理解起到误导作用。因为这个背景不是理解作品的“钥匙”,因此是无效的。“套板效应”是近代文艺心理学的术语,原指“一件事物发生立即使你联想到一些套语滥调,而你也就安于套语滥调,毫不斟酌地使用它们,并且自鸣得意”(朱光潜《咬文嚼字》)。可以说在个性化阅读中,“套板效应”也是阻碍之一。
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一些参考书和一些教师一直把“年华易逝、壮志未酬的苦闷”作为词的主题,把作品的结句“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视作消极思想的流露。这就是“套板效应”而造成的对苏东坡的误读。据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说,苏东坡在黄州“过的是神仙般生活”,“黄州也许是肮脏的小镇,但是无限的闲暇、美好的风景、诗人敏感的想象、对月夜的倾心、对美酒的迷恋——这些合二为一,便强而有力,是以使诗人的日子美满舒服了。”
余秋雨先生在《苏东坡突围》中虽然觉得“语堂先生把苏东坡在黄州的境遇和心态写得太理想了”,但认为苏东坡在寂寞中反省过去,“无情地剥落自己身上的每一点异己成分,哪怕这些成分曾为他带来官职、荣誉和名声”,“他渐渐回归于清纯和空灵”,《念奴娇·赤壁怀古》是他“真正地成熟了”之后的千古杰作。
所以,“人生如梦”与其说是消极思想,不如说是诗人大彻大悟后对生命的一种豁达坦然。尽管学生未必会达到这样的认识,也未必一定认同这样的解读,但是如果教师能够引导学生自觉放弃“套板效应”,那么文本的多重意义就会向学生敞开。
林语堂、余秋雨就是根据苏东坡“有效背景”做出的有效的个性化解读。如果还是抱着苏东坡是被贬谪到黄州的这个背景,理解作品时就会发生偏差。
在执教季羡林先生的《幽径悲剧》时,一般只是理解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保护环境”的层次。为什么?就是背景理解的错位,以为文章中砍伐紫藤萝发生在现代社会,和经济发展中对环境的破坏有关。笔者认为
这是“无效背景”。在教学时,笔者要求学生找出含有“人”字的句子:
1.我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
2.真正的伟人们是决不会这样的。
3.这一棵古藤的灭亡在我心灵中引起的痛苦,别人是无法理解的。
4.它在控诉无端被人杀害。
5.它虽阅尽人间沧桑,却从无害人之意。
6.每年春天,就以自己的花朵为人间增添美丽,焉知一旦毁于愚氓之手。
7.在茫茫人世中,人们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哪里有闲心来关怀一棵古藤的生死呢?
接下来,我又印发给学生《牛棚杂记》相关篇章,让学生分组讨论、揣摩体悟。经过学生的“自主挖掘”,解读出“文章是对丑陋人性的批判,是对社会缺少良知的批评,是结合自身‘文革’遭遇而对当代社会虽物质丰富却精神‘愚氓’提出的呼号,表现了知识分子深沉的社会责任感。”而这样的“个性化解读”教学参考书中没有,作者也没有阐述,却体现了学生在主体阅读意识下利用有效背景正确“阅读”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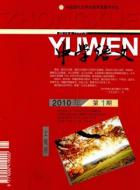
- 回眸与前瞻:语文课程文化的研究现状及反思 / 邱福明
- 《行路难》教学实录及评点 / 执教:余映潮 点评:孙竹青
- 《石壕吏》文本细读的四个问题 / 俞建科 孟兴红
- 解构与重建——语文课堂有效性要素分析 / 刘艾国
- 特别的莱辛,特别的猫 / 许 珂
- 语文课得讲究“度” / 刘小华
- 语文课堂教学内容浅说 / 梁 杰
- 一场“误会”为什么冠之以“错误” / 张 琴
- 教师“评课能力”评价方法初探 / 吴太平
- 阅读教学中“整体感知”的误用和适用 / 刘竹君
- 一曲语妙情真的游子吟 / 张所卿
- 怎一个“忽视”了得 / 赵 刚
- 抓准一个牵动全篇的切入点 / 王柳群
- 谈语言表达的虚境 / 刘有斌
- 主体内化型语文课堂模式的构建 / 陈卫东
- 回归阅读原点:呼唤“保守”的个性解读 / 陈连林
- 中学语文词汇教学漫谈 / 杨海霞
- 浅谈读为写用的作文教学 / 郑雪丽
- 浅论写作教学中的立体开发资源观 / 纪 勇
- “牛”的活用 / 赵小娜
- 现代文阅读主观题的解题意识 / 孟 华
- “套餐”新义 / 高环生
- 试论学生表达的常见缺失及实现策略 / 毕泗建
- “女红”之“红” / 牛现冬
- 思路清晰 气韵酣畅 / 刘 芹
- 《别了,不列颠尼亚》教学反思例谈 / 李虎润
- 历史幽愤的现代回响 / 孙绍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