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9年第3期
ID: 135757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9年第3期
ID: 135757
朱自清的诵读观及其当代启示
◇ 王春芳
探索和总结语文教学的规律和方法,发掘和继承中国传统语文教学中的精髓并不断创新发展是每个语文教师的义务和责任。诵读,作为中国传统的语文教学方法,在其被运用的过程中被历代语文教育者不断地改造并赋予新的成分和含义。朱自清,作为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散文作家、古典文学的研究者、中学语文教师,他对诵读的研究以及由此形成的诵读观值得处于改革背景下的我们认真地玩味和思索。
为了更好地挖掘朱氏诵读观中的有益成分并对其进行扬弃,我们先对其诵读观进行必要的梳理。
一、朱氏诵读观的内涵
诵读,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念(诗文)”。在朱自清的著述中,诵读多数是个上位概念,包含“诵”“吟”“读”“说”“吟诵”“朗诵”“朗读”等等[1]。朱氏认为语文教学应该重视诵读,因为诵读有助于了解文章真正的含义,领会文章的意蕴、神气,提高学生对美的感悟、鉴赏能力。除了能提高学生的国文水平外,还能帮助学生人格的形成及自我价值的实现。他的诵读观包括以下几个层面:
(一)诵读是个必不可少的教学环节
朱自清是把诵读作为语文教学中不可缺少的环节来论述的,他曾多层次多角度地论述诵读这个环节的过程:“可以先由教师范读,后由学生跟着读,再由学生自己练习着读,有时还得背诵。”还可以“看着书自己读,看着书听人家读”。从方式上说,可以读,可以诵,可以吟,可以说,还可以吟诵、朗诵,或者吟唱。
朱自清是从文言诗文和现代白话文两个范畴来进一步阐述这个环节的具体实施的:一般地说,现代白话文要读、朗读或朗诵,文言诗文就要配以吟诵或吟唱。如果说现代白话文的诵读要清晰响亮,即朱自清所谓“清朗”的话,那么文言文的诵读则讲究“行腔使调”,韵味十足。
先说文言诗文。朱自清对文言诗文情有独钟,他建议文言诗文“每讲完一遍,还该由教师吟诵一两遍,并该让学生跟着吟诵”。文言诗文讲究韵律、神气(或兴味)、节奏、美感,讲究“因声求气”,单凭朗读是不足以表达气韵和神采的,要表达气韵和神采就必须得“行腔使调”地吟诵。朱自清说:“现在教师范读文言文和旧诗词,都不好意思打起调子,以为那是老古董的玩艺儿。其实这是错的;文言文和旧诗词等,一部分的生命便在声调里;不吟诵不能完全知道它们的味儿。”(《再论中学生的国文程度》)他很赞赏钱基博给黄仲苏的《朗诵法》所作的序。钱先生援引姚鼐和曾国藩的话,称他们论“因声求气”最详尽。姚鼐说:“大抵学古文者,必要放声疾读,只久之自悟;若但能默看,即终身作外行也。”(《尺牍·与陈硕士书》)曾国藩说:“《四书》、《诗》、《书》、《易经》、《左传》、《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读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趣。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自觉朗朗可诵矣。”
姚鼐说的“放声疾读”、曾国藩的“高声朗读”“密咏恬吟”都非我们今天理解的“朗读”,而是集读、诵、吟于一体的诵读,是朱自清着力探讨的诵读方法。
文言诗文又分为散文和韵文。散文的诵读方法因文势而不同。比如他举唐擘黄朗诵韩愈《送董邵南序》和苏洵《乐论》的节拍为例,唐先生认为前者是二字一顿或一字一顿,如“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有六拍;后者如“雨,吾见其所以湿万物也”便只有两拍。唐擘黄说:“每秒时中所念的平均字数之多少随文势之缓急而变。如上示两例,《乐论》比《送董序》每秒平均字数多一倍(前者每秒均二、四字,后者一、二字);而它的文势也比《送董序》急得多。”一般而言,情境、情感的缓急决定着诵读文势的缓急,也就是说诵读的语气语调一定要契合文章的思想感情,要能恰当地传情达意。
韵文主要指诗。诗和散文的诵读方法不大一样。诗中的近体诗和词要吟,古体诗有时吟,有时吟诵,或者吟诵相杂。两者都有一定的曲调。朱自清是古典文学研究者,对古典诗歌有特别的兴趣。他说吟诵是古典的训练,文化的训练,有助于对旧体诗的了解和欣赏。吟诵“是诗的兴味的发端,也是诗学的第一步。”“但偶然的随意的吟诵是无用的”,因为随意吟诵虽“足以消遣”,却“不足以受用或成学”,要受用或成学,“那得下一番切实的苦功夫,便是记诵。学习文学而懒于记诵是不成的,特别是诗。”而且“中国人学诗向来注重背诵”。朱自清主张在吟诵前要熟读。“‘熟读’不独能领略声调的好处,并且能熟悉诗的用字、句法、章法。”朱自清说,诗是精萃的语言,有它独具的表现法式。学习这些法式最有效的方法是综合,背诵便是这种综合的方法。“因为声调不但是平仄的分配,还有四声的讲究;不但是韵母的关系,还有声母的关系。”而这些都需从熟读里慢慢体会。“这些我们现在其实也还未能完全清楚,一个中学生当然无需详细知道”;“但他会从背诵里觉出一些细微的分别。他会觉出这首诗调子比另一首好,即使是平仄一样的律诗或绝句。这在随便吟诵的人是不成的。”(《论诗学门径》)
朱自清没有详尽论述或举例说明旧体诗的吟诵曲调,但从他对“平仄的分配”,“四声的讲究”,韵母和声母的关系等问题的强调来看,学好旧体诗仅仅朗读两下子怕是不能深得其味的。他说:“文言诗文,最好恢复吟诵;只有在吟诵里,骈文和所谓八家文,以及近体诗,才能发挥充足的意味。”当然,他认为有些古典诗文也是可以朗读(宣读)的:“其馀经、史,和一般著述的文字,以及古体诗,可以用‘宣读’的调子,却要使每个字都有相当分量。白话诗文,也该用‘宣读’的调子;那些用口语写的,得用口语的调子说出。”(《诵读的态度》)
吟诵曲调还有地域上的差别。语言学家赵元任说:“吟律诗吟词,各地的腔调相近,吟古诗吟文就相差得多。大概律诗和词平仄谐畅,朗读起来,可以按二字一拍一字半拍停顿,每顿又都可以延长字音,每拍每顿听上去都很亭匀的,所以各地差不多。古诗和文,平仄没有定律,就没有这样客观的一致了。而散文变化更多。”(朱自清《论朗读》)笔者曾经听过一位老师讲授杜甫的《登高》,该教师把杜甫沉郁的诗风用诙谐的语言与当下学生的情感经验巧妙串连起来,并采用了一家吟诵的曲调当堂吟诵,随后让学生跟着吟诵。由于诵读过程中的朗读、朗诵、吟诵变化有致,又寓满轻松幽默,不知不觉间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让听课教师耳目一新,记忆深刻。
现代白话诗文。在现代文学史上,由于教学和文学艺术探索的目的不同,白话诗文的诵读有着形式的不同。在语文课堂教学中,白话诗文的诵读是为了培养语感,训练文脉,积累词句,提高说话和写作的水平,方法主要以朗读为主;而对于文学艺术的探索来说,除了运用朗读的方式外,还要运用朗诵和说(类似日常说话,也类似于话剧的说话)的方式。朗诵的发端是为了探索新诗的发展,摸索新诗的韵律,所以新诗要朗诵;说则是为了体现口语化文章的情感内涵,多用于信件及独白之类的文章。作为一个热衷于探索文学艺术形式的学者,朱自清不仅与时人讨论了白话诗文的具体诵读方法,而且身体力行,多次参与诵诗和说文的活动。他“说”过自己的独白体散文《给亡妇》,也听别人“说”过胡适之、康白情等人的白话诗。这些对现代白话文诵读形式的探索,对于今天多元化的语文教学来说,都能给我们很好的启示。
(二)诵读环节与分析、讲解的关系
诵读作为教学中的重要环节,它又与其它环节诸如讲解、分析相互关联,相互糅合,不可机械割裂。朱自清反对死记硬背,认为“从前私塾里教七八岁的孩子念‘四书’,并不讲,只教念,念了背”,古人“以为‘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处’”,其实所得只是“不能消化的句子”,于培养学生对文学的理解、欣赏、感悟能力是毫无用处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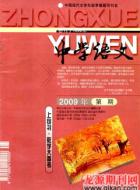
- 细读 / 史绍典
- 确定阅读教学内容的三个维度 / 胡根林
- 意义建构 / 张红顺
- 朱自清的诵读观及其当代启示 / 王春芳
- 悠长的愁 / 黄真金
- 谈《〈论语〉选读》的教学策略 / 张永飞
- 孔子的教育之道(之三) / 韦志成
- 构建有效课堂教学行为的策略研究 / 茹红忠
- 诗歌教学方法探讨 / 李高丽
- 对初中悲剧文本边缘化的反思 / 王林喜
- 也谈语文课堂的学生活动 / 蔡嘉伟
- 消除写作动力不足的有效尝试 / 王相武
- 确定性的课程内容从哪里来? / 于 龙
- 营造语文课堂良好氛围三法 / 朱宇舟
- 让厚重的文化底蕴提升作文品位 / 张来昌
- 预设诚可贵,生成价更高 / 刘晓宁
- 谈学生课堂参与 / 李先利
- 楚才作文命题的媒体取向和时代特征 / 陆 阳 张年军
- 无“读”不丈夫 / 陈永华
- 课程资源开发要回归教学意义 / 王 俊 周 於
- 作文指导三法 / 冯齐林
- 中高考语文试题命制荆楚地域文化特色摭谈 / 李 劲
- 关于树的诗文赏析(一) / 孙绍振
- 高考临场作文谨记“六先六后” / 姜有荣
- 在课程目标引领下设计课堂 / 刘 祥
- 三谈解读作品的深层结构 / 董成亮
- 不可轻视老王之“苦” / 沈坤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