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07年第11期
ID: 92833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07年第11期
ID: 92833
寻访敦煌俗文学作品研究者
◇ 孙 苹
1900年6月21日,王道士无意间打开了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引发了本世纪初最大的文物、文献新发现:古代公私文书大约5万多卷,还有幡绢绘画以及法器杂物数千件。这些藏品的制作年代,上起东晋,下至北宋,其中价值最为突出的是俗赋、变文、曲子词、儿郎伟等俗文学作品,为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填补了许多资料空白。
黄征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汉语史词汇学和敦煌语言文学,尤致力于汉魏六朝隋唐五代宋初的俗语词、俗字、俗音和敦煌变文、曲子词、愿文等敦煌俗文学作品的研究,用训诂的方法解决敦煌文献中的语言文字难题,把以前被认为无法读懂的敦煌俗文学作品解读得怡然理顺,人人皆懂。他的著作多次荣获学术大奖。例如《敦煌变文集校议》(郭在贻、张涌泉、黄征合著)曾荣获“王力语言学奖”;《敦煌变文校注》(黄征、张涌泉合著)曾荣获“中国青年语言学家奖”一等奖;《敦煌愿文集》(黄征、吴伟合著)曾荣获第十届中国图书奖;《劫尘遗珠——敦煌遗书》曾随所属丛书《陇文化丛书》荣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敦煌语言文字学研究》曾荣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并随“敦煌学研究丛书”荣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敦煌俗字典》曾荣获“江苏省高校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学术界是这样评价黄征教授的:
“他这一部《敦煌愿文集》是一部开拓性的著作。‘愿文’(还有一些别的名称)是敦煌文书中的一个大家族。但可惜过去注意的人不多,研究更谈不到。黄征教授研究这个问题,搜集如此齐全,分析如此深入,可以说是破天荒之举,实在值得我们同声祝贺。有了这样一批前途远大的新生力量,行将见我们中国敦煌学繁花满园,辉煌无限了。连我这一匹并不识途的老马也为之欢欣鼓舞,引以为荣了。”——摘自季羡林《〈敦煌愿文集〉序》
“运用校勘学、训诂学的规律,产生了质疑问难的多型研究模式和心得,像挤牛乳般滤出点滴的新血液,输入敦煌写本的体内,这些缜密的校订工作,孕育出许多语文讨论上辉煌的成果。黄征先生这五十篇大小不一的论文,是多年以来他在学圃上默默耕耘的新结集,也是他多方面不同造诣的具体表现。……”——摘自饶宗颐《〈敦煌语文丛说〉序》
孙:黄老师,您好!久仰您在敦煌文献研究与语言文学研究方面的大名,并拜读了您颇具影响的一系列著作。在阅读您的著作时,很多读者都想知道您的学术研究经历,您是怎样走上敦煌学研究道路的,您是否受到过哪些前辈的熏陶和影响。您能否就这些问题先给我们谈一谈呢?
黄:我大学的后两年对古典文学特别感兴趣,杭州师范学院的樊维刚、罗仲鼎先生给了我很多的指点,也使我逐渐留意训诂知识。当时我自感读书较晚,时不再来,所以学习非常用功,读的书比极大多数同学要多得多。除了学校图书馆的书,我还读省图书馆的书、自己买的书。我习惯在图书馆做笔记,把卡片柜中的书目按类抄撮,于是在心中建立起比较完整的知识结构,也知道哪些书是自己想读或该读的。我最早接触敦煌学的材料也是在那里,读过罗振玉编的《敦煌零拾》、刘复编的《敦煌掇琐》等线装书,把其中的敦煌曲子词全部抄录下来,连同校勘记也没有漏掉。不过,我当时万万没有想到三年之后竟专门研究起敦煌学来。
1985年我考入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攻读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学位。当时读的是研究生班,由于是个七个人的班,而且学制二年,导师不固定,所以第一年全靠自己摸索。不过我还是很幸运的:姜亮夫先生是我们导师,沈文倬、刘操南、郭在贻、张金泉等著名学者都是我们的任课教师,我的毕业论文是著名训诂学家、敦煌学家郭在贻先生指导的。我也广泛钻研其它先生的著作,尤其是姜亮夫、蒋礼鸿先生的著作,他们都是敦煌学的最著名专家,同时也都是语言文字学、文学的专家。两年学习后我顺利毕业,并在郭在贻先生的推荐下留校到中文系工作。
1990年我考取所在中文系汉语史专业训诂学方向在职博士生。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先生都是我的导师。我之所以以训诂校勘学为根底,而又从事敦煌文献、敦煌语言文学的研究,就是直接受到了三位导师的影响,他们的“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的学术精神自始至终影响着我的学习和研究。
孙:2007年1月27日,南师大隋唐敦煌写经卷首度公开亮相。如今,这3卷价值千万的敦煌卷子的真实性和学术价值已经得到了学者们的公认。听说文学院两代学者为收藏与鉴别这3卷敦煌写经卷的真伪付出了巨大努力。您能不能给我们详细地谈谈经过呢?
黄:谈到这个问题,的确有故事可讲了。这3个敦煌卷子是南师文学院前身中文系的第一任系主任、著名诗人孙望教授在1956年花了130元从北京琉璃厂买回来的。孙先生带回敦煌卷子之后,也曾邀请一些专家学者来鉴别真伪,但是大多数人口头赞叹而内心存疑:若说是赝品,又没有依据;但若说是真品,为何纸色、墨色都刷新的呢?尤其是“文革”时期,孙望教授更因为“乱花钱买假古董”而遭遇批斗,蒙受多年不白之冤。于是,更多的时候这3卷隋唐敦煌写经卷子就锁在文学院资料室的一个简易书柜里。当时我还在浙江时,跟施谢捷教授一直都有书信来往,所以两人熟识较早。后来我1999年来南师大工作,施谢捷教授告诉我文学院资料室藏有3卷隋唐敦煌写经卷子,建议我去看看,能否鉴别一下真伪。于是我们就向院长作了请示,去资料室看看这3卷写经卷。当时柜子锁着,我也没有钥匙,征得院长同意后,我轻轻一拨,就打开了柜子,见到了3个用牛皮纸袋简易包着的写经卷子。这3卷写经卷子都很长,其中一个纸张特别新,墨色也特别新,上面像用铅笔画出来的格子也特别清晰。很多人都会认为这个卷子不可能是真品。可是我一眼就认定这一卷肯定是真品。其实它的“新”是有原因的:古代有的经卷不是常用的经,所以保存完好,簇新如今。敦煌经卷中,做功德捐赠寺庙的,如今往往有成百上千卷抄本保存下来,都是当时常见常用的,由于经过很多人的翻阅以及灰尘等因素,相对而言就比较破旧,无论纸张还是墨色都比较暗;另一种经是平时很少有人看的,换句话说,抄完后基本上再也没有人去翻阅,古今历史上可能也只有管理员翻一翻,这种经基本没有磨损,所以就很“新”。但是,鉴别真伪是比较复杂的事情,我们不能仅凭自己的感觉,是真是假需要拿出证据来,尤其是要找到铁证,才能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为此我查阅了各国藏卷的目录,终于在大英图书馆所藏敦煌写经卷中发现了与南师大文学院藏01号卷子相同名目的经卷(编号S.4718),经过细心比对,结果发现正好与南师大所藏隋唐写经卷01号前后衔接,两者可以完全缀合。既然大英图书馆所藏经卷的真实性在国内外学术界是公认的,二者可以缀合,那么就证明了南师所藏隋唐写经卷也是真品。自从我的这条证据列出来,立刻得到国际敦煌学界的一致承认。因为这是不可动摇的铁证。我终于用我的研究为孙望先生洗清不白之冤,为学术界挖掘出一份珍秘资料,也为南师大平添了无价重宝。
孙:敦煌真是一个宝藏!栖霞山石窟向来被誉为“江南云岗”、“江南敦煌”,“栖霞飞天”是否与敦煌飞天有很密切的联系呢,黄老师您怎么看待这些问题?
黄:栖霞山的千佛岩被人们誉为“江南云岗”、“江南敦煌”,其实,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就跟我们常说“塞上江南”是一样的道理。栖霞山千佛岩保留了南朝的造像艺术,窟内的壁画我亲自去考察过许多次。“栖霞飞天”轻衣长带,卷舒自如,异常生动,至今还留存着当年起稿时所打的底线。栖霞山石窟最早开凿于萧齐永明二年(484年),敦煌莫高窟最早开凿年代在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年代很接近。敦煌莫高窟早期的壁画体现的是比较粗犷的北方风格,而栖霞山的壁画则是比较柔和细腻的南方风格。后期的敦煌壁画变得细腻柔和,明显受到了南方画风的影响。有一点需要指出,千佛岩壁画由于气候潮湿,自然风化严重,几乎全部脱落,残留的也不完整。事实上整个南方就没有保存下1000年前的壁画,所见的就这点遗迹。有鉴于此,“栖霞飞天”壁画就“奇货可居”了,有人认为面积很小没价值,完全是以大小论高低,不值一哂。“栖霞飞天”对于敦煌文化传播和演变、南北文化交流的研究,毫无疑问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
孙:您刚才提到敦煌文化,那您能不能谈谈敦煌学研究对古代文学史以及西域文化研究的贡献呢?
黄:莫高窟藏经洞出土文献的发现以及研究,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一大批珍稀资料。这些敦煌文献中有失传很长时间的变文、词话、讲经文、故事赋、历代诗词等,还有少数民族的诗歌、散文、旅行记等等,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宝库,填补了古代文学的空白。
敦煌文献还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西北地区的民族文化提供了大量资料。唐五代宋初是我国西北地区民族大融合的阶段,但传世史籍记载较粗,很难据以进行深入系统的考察。敦煌文献保存了一批反映这一时期民族情况的汉文、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等的公私文书,为我们探讨西北地区民族文化与相互间的交往提供了难得的宝贵资料。根据敦煌文献,我们在对少数民族文字历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方面也有较大进步。
孙:您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刚才提到的敦煌文学文献呢?
黄:敦煌文学文献有敦煌变文、曲子、王梵志诗、敦煌杂诗、儿郎伟等许多种类。
敦煌变文包括变文、因缘、讲经文等类别,是唐五代宋初流行于全国的说唱文学形式,南宋以后被禁而失传,因此传世文献中一篇都没有保存下来。由于敦煌变文的发现,使得文学史上一系列的重要问题得以解决,尤其是宋元话本的来源问题。
曲子即词,唐代称当时民间流行的杂曲歌词为“曲子”,所以今之学者有称敦煌词为“曲子词”的。敦煌曲子的创作年代大约起于盛唐时期而止于宋初。敦煌曲子的出现,给本就丰富多彩的唐代文学又增添一道清新动人的风景。敦煌曲子的作者绝大多数都是民间的无名氏,他们的身份非常复杂,有乐工,有歌伎,有游子,有征夫,有思妇,有僧人,有道士,有妓女,有商人,有士卒,有医生等等,可以说是渗透于社会下层的各个方面,包括民间的各个阶层。由于作者的广泛性,极大地影响了题材内容和创作风格,使得它的题材内容丰富多样,艺术风格多姿多彩。其中有较为细腻缠绵的闺情词,有慷慨激昂的边塞词,有描写世情民俗的词,也有带着很深时代色彩的咏时事词。敦煌曲子中最具艺术特色的是反映妇女思想感情和生活情态的作品。这些词的作者大多是社会中下层的妇女,因为感情真实,其作品也就纯朴清新,毫不矫情;因为感情细腻,其作品也就缠绵婉约。由于原作抄本多有误字、假借字,我们引用时作了校改。例如:
霏霏点点回塘雨,双双只只鸳鸯语。
灼灼野花香,依依金柳黄。
盈盈江上女,两两溪边舞。
皎皎绮罗光,轻轻云粉妆。
——P.3994《菩萨蛮》
这首词给人们展现的是一幅明媚的春光图。细细的春雨,成双的鸳鸯,香气袭人的野花,袅娜的柳树,盈盈的少女,翩翩的舞姿,都给春天增添了无限的生机。人的心情也有如这春光,有一种细细的暖暖的快乐。
王梵志的诗在唐代流传很广,王维、寒山、拾得、黄庭坚等都曾受他的诗的影响。但《全唐诗》里却不曾收他的诗作,宋代以后几乎没有人再提起他,他的诗后来也就绝迹了,直到敦煌卷子的发现。敦煌卷子中王梵志诗至少有三十一个写卷,三百多首。这对研究隋唐文学来说意义非常重大。
敦煌的民间杂俗诗充满民间生活气息,虽然艺术成就并不是很高,但都纯朴可爱。这些诗歌对于研究敦煌社会风俗、历史文化都有很高的价值。
《儿郎伟》是敦煌文献中特殊的一类,主要以诗歌形式表现民间风俗:驱傩风俗——古代的打鬼运动;障车风俗——婚礼中的闹剧;下女夫风俗——《游仙窟》的源头;上梁风俗——房屋建造中的娱乐活动。《儿郎伟》以六言和四言为主,间有五言和七言,有时则三、四、五、六、七言相杂。通常每首一韵到底,是一种有固定名称的俗诗。多数《儿郎伟》末尾标有“音声”二字,可知是入乐的,因些也可说是一种歌辞。从内容看,《儿郎伟》可分为三类:驱傩词,上梁文,障车文。驱傩词写岁终驱除鬼魅疫疠,上梁文写建房造窟,障车文写婚娶。这三类内容都可归为“祝愿文”。驱傩词祝愿新年平安,无病无灾;上梁文祝愿建筑成功(上梁是造屋成功的象征);障车文祝愿新郎、新娘快活和婚后发达兴旺(障车是挡迎娶之车向新郎、新娘讨赏的游戏)。在这中间,还有大量对当时政治清明、建造捐资、新郎、新娘恩惠的赞颂,因此也是一种赞颂文。这些《儿郎伟》大抵作于张议潮、张淮深及曹议金等统治敦煌时期,是确定无疑的敦煌地方文学。
孙:您在从事研究工作的过程中,以勤恳扎实的工作态度和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默默地为敦煌学做着贡献,时刻把“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作为鞭策自己的格言,您能否就学术研究问题给我们这些后来者的学习研究提些建议呢?
黄:在学术研究上,我觉得寻找切入口很重要。很多初学者都是从高处着眼做文章,这样做也可以,但是往往后劲不足,再做更多文章可能会力不从心。我比较主张进行学术研究要从微观入手,从材料入手,所以材料大小要适当,不能太小。要选择那些发展前景比较深广的材料来切入。我们以敦煌学研究为例,敦煌文献就是很好的大块材料。我们要在里面挑选一个易下手又很有研究价值的一个小块。进入敦煌材料,我们就可选变文、歌辞、王梵志诗等等。传世文献中,如汉译佛经,碑刻,安徽古代民间写本,明清杂史等等,也都是很好的研究材料。下一步就要接触原始材料。用原始材料与前人对原始材料的录文进行比勘,就能够发现许多问题。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一些敦煌写本的录文都是著名专家做的,所以大家也就很迷信这些录文。我们做学生时,郭在贻先生就让我们看原卷,在我们看的过程中,问题就显示出来了。不同的人读原卷就会有不同的结果。就是同一个人,他在不同的时间读同一篇材料,也会有不同的发现。在考证中我们会发现很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可以获得很大的收获,考证功夫也正是在阅读原卷、进行校勘过程中锻炼出来了。当然,我们从微观入手的同时,也不能没有宏观的指导,要用宏观的理论去指导自己的研究。搞我们这一行的,训诂学概论也要读,防止在实践中出现大的偏差。“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训诂的目的就是读通读懂一切古代文本。找到一种可以破解难题的方法,就是训诂研究的最佳方法。
必须一提的是学风问题。我们搞学术研究最需要的便是实事求是的精神。一个学者的成就大小,往往取决于他的学风,甘于寂寞是取得巨大成就的必要条件。青年人要脚踏实地、潜心钻研,把创造灵感与扎实基础结合起来,不可沾染道听途说、一蹴而就甚至公然抄袭的不良风气。能开自己的花,结自己的果,就是精彩。我们要自觉地养成求真务实、严谨自律、勇于创新的治学态度,在学习和研究中充分发挥自身的主动性。只有变被动为主动,你才会感到有兴趣,你才会废寝忘食地投入学习,你才能真正掌握有关的知识和技能。我觉得要学的好,必须要坐“冷板凳”;但要坐得“冷板凳”,还是要主动出击,对所学内容产生真正的兴趣。这是我对现在的青年人想说的心里话。
孙:您的建议对我们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今天能有机会面对面听您谈敦煌学研究的心得,真是受益匪浅。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孙苹,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字学专2005级研究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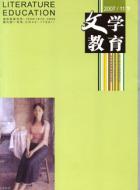
- “文学教育研究”课题开题报告会综述 / 佚名
- 读《社稷坛抒情》有感 / 周 雯
- 带着希望上路 / 黄子豪
- 美好由心 / 刘 畅
- 随笔两篇 / 曹雨菡
- 冰与茶 / 牟 茜
- 凄与悲 / 朱 丹
- 我的教学故事 / 周 莉
- 我们应该坚守什么 / 邱佩丹
- 转型期女性伦理重构分析 / 李 莉
- 如何加强中学生的养成教育 / 陈 娟
- 教学中不可忽视课文注解 / 吴 琦
- 让学生成为主动发展的人 / 杨 燕
- 语文教学应强化德育功能 / 史爱青 蒋丛英
- 文言实词词义推断七法 / 王掌珠
- 解析《黄土地》的象征艺术手法 / 周 林
- 语文教师应具备的语言品质 / 顾乐远
- 让音乐走进语文课堂 / 李艳梅
- 语文情感激发四法 / 丁 梅
- 排序题解法的由来与教学体验 / 胡 博
- 让学生享受语文之美 / 李连举 黄传超
- 语文教学如何做到效率最高化 / 唐科技
- 课堂教学应处理好五个环节 / 刘家怀
- 文言文教学三步诵读法 / 刘 希
- 古典诗歌鉴赏技巧谈 / 袁海侠
- 新理念下的语文课外阅读 / 段红霞
- 高中生快速阅读能力的研究综述 / 张 杰
- 阅读课的课程资源开发示例 / 胡群华
- 通过有效朗读培养学生语感 / 李丽萍
- 诵读是语文阅读教学的不二法宝 / 王大军
- 从戴维的成长看犹太人的家庭教育 / 田松茂
- 教师角色应科学定位 / 张小凤
- 语文教学中要加强美的教育 / 王其祥
- 对课外阅读的深度反思 / 段宗旺
- 关于语文教学的理性思考 / 黄汉云
- 近几年高考语言表达题带给教师的启示 / 王立合
- 语文教学个案分析与反思 / 张玉兰
- 语文教学要正确面对实然与应然情境 / 姜洪根
- 新诗散文化现象管见 / 赵长慧
- 散文《搭石》美感解读 / 严凯捷
- 《山居秋暝》“空”的意境 / 程永生
- 品《背影》的情意美 / 顾 军
- 析柳永《蝶恋花》对生命的哀怨 / 彭树欣
- 再论《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 / 李述河
- 《百合花》与《黎明的河边》比较赏析 / 王柚田
- 对梁生宝典型形象的再认识 / 王惠民
- 《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美点导析 / 柯贞金
- 《阿Q正传》艺术魅力解读 / 樊 洁 杨谨瑜
- 作文教学要重视两个积累 / 牟贵强
- 作文开头的四个妙招 / 束小红
- 联想和想象是展开作文思路的双翼 / 马延军
- 作文教学中的材料积累与教法初探 / 李小军
- 激活式作文教学的实施措施 / 潘武红
- 环境描写的妙用 / 邓翠红
- 活动式作文教学浅探 / 王怀艳
- 互动式作文批改教学法探析 / 孙 剑
- 创造性拓展训练在作文教学中的运用 / 宗永臣
- 让学生真情写作的四条途径 / 段丙武
- 文章写作三谈 / 阿布都艾尼·吾守尔
- 语文教学的新尝试 / 黄秋莲
- 巧用活水激活语文课堂 / 祝佩华 王全红
- 合作学习在学科教学中的运用例谈 / 林冬玲
- 高师语文教学中的德育及其实施 / 李富才
- 《狼和鹿》教学设计与评析 / 胡士秀
- 《我的老师》教学实录 / 高 旭
- 综合实践活动课可操作性探究 / 徐华君
- 课堂上教师如何修饰语言 / 胡常柏
- 新课堂结构改革带来语文教学的春天 / 张桂芳
- 语文教学中的互动关系建构 / 项 挥
- 语文教学中学生质疑能力的培养 / 余茂琴
- 提高语文课堂教学有效性方法探究 / 胡 芳
- 如何诱发学生的思维顿悟 / 王 云
- 大学语文课堂应然面貌摭谈 / 房义斌
- 语文审美教学的理性基础 / 潘家明
- 在规范与变异中探寻语言艺术之美 / 赵 燕
- 释“有朋自远方来”中的“朋”字 / 张明平
- 宋代豪放词中的侠气小议 / 王 灿
- 诗家语的句式构成形式 / 程洪远
- 周敦颐为何独爱莲 / 陈兆进
- 文言文教学中的互文修辞 / 史鸿敏
- 学生主动学习语文归因分析 / 翟国民
- 大学语文与大学人文教育研究 / 石秀华
- 浅析唐诗的浩然之气 / 毕 琳
- 苏轼词的喜剧特色 / 严玲玲
- 论大学语文教学中的美育问题 / 毛韶华
- 《红楼梦》人物语言与交际技巧试析 / 祁福雪
- 从信陵君解读边缘人物的命运 / 黄春黎
-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苦难问题 / 翟均林 叶 蓉
- 曹植生命态度对李贺的影响 / 曹丽萍
- 《呐喊·自序》中的寂寞与悲哀情结 / 罗 红
- 椭圆形 / 江少宾
- 杯子 / 黄孝阳
- 到中流击水 / 陈启文
- 鲁迅是个复杂的人 / 吴 俊
- 寻访敦煌俗文学作品研究者 / 孙 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