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06年第3期
ID: 81691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06年第3期
ID: 81691
我看语文教师应试能力的缺失
◇ 徐 江
《中国教育报》在2005年12月8日发表了吴平安先生批评我的文章——《中学语文老师惹谁了》。该文发表后,引起了不少中学语文老师情感上的共鸣。同时,该报还以图配文刊登了一幅漫画,讽刺那些对中学语文发表了一点儿批评意见的人是“躺着说话不腰疼”。如果用我解读《游褒禅山记》时所讲“表现性追问解读法”来解读这些事相之表现,即吴平安先生的艾怨与某些人的呼应其“表现性”是什么呢?我认为答案是悲哀的。
吴平安先生在文中说,一个在中学,一个在大学,“两所不同层次的学校,造成了我与徐先生在一系列问题上的根本分歧”。我认为此言差矣。不是学校的层次不同造成了我们的分歧,而是我们对语文的认识以及对语文教学现状的认识在根本上是不同的。吴先生说:“徐先生是以专业性的目光,来审视一门工具性很强的基础课的,于是诸多谬误的产生与众多中学语文老师的反对便毫不足怪了。”吴先生批评我混淆了“常规”教学与“专业”研究。其实我对中学语文界的批评,恰恰就在于语文界的“专业性眼光”太弱,把“常规”与低起点等同起来,也就是与无思维性、无创造性、无探究性等同起来。尽管语文界在大谈创造、大谈探究。下面我就以中学语文教师解读高考作文题——《留给明天》为例分析中学语文“常规”教学如何迟滞和压抑学生的思维,教师如何因自身缺少应试能力而无法为学生形成应试能力提供有效教育的问题。
先请看发表在2005年上海某语文学习杂志上某特级教师的文章——《让心灵放飞,把阳光守候》,作者在谈到《留给明天》作文题的时候说——《留给明天》是一道“零审题”作文,啥叫“零审题”?这位老师说,就是不用费气力,让思路率领材料在抒写性灵的大道上奔跑。不花费气力,哪有这么简单的试题?正是这些语文老师认为不用花费气力来分析这道试题,所以他们便作出了这样的回答——“把甲午战争的屈辱留给明天”,“把仇恨留给明天”,“把初恋的甜蜜留给明天”。天津某报还把这些答案刊在2005年7月《名师家教》版上。
如果不是白纸黑字赫然刊登在杂志上、报纸上,谁敢相信这是高三把关教师的答案!这就是现在的语文界所谓的“常规”教学在临场应试时的“常规”表现。请不要以为这是少数几个教师的作为,事实上很多很多的语文老师不会解析《留给明天》。特别是不能从试题文字的语感及内涵搞清它的题旨,不能从哲学思维上明确此类试题应对的思想原则是什么,更不能在平日的语文教学及写作训练中养成这种思维意识及能力。应试能力其实就是一种素质,语文教学现在是在搞应试教育,但大多数语文老师不能培养学生的应试能力,因为这些老师自己就没有应试能力。若把上述“不能”变“能”,就必须超越现在的语文“常规”,请语文界倾听我的批评与建议。
一、学会理性地认题
先从《留给明天》理性诠释认题谈起。语文老师本应该会这样分析,并且应该训练学生也会这样分析。但前边所述情况证明,很多人没有这种能力。
在高考作文辅导中,中学老师都习惯地称这一环节为“审题”。我反对这种提法,而将这一过程命名为“认题”。因为“审”的本意是关在房子里“问”,在考场上你向谁去“问”呀!而“认”呢?就是“识别、辨明”的意思,考生要依靠自己去辨别题的内涵,要求写什么,自己选择写什么。
下面就分析《留给明天》。“明”,日月朗照的意思。由此引申暗夜日出,天大亮,明也。从日出天亮开始为下一时段,故“明”引申为“下一”时段的意思,所以又有“明月”、“明年”之说。但作为时间概念的“明月”与作为自然景物名称的“明月”音同字同,比如“明月照天山”,所以人们不用“明月”表示时间,而称之为“下月”。“留”呢,很简单,留存之意。“给”的本意是赐予、给予,它后边有明确的承受者,前后连贯起来阅读,从语感上可以体会出那个存留行为是有一定自觉意识的。所以,“留给明天”是指行为主体在“明天”的前一时段(即“今天”)有理念、有目的、有规划地把某种东西留存到下一时段。事物从“今天”到“明天”的运动是紧密的流逝过程,因为事物的“明天”是“今天”的延续。也就是说,事物的“明天”是在“今天”的基础上发展变化的,两者间有不可斩截的因果关系。早先的阶段是此后阶段的前因条件,后阶段是此前阶段的结果。事物的“今天”蕴育着它的“明天”,“明天”承继着“今天”。所以,“今天”做什么,“今天”怎样做,都将关乎“留给明天”。“留给明天”,实质上是从“明天”着眼关注“今天”,这就是从事物“今”与“明”的流逝发展变化关系来认识事物的“今天”,把握事物的“今天”。请注意我的解释,讨论“留给明天”不是消极地看“今天”留给“明天”什么,而是从“明天”的预期来认识“今天”之所“留”,也就是“今天”行动时要想到对“明天”的影响。我们的语文老师应该教会学生这样逐字逐词从试题的内涵分析中“认”清试题的题旨,明确应对要点。我以为这种思维,这种认识,包括这种严谨的学风、方法对于高中生来说都是必要的素质性教育示范。如此认题虽然超越“常规”而有深厚的思辨意味,但对高中生来讲应该是一说就懂,并未超越他们的知识范围。如果老师有这种意识和能力并且使学生在应试辅导中得到这种思维训练,那么,不论是老师亦或学生,大家都会懂得“留给明天”要从“今”与“明”的绵延关系来作阐释,以理性的态度慎待“今天”,把握“今天”。讲出这些道理——也就是前边的试题内涵诠释——本身就是从事物流逝过程的哲学关系来论证为什么要“留给明天”,这种应试思路是一般考生所缺乏的,但这是不应该出现的现象。有了这样理性的分析,然后再联系具体情况加以佐证,两者结合在一起对试题作出应对,那么应试质量岂不是有很大提高吗?
正是因为教师不能理性地从破解试题的内涵入手,所以不知道《留给明天》题旨是指行为主体在其行动过程中,自觉地有意识地为了“下一”时段即“明天”而在“今天”创造某种条件,主动地“要”为“明天”“留”下“明天”诞生所需的东西。他们以“常规”的简单的字面意思理解试题,胡乱回答什么把“甲午战争的屈辱”留给明天,把“仇恨”留给明天,把“初恋的甜蜜”留给明天。
这些答案错在什么地方呢?
“留给明天”,我前边说过是行为主体的自觉性行为。那么,“甲午战争的屈辱”是谁留给我们的呢?是日本鬼子,他们是那一事件的主动者,我们失败了,记住这段屈辱,世世代代不忘国耻,但那不是“留”,而是“记住”。“记住”≠“留给”,这样的命题模糊了行为主体。
“把仇恨留给明天”,这位语文老师是说人们有了矛盾纠纷时要冷静,不要冲动,让时间化解分歧,但他违背了“把握今天”、“搞好今天”的宗旨。为什么不在“今天”把事情解决?这样的命题颠倒了“留给明天”的行为意义。
“把初恋的甜蜜留给明天”,本意是告诫中学生不要早恋。但是,从“今天”与“明天”的关系看,“今天”没有“初恋”,也就是“今天”在恋爱的问题上没有什么作为,那也就无所谓“留”与“不留”,包括“甜蜜”与“苦涩”。如果行为主体——中学生——理性地、自觉地要“保证”在“明天”回味到“初恋的甜蜜”,那么就必须在“今天”进行“初恋”,而且是“瞄准”对象,发挥优势,讲究策略,把初恋搞得红红火火,浪漫而刺激。总之一句话,一定要把“初恋”搞好,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给“明天”留下初恋的“甜蜜”,否则也许是终生的遗憾。老师的目的是劝导学生不要早恋,但这个命题却是要学生必须早恋,而且要搞好早恋。这是一个违背试题命意逻辑的答卷。
[##]
这就是不能对试题进行思辨诠释搞“零审题”的结果,这种“常规”的高考作文辅导是很普遍的。
二、学会在语文课文本研究中摄入有效思维成分
面对《留给明天》这道作文题,敏锐地察觉到要从“今天”到“明天”事物流逝过程的哲学角度切入,从流逝过程中的“因果关系”认识事物,这种理性应试能力,对学生来讲还要依靠正正规规的语文阅读与鉴赏这一环节来生成。这就牵涉到“今日”的语文教学是否能为学生提供构成这种思辨意识的营养成分。语文老师负有这个责任,他们应该在自己平日的语文教学中,结合具体的文本解读,首先使自己在理论认识上有长进,有提高,培养自己的思辨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为学生树立事物流逝过程中的思辨意识提供有效成分。然而从整体上讲当今的语文界没有这个能力,最可悲的是语文界没有这样超越“常规”的意识。老师自身不懂文本解读的过程本身就是自身思维意识改造和提高的过程。
传统语文课文本解读的教学内容面临着彻底的结构性调整与颠覆。许多所谓的文本解读只不过是对文本的说明,即对文本信息的重复性归结,老师自身没有深度解读能力,只能讲授学生已经懂得的东西,学生不能从老师那里摄入任何有效的构成思维能力的成分。这是当前语文课文本解读最失败的地方。比如高中课文——《〈宽容〉序言》,“常规”的解读就很无意义。该文作者——房龙是一位社会思想史研究者。这篇序文,实际上是一个寓言故事:“无知山谷”的村民被“守旧老人”掌控,他固守着一部“千年”古书所记载的信条,大家过着“宁静”的贫困生活。有些村民冒着生命危险走出了山谷,其中还有一位“漫游者”(实际上就是一位改革家)返回家乡来,他勇敢地揭露“守旧老人”在愚弄人,号召人们走出去,他被“守旧老人”判处了死刑。后来,天大旱,“无知山谷”已无法生存,村民终于推开了“守旧老人”,沿着“漫游者”的足迹,找到新的“绿色牧场”,获得了新生。房龙在序言最后说,压抑新生事物这种事情“过去”发生了,“现在”还在发生着,希望“将来”不要再发生。面对这样一篇课文,许多语文老师都是这样解读:
在这个故事中,勇敢的先驱者和守旧老人进行了殊死斗争。……他毫不畏惧。历史证明,他是对的,他终究得到了人们的尊崇。
那守旧老人奉祖宗律法为不可亵渎,……无知的人们……盲从守旧老人,用沉重的石块砸死先驱者,抛尸山脚。
但是,真理终究是不可抗拒的。一场生存危机迫使人们推翻传统秩序,走上先驱者开辟的道路,终于找到了生存的希望和幸福的家园。
在这样的“课文整体说明”之后,接下来就是进一步总结其思想意义:第一点是“贫穷、落后、反动的根源在无知、愚昧、闭塞。……历史的进步,要靠知识的进步,靠真理的发展”;第二点是“人类追求真理的努力是不可阻挡的,真理是一定要发展的。……探索者、先驱者是可敬的”。以上所引述的内容均出自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语文《教师教学用书》第二册,出版时间为2000年11月。
这就是老师阅读序文之所得。我以为读成这个样子就是无效解读。因为“真理是一定要发展的”、“先驱者是可敬的”不需要老师讲嘛!吴平安先生及其同仁或许要问,你徐老师又怎样解读呢?我是这样想的,我要引导学生发挥想象能力,把这个寓言故事中“无知山谷”村民的经历看作是一个小社会历史过程的缩影,分析它动态性生成过程所蕴涵的意义及其所昭示的运动法则。
“无知山谷”村民的经历就是一种象征。“守旧”,只能守贫守困,甚至是死亡;“变革”,就有希望,就有美好的将来。在整个事件的流程中,前边的变化——探索者走出大山又回来揭露“守旧老人”的谎言,村民被环境所迫为求生存勇敢面对“守旧老人”的阻拦而走自己的路,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后边寻找“绿色牧场”的限定条件。当然,在“绿色牧场”开始新的生活就是前边变化的结果。“前边”的“条件”生成“后边”的结果,这是事物流逝过程中永恒的规律。消逝的“过去”产生着“现在”并且延及“将来”,而“现在”每一种新情景出现——至少是决定它出现的各种条件——是可以从在它出现之前的“过去”中找到的。我们要从“无知山谷”的村民前后经历的变化中,读懂事物生成过程的原理——事物如何生成将决定它是什么,而它生成前的条件又将影响它的生成过程。“守旧老人”和“漫游者”各为“无知山谷”村民的生存发展提供了不同的生成条件,所以“无知山谷”村民在不同的条件下,他们将成为不同的村民。房龙希望残害“漫游者”的事件“将来”不要再发生,就必须在“现在”消除产生残害事件的因素,比如不能固守千年古书的遗训,而“宽容”新思想。教师如此解读《〈宽容〉序言》,那么就会在类似的文本解读过程中为使自己形成事物流逝过程的思辨意识摄入有效成分,并为学生形成这种意识提供有效指导,师生有了这种意识,那么解读“过去——现在——将来”或者说“昨天——今天——明天”的关系就是很容易的事了。因而遇到《留给明天》这样的作文题就不会犯难了。所以说,在课文解读中培养这种思辨意识,显然要比懂得“真理是一定要发展的”这种真理的价值要大。我这样以“专业性眼光”超越现在中学语文界的“常规”教学,即从事物流逝过程中的思辨意识的角度理解这篇序言,这个教学流逝过程本身也就构成了学生接受教育并生成一种独特思维品质的前因条件。这种教学使学生所得与传统教学所得会有很大的不同。
三、学会在写作理论研究中把握认识方法
教师要树立事物流逝过程思辨意识并能对学生进行这方面的培养,其途径本来是多方面的。我们不仅可以在文本解读中渐进熏陶,而且还可以通过写作理论的学习直接摄入这种理念。然而在这方面中学语文教师存在着先天的不足——他们缺少基本的写作理论涵养。无论是研究记叙文亦或是学习叙述理论,他们还不能从哲学层面搞懂“什么是叙述”以及“为什么要有叙述行为”。
许多人认为写作理论没有用。实际上,不是写作理论没有用,而是不懂有用的写作理论。也许有人会问我,就以“什么是叙述”或者“为什么要有叙述行为”为例,它与培养流逝过程思辨意识乃至回答《留给明天》这道作文题有什么关系呢?
这里不便详述有关叙事的写作理论,但我可简要地对叙述作这样的概括:所谓叙述行为,从本质方面讲就是站在“现在”的基点上,为了“将来”,用语言文字重构“过去”,使“过去”成为可阅读的材料。这里所说的“现在”不是物理的“现下的存在”时间,而是一个人文性的时段概念,包括“过去”、“将来”都是如此。事情从开始到结束的一个时段,就是事物的“现在”。“现在”之前已经结束的事情时段是“过去”,“现在”之后将继之而来的事情时段当然就是“将来”了。任何事物的“过去”、“现在”、“将来”都是连续在一起的,人们在特定的事物运动行进中,也就是它的“此在”时很难对它进行“叙述”,而且也没有多大必要。惟有完成了的东西才能使反思者与反思对象实现分离,只有分离才能实现反思。人们对完成了的东西(或已做过的行为)才更有兴趣评判它,并作出合法性辩护。所以,只有事情成为“过去”时,它的意义才会显示出来。正是事物的这个“过去”蕴涵着“现在”正在发生之事的条件,在“现在”叙述“过去”,认识事物“过去”时段的终结性,即它结束的意义乃至对“现在”产生的影响。人们根据之所以产生“现在”的这些因素,同时又结合“现在”运动的方向,就可以认识“将来”、判断“将来”。这就是“叙述”的重要意义。很显然,明白这个道理,你也就明白叙述“过去”的一件事情时要叙述什么——那就是决定或影响“现在”乃至“将来”的某些因素、条件。认清这些普遍的道理,人们才能自觉地写作。客观事物的流逝过程规律是这样的,叙述、反映事物流逝过程的写作理论必然要依从事物的运动规律。所以从这个层面掌握叙述道理,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认识事物流逝过程的思辨哲学,并非仅仅是讲写作理论,这里面包涵着一种认识事物的方法。在本质上讲,写作本身就是认识事物,解释事物。这种形而上思维元素的摄入,对于教师和学生应试能力的产生影响是巨大的,绝非翻来覆去讲什么“常规”的“叙事要有真情实感”、什么“表达方式”、什么“叙述六要素”等具体要求所能比及的。
[##]
王安石写《游褒禅山记》,就是在他们“游山”事件过去后的那一个“现在”,而且他只有在那个“现在”的时间,才能清醒地“深思”那次游山的“终结性”——体会到“尽志”、“尽力”与“慎取”、“深思”对他在那个“现在”阶段以及他后来的“将来”阶段做学问、写文章乃至治理国家大事所具有的意义。所以他的写记行为本身,就是在认识游山这一事件。王安石所留下的《游褒禅山记》,也就是用文字重构的游山事件,成为他自己的精神财富,也成为后人的精神财富。我们读《游褒禅山记》,把王安石以记的方式重温他游山经历作为一个“表现”,可以看出其独特的“表现性”——他很懂得“回头看”的哲学,也就是善于把自己已成“过去”的经验上升为思想和原则。所以,我们学这篇文章的本质意义并不仅仅在于知道《游褒禅山记》的主题思想是讲什么“志、力、物”三者的辩证关系,更重要的是能对王安石善于“回头看”的行为哲学“深思”之,“慎取”之,使我们自身聪明起来。王安石写《游褒禅山记》本身就是具体解释人们站在“现在”,为了“将来”,用语言文字重构“过去”的好例子。
当我们有了这样的叙述观时,也就意味着我们确立了一种认识观,懂得了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思维原则——事物流逝过程的思辨意识。因此当面对《留给明天》这道作文题时,也就明白试题在本质上就是讲“今天”与“明天”的关系,也就是“今天”蕴涵着“明天”,两者系着因果链。“今天”做什么、怎样做都将给明天“留下”相应的诞生条件。所以写议论文《留给明天》,考生从“今”、“明”的关系作理性阐述也就不成问题了。写叙事文《留给明天》,考生同样会更明确地知道把握什么叙述元素,把应试文章写得更好。比如说圆明园作为历史遗迹,属于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圆明园管理部门未向有关文物保护主管部门报告,“今天”擅自决定改变圆明园的遗貌结构,这种“决策”行为作为叙述元素就关系到“明天”圆明园存在的意义。
遗憾的是中学语文老师不知道叙述理论对认识事物的意义,当然这要怪罪于中学语文老师的老师,即那些大学教授有教无学,没有讲清这些写作道理。
以上我从高考作文考前辅导、平时语文课文本解读乃至写作理论学习三个方面,并且以天津市高考作文题《留给明天》应试为例对一些语文教师应试素质现状进行了分析,很显然在这三个重要方面许多中学语文老师都存在着巨大缺陷。我想,大家在解读“留给明天”的过程中,应该清醒地认识教师“今日”之所教与学生“明日”之所成有着紧密的关系,也就是说知道“留给明天”应该“留”什么的重要性。如果我们的中学老师不提高自身的素质条件,无力突破目前“常规”的“无效”的教学窘境,中学语文教育留给“明天”的将是什么还需再说出来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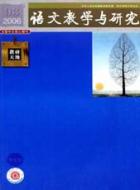
- 动静结合的妙趣 / 崔兰英
- 如何记好语文课堂笔记 / 张 靖
- 把握课堂教学的多与少 / 陈红忠
-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 张 波
- 语文教学的心理位置互换 / 马乃信
- 探究高中语文教学盲点 / 高松达
- 善待学生的“挑刺” / 徐宏寿
- 让私塾模式重现语文课堂 / 薛晓伟
- 语文备考中作文目标的设定 / 马新民
- 话题作文训练案例一则 / 陈胜林
- 《邹忌讽齐王纳谏》教学思路 / 左松良
- “唐诗中的音乐描写”专题教学设计 / 沈中尧
- 否定副词“没”和“不” / 张时阳
- 语言分析与文本解读 / 邹兆文 胡志强
- 鲁迅语言的变脸艺术 / 袁德俊
- 中考语文开卷考试未必有益 / 曹红勇
- 从近几年高考看文言文翻译 / 周同一
- 高考文学作品阅读题的应试对策 / 狄永兴 金卫华
- 《木兰诗》中木兰承载的文化意蕴 / 邬永辉
- 《庄周买水》假拟构思解析 / 赵泽学
- 《怀疑与学问》中的“怀疑” / 陈恒军
- 试析《岳阳楼记》的和谐美 / 邓吉斌
- 《故都的秋》主题探究 / 周美珍
- 《荷花淀》的传统文化内涵 / 张云飞
- 新课程写作教学的实践探索 / 董 琳
- 作文情感的引发与培养 / 徐淮滋
- 旅游资源与作文教学 / 曾蓉蓉
- 写作教学中的角色意识 / 柯 极
- 寻找让思考立体展开的支撑点 / 金健人
- 考场作文如何多角度构思 / 洪 峻
- 想象在阅读中的作用 / 刘 丽
- 把握好阅读教学的度 / 高秀兰
- 现代文阅读归纳要点的步骤与方法 / 陈帮明
- 论文学作品主题理解的差异性 / 李旭东
- 文本的意义和限度 / 邵国义
- 语文高考备考策略 / 赵艺阳
- 联想和想象能力培养例说 / 刘国成
- 篇章结构的重复技巧 / 陈堂君
- 诗歌教学不一定要激情燃烧 / 徐国年
- 语文合作学习中的不良局面 / 卜廷才
- 新课标下语文教师的三大尴尬 / 林振远
- 语文教师课堂失位现象剖析 / 陈海光
- 语文教学中的花架子描述 / 刘东平
- 我看语文教师应试能力的缺失 / 徐 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