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06年第8期
ID: 81460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06年第8期
ID: 81460
修辞的创造观
◇ 朱 军
修辞本质问题,是修辞学最基本最重要的理论问题。综观修辞学史上各种观点,因分析的角度不同,差别很大,有“美辞观”或“文辞修饰加工说”、“就意修辞观”或“语辞调整说”、“表达效果观”等,各有各的道理。随着修辞学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人们对修辞本质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同义形式选择说”最具影响,似乎更接近于修辞的本质。但上述各家说法都不能完全概括修辞的本质,他们都忽视了语言同义形式或同义手段的创造在修辞中的重大作用。修辞现象的不断丰富和语言的不断发展,都离不开人们的创造性劳动。本文在评析修辞学史上各家观点的基础上,提出和论证我们对于修辞本质的看法。
一、历史上的修辞观
在中国,“修辞”二字连用,最早见于《易经》中的“修辞立其诚”,这里的“修辞”和今天说的“修辞”并不完全一致。最早以“修辞学”命名,全面系统地论述修辞的是王易的《修辞学》。在这以后,修辞学发展很快,修辞学的研究范围也逐步扩大,并出现了几次繁荣。对于修辞的认识,各个时期也不尽相同,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美辞观
这种观点在我国古代修辞学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说文解字》九篇上“彡部”说“修,饰也。从彡,攸声”。段玉裁注道:“修之从彡者,洒刷之也,藻绘之也”。“修”作“修饰”解,“辞”是“文辞”,“修辞”就是修饰文辞。修辞被看作是一种手段和技术,而“修辞学”仅仅就是研究修辞格。在西方的古典主义修辞学时期,情况也差不多。这种观点在我国二十世纪初修辞学第一次繁荣时期非常流行,王易的《修辞学》、陈介白的《新著修辞学》、郭步陶的《实用修辞学》、章衣萍的《修辞学讲话》等都持这种观点。他们都把修辞看作是一种技术或艺术,是加工、修饰语言、文字的技术或艺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后张弓的《现代汉语修辞学》、朱星的《语言学概论》和张斌的《现代汉语》仍持这种观点。美辞观基本上是把修辞看作艺术修辞,没有把规范修辞放到应有的位置,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
(二)适切观
针对美辞观存在的缺陷,一些修辞学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这其中尤以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提出的“修辞以适合题旨情境为第一义”为代表,[1]修辞学界称之为“就意修辞观”或“语辞调整说”,也叫“适切观”。《辞海·语言文字分册》也认为:“修辞,依据题旨情境来恰当地表现写说者所要表达内容的一种活动。”“适切观”是对美辞观的继承和发展,因而比美辞观更全面、更完整。这种修辞思想早在公元前几世纪就有了萌芽;我国春秋时期的孔子就说过“辞达而已矣”。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也说过:“风格的两个要点:一是清晰,二是适当。”[2]
(三)表达效果观
在实际的修辞活动中,很多修辞现象并不是适切观所能概括的,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表达效果观”。顾名思义,这种修辞观重视修辞的表达效果。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修辞是运用恰当的表达手段,为适应特定的情境,以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规律。”[3]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和王德春主编的《修辞学词典》有类似看法。表达效果观考虑较为全面,但对好的表达效果的产生来源和过程缺乏有力的论证,且对怎样取得好的表达效果,各家说法莫衷一是。
(四)同义手段选择说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同义形式选择说”最具影响,同义手段选择说是随着一些修辞学家对作家文稿的原稿和修改稿的对比研究的重视而兴起的。什么叫同义手段?王希杰认为:“同义手段指某一零度形式同它的一切偏离形式(包括正偏离或负偏离,显偏离和潜偏离)的总和,它们之间的关系模式、关系矩阵、关系网络。”[4]张弓在《现代汉语修辞学》中曾涉及过同义形式的选择问题,但并不是从修辞本质的角度提出来的。张志公先生在《修辞学习》的创刊号上发表了《修辞是一个选择过程》,可以说是开了同义手段说的先河。吕叔湘《我对“修辞”的看法》也持类似看法。同义手段选择说将修辞问题形式化、模式化,使之更具有操作性,这是以往的修辞学理论所没有的。
上述修辞观都是从静态、共时的角度看待修辞,忽略了修辞活动动态、变化的一面,无疑是不全面的。我们认为修辞活动不仅是同义手段的选择,也是同义手段的创造。“同义手段选择”观,前人已有详细的论述和论证,本文主要论证“同义手段的创造”在修辞活动中的作用。因为修辞活动不仅是语言活动,和文学创作也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将从语言范畴和文学范畴两个角度阐述我们的观点。
二、语言范畴的“同义手段创造”
语言交际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不仅交际双方——表达者和接受者之间有矛盾,而且交际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同样的意义,可以用不同的形式表达,同样的语言形式,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可以表达不同的意思。修辞活动存在于语言交际活动之中,同样充满着矛盾。表达者在许多语言材料中选择,既有对固有的同义关系的选择;又有对临时形成的同义关系的选择。许多语言单位在语言体系中不是同义关系,甚至是反义关系,但在言语表达中可构成同义关系,这种临时形成的同义关系,就不是同义手段选择,而是同义手段的创造。陈光磊在《修辞学研究什么》中曾说过:“在修辞过程中,炼字、删改等不见得只是对现行的‘平行的同义结构’作选择,也完全可以另施炉锤,进行创造,‘修辞学不但要指导人们从平行的同义结构中选择最恰当的一种表达自己所表达的思想内容,更重要是指导人们运用修辞规律去创造新的表达手段’。”[5]他认识到“创造”在修辞活动中的作用,但还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我们再从语言系统的“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的角度来认识修辞中同义手段的创造。同一级语言单位的同义手段构成一个聚合体,表达者在修辞过程中首先要在聚合体中选择,再将这些语言单位进行组合,形成新的组合关系;即使是单独的词、单独的句子、单独的段落、单独的篇章,不直接和其它语言单位组合,它们也和整个语境形成一种组合关系。这种组合关系形成后又和其它同级的同义语言单位形成一个更大的聚合体。所以说在修辞活动中不仅存在着聚合关系,也存在着组合关系。而这种组合关系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依赖表达者的创造。以往的修辞观只意识到聚合关系的选择,而忽视了修辞活动中组合关系的创造,这是它们的局限。在修辞活动中,处处体现着组合关系的创造。同一个意思,既可以用这种组合关系表示,又可以用那种组合关系表示,表达者可以从聚合体中选择已有的一种组合关系,这就是同义手段的选择;如果表达者对已有的组合关系不满意,他就要去创造新的组合关系,这就是同义手段的创造。修辞贵在新、奇、变,从这个角度说,同义手段的创造显得尤为重要。
在语言的实际运用中,同义手段的创造也是无处不在。语言中的“语流义变”现象就是语义在语流中失去原来意义,变成另外一种意思。这种现象似乎是表达者无意为之,实际上是刻意创造的结果。如我们刻画热恋中的男女,要表达女方称赞男方的意思,可以从“你真好”这个同义聚合体中选择,也可以从“你真坏”这个同义聚合体中选择,配合男女恋爱特别的环境,形成一个新的组合关系,和“你真好”聚合体形成同义手段。本是反义关系,在这里成为同义手段,这就是表达者同义手段的创造。一些表达者还常常创造新词,或改变词的用法,以取得好的表达效果。如古人作诗非常讲究字眼(也就是今天说的炼字),字眼的创造性很强,如“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之“入”、“归”、“红杏枝头春意闹”之“闹”,“云破月来花弄影”之“弄”,这些词一般情况不这样使用,但在这里临时改变一下用法,形成新的组合关系,境界全出,这也是同义手段的创造;现代诗歌创作中语言的“陌生化”现象也是语言同义手段的创造。
[##]
正是由于修辞活动中时时处处存在同义手段的创造,所以不断有新的同义手段产生,辞格的发展就说明了这一点。现代汉语中,自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提出了三十八个修辞格以来,又增添了三十多个新格,这些修辞格有的是现代汉语新创,有的是古已有之,而为现代汉语继承,但直到近年才被人正式发现,如“舛互”、“列锦”、“断取”、“歧疑”等,而且还在不停地创造新的辞格,这些“新格”的出现就是同义手段的创造。
创造同义手段不同于生造语言,因为固有的语言手段无法满足表达的需要,就必须创造新的语言手段。对于固有的语言手段来说,有突破规范之处,但依赖具体的言语环境能够被人理解,更重要的是能取得好的表达效果。但不管是创造词语也好、创造句子也好,还是独创一种风格也好,必须把握一个度。作文不可“因辞徇意”,而应“以辞达意”。孟子所谓“……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朱熹所谓“韩子为文,虽以力去陈言为务,而又必以文从字顺各识其职为贵”,说的都是这个道理。
三、文学范畴的“同义手段创造”
中国古代的文论家都很重视同义手段的创造,强调语言表达要创新。王充主张写文章“不类前人”,要敢于创新,要有自己独特的个性,他不仅反对在思想内容上模拟他人,在语言表达形式上也反对模拟,要“各以所尊,自为佳好”。[6]相似的论述还有很多:陆机说“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7]李德裕强调“文章譬诸日月,虽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此所以为灵物也”。[8]陈望龄的《徐文长三集序》说:“文也者,至变者也。古之为文者,各极其才尽其变。故人有一家之业,代有一代之制,其洼隆可手模,而青黄可目辩,古不授今,今不蹈古,要以屡迁而日新,常用而不可敝”。[9]李腾芳的《文字法三十五则》说:“凡句必须独造,不可用古人现句。古今文章大家必能造句,晓得造句法然后可以行意。孔子曰:‘辞达而已矣’,不能造句,则必不能达也”。[10]叶燮的《原诗》也说:“今人偶用一字,必曰本之昔人,昔人又推而上之,必有作始之人。彼作始之人,复何所本乎?不过揆之理、事、情,切而可,通而无?,斯用之矣,昔人可创之于前,我独不可创于后乎?古之人有何之者,文则司马迁,诗则韩愈是也”。[11]李渔的《窥词管见》还说:“文字莫不贵新,而词为尤甚……同是一语,人人如此说,我之说法独异,或人正我反,人直我曲,或隐?其词以出之,或颠倒字句而出之,为法不一”。[12]可见文论家们对语言的创新一直都是非常重视和提倡的。
文论家们还给予善于变化、创新的作家及一些杰作、“胜”语较高评价。钟嵘的《诗品序》说:“……‘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13]刘大??的《论文偶记》也说:“文贵变。《易》曰:‘虎变文炳,豹变文蔚’。又曰:‘物相杂,故曰文’。故文者,变之谓也。一集之中篇篇变,一篇之中段段变,一段之中句句变,神变、气变、境变、音节变、字句变,唯昌黎能之”。[14]刘勰的《文化雕龙·辨骚篇》曾说《离骚》异乎经书的部分是“望今制奇”,是新变,所以超过诗经。[15]刘熙载的《艺概·文概》则认为文章贵在精能变化,并认为韩愈的《送董邵南游河北序》是变化中的极品。[16]
文学创作中既有有意为之的创造,又有情与物遇自然而发的创造,后一种创造需要创作者具有高超的独创能力,也是古代文论家特别推崇的,他们提倡要有“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境界。王充的《论衡·超奇》说:“心思为谋,集札为文,情见于辞,意验于言”。[17]挚虞的《文章流别论》说:“古之作诗者,发于情,止于礼义,情之发,因辞以形之,礼义之旨,须事以明之”。[18]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特别推崇以境界见长的作品,他说:“‘明月照积雪’、‘大江流日夜’、‘日无悬明月’、‘长河落日圆’,此种境界,可谓万古壮观。求之于词,唯纳兰容若塞上之作,如《长相思》之‘夜深千帐灯’,《如梦令》之‘万帐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差近之”。他对“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也极为赞赏,称其为“元曲唯一接近盛唐诗者”。[19]这种看法是非常有道理的。相反,对模拟他人之作,评价不高。姜夔的《白石道人诗说》认为:“一家之语,自有一家之风味。如乐之二十四调,各有韵声,乃是归宿处。模仿者语虽似之,韵则无矣。”[20]这种评价是很中肯的,在文学史上得到验证:李清照的《声声慢》一开始以“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十四个叠字形容她孤寂无依的处境,很有独创性,后多有模仿之作,但往往意存,境界相去甚远。洪迈的《容斋续笔》也曾举例说:“左太冲《咏史诗》曰:‘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白乐天《读古》一篇全用之曰:‘雨露长纤草,山苗高入云,风雪折劲木,涧松催为薪。凡催此何意,雨长彼何因。百尺涧底死,寸茎山上春’。语意皆出自左思,但含蓄顿挫不逮也。”[21]
不同的文体也可以看作同义手段,文学史上各种新文体的出现亦离不开文学家们同义手段的创造。屈原在学习楚声歌曲的基础上创造了“新”诗体——骚体;司马迁“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开创纪传文学;沈约把四声运用到诗歌的声律上,提出“四声八病”之说,创立“永明体”,奠定了律诗的基础……
各种语体也可以看作是同义手段,各种语体都有自己的使用范围,但有时变用一下,能达到意外的使用效果。钟嗣成说:“维杨诸公俱作《高祖还乡》套数,惟公(睢景臣)[哨遍]制作新奇,诸公皆出其下”。[22] [哨遍]《高祖还乡》的新奇之处在于在《高祖还乡》这个严肃的主题下用一些民间口头俚言俗语,达到绝妙的讽刺效果。从语言风格的角度看,是用语体的变用达到寓庄于谐的修辞效果。
作家独特文风的形成更是创新、求变的结果。在中国文学史上,许多文学家就非常重视语言表达的创新,给后人很好的示范。杜甫是“语不惊人死不休”,韩愈是“唯陈言之务去”;贾岛是“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李翱是“创意造言,皆不相师”。所以谢灵运诗能“《易》辞《庄》语,无不为用,裁剪之妙,古今为宗”;李白能继承陈子昂的革新精神,学习楚辞和乐府,创造了独特的浪漫主义诗风;杜甫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元稹语),号为诗史;韩愈能“文起八代之衰”,“唐诗之一大变”,“诗无一字犹人,如太华削成,不可攀跻”;[23]苏轼能创立豪放词派,极大地扩大了词的表达领域……
创作手法的“推陈出新”和“以故为新”也是同义手段的创造,也就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杜甫是个推陈出新的高手,他的《戏为六绝句》说:“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才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未及前贤更勿疑,?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24]皎然《诗式》也主张继承和创新相结合:“作者须知复变之道。反古曰复,不变曰滞。若惟复不变,则陷于相似之格,其状如驽骥同厩,非造父不能辨。能知复变之手,亦诗人之造父也”。[25]史绳祖在《学斋占毕》中举例:“东坡《泗州僧伽塔诗》:‘耕田欲雨艺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此乃隐括刘禹锡《何卜赋》中语:‘同涉于川,其时在风,沿者之吉,诉者之凶。同?于野,其时在泽,伊种之利,乃穆之厄’。坡以一联十四字而包尽刘四对三十二字之义,盖夺目换骨之妙也。至如《前赤壁赋》尾段一节,自‘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至‘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却只是用李白‘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难’一联,十六字演成七十九字,愈奇妙也。”[26]这里说的是篇章结构同义手段的创造。句式同义手段的创造也很常见,杨万里的《诚斋诗话》就有记述:“庾信《月诗》云:‘渡河光不湿’;杜云:‘入河蟾不没’;唐人云:‘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坡云:‘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尽日凉’;杜《梦李白》云:‘落日满屋梁,犹疑照颜色’;山谷《簟诗》云:‘落日映江波,依稀比颜色’;退之云:‘如何连晓语,只是说家乡’;吕居仁云:‘如何今夜雨,只是滴巴蕉’,此皆用古人句律,而不用其句意,以故为新,夺胎换骨。”[27]可见继承基础上的“创造”同样有非凡的效果。
[##]
四、修辞的“创造”观及其作用
我们从语言学范畴和文学范畴两个角度论证了修辞活动中处处有创造、处处需要创造。可以说,没有创造,就没有修辞。归结起来,我们认为,修辞就是对同义手段的选择和创造、以求最好的表达效果的活动,简称“修辞的‘创造’观”。修辞的“创造”观的提出,不仅在修辞学理论上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我们认识语言的变化、发展,树立正确的语言发展观,以及指导我们的语言实践都有重要意义。
如前所述,“修辞的本质”问题是修辞学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以往的理论都不能全面地概括修辞的本质,这势必影响修辞学的发展。“同义形式选择说”在理论上较以往的说法有很大的进步,但仍旧不完备,因为它只重视语言体系中的聚合关系的作用,而忽略语言体系中的组合关系的作用。组合关系是语言单位先后的排列关系,排列有一定的规则,语言单位在组合中产生特定的意思和效果,表达者要利用这种意思和效果,甚至是打破规则创造新的组合以获得这种特定意思和效果,语言的创造性也更多地集中在组合的创造上。修辞的“创造”观考虑了语言组合关系在修辞中的作用,在理论上更为完备,这对于拓展修辞学的研究领域,促进修辞学的发展,必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认识到修辞的“创造”观,才能树立正确的语言发展观。语言的变化、发展,有社会的因素,因为社会在变化、发展,语言必须不断发展才能满足交际的需要;但语言的发展不完全是被动的,也有其自身的发展机制,有语言使用者本身的主观能动作用。语言的各组成部分,各种表达手段的发展并不平衡。某一部分优先发展,打破平衡,会促进语言整体的发展。语言中的创造就是要打破平衡,同时又促进语言的发展。
认识到创造性是修辞的本质属性,对于指导我们的语言实践也有重要意义。一方面,语言的使用要符合规范,合逻辑;另一方面又要打破惯性思维,运用超常思维、发散性思维,创造一些新奇的语言形式和表达手段,使语言更具变化和美感。在某种程度上,语言已不仅仅是工具,还是精神享受对象。语言的创造,能使人产生新奇感、愉悦感和美感,有很重要的审美效应。
注 释:
[1]《修辞学发凡》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P11。
[2]《修辞学》三联书社,1991年。P150。
[3]《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P394。
[4]《修辞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P259。
[5]《修辞学研究》第1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
[6]《中国文学史》一,游国恩等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P176。
[7][8][24][25]《汉语修辞学史纲》易蒲、李金苓主编,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分别见P126、P192、P701、P202。
[9][10][11][12][13][14][16][17][18][20][21][23][26][27]《古汉语资料修辞资料汇编》郑奠、谭全基,商务印书馆,1980年。分别见P383、P400、P610、P662、P79、P526、P585、P42、P65、P279、P186、P607、P193、P270。
[15]《文心雕龙注释》周振甫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
[19]《人间词话》黄霖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22]《中国文学史》三,游国恩等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P3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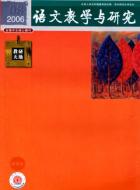
- 节令诗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征 / 屈万青
- 高中“小语文”整体化教读初探 / 孙哲平
- 当代文学与中学语文教学 / 高重远
- 在文化平台上进行古诗文教学 / 张琴儿
- 把幽默引进语文课堂 / 黄宝雄
- 走出答题误 / 陈学富
- 关于高考作文积累素材的思考 / 龙泽润
- 近年中考作文题例析 / 朱升权 连万斌
- 试论语文课堂的教学语言 / 龙珍华
- 关于“象”和“像”的使用问题 / 李学军
- 临时同义词的生成特点 / 郑安君
- 《纸船》教学案例 / 王晓冰
- 第三只眼睛看语文课改 / 程少堂
- 语言运用也是一种习惯 / 李通海
- 整合语文教学资源的基本技法 / 刘文松
- 文学能力与话题作文 / 杨锦全
- 入境·生情·悟道 / 吕 歌
- 在阅读中发展直觉思维 / 朱海燕
- 怎样解读古典诗词的主旨 / 袁红玉 汤道霞
- 解题是导读深入的前提 / 秦新丽
- 为个性化阅读提供路标 / 吴振华
- 修辞的创造观 / 朱 军
- 丑小鸭是怎样变成白天鹅的 / 陈晓涛
- 从两个教学片断谈合作学习 / 张启和
- 语文课堂教学用时摭议 / 谢英杰
- 关于问题的三个问题 / 蔡伟胜
- 《〈宽容〉序言》中的四个“幸福” / 余晓明 徐 琳
- 从修辞的角度解读《归去来兮辞》 / 王 力
- 由《墙上的斑点》认识伍尔夫 / 陈 溪
- 《读〈伊索寓言〉》教学新设想 / 张家胜
- 《故都的秋》意象新解 / 林大岳
- 《藤野先生》备课补遗 / 李 芝
- 《湘夫人》中的爱情描写 / 陈理萍
- 《陌上桑》的虚构艺术 / 王 锐
- 抽象化文本与具体化教学 / 李胜志
- 人本作文的四维解读 / 王启彦 瞿红安
- 开展快乐作文的几点体会 / 史显坤
- 影视文化与记叙文写作 / 彭爱华
- 作文写作的创新与转型 / 唐祥明
- 用好文本这个作文素材库 / 赵胜启
- 圆形思维的整一与激活形式 / 夏 玲
- 作文教学要尊重学生的主体性 / 王春红
- 作文竞赛与教育创新 / 谭根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