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06年第9期
ID: 81427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06年第9期
ID: 81427
沈从文《边城》细读
◇ 金 理
沈从文出生于湖南凤凰县,地处湘、川、鄂、黔四省交界,又是苗、侗、土家等少数民族聚居之所。1923年,他带着湘西明秀山水铸就的自然灵性和少数民族血统中积淀的沉痛隐忧的独特气质,只身来到北京。手上没有文凭,囊中空空如洗,生活的困窘以及都市人自以为是的优越感,无不让沈从文体会到一种深刻的心理压力和被排斥感。这一心理压力和被排斥感一方面促使他对都市人的性情、趣味进行猛烈抨击,另一方面又是一种反作用,越是被排斥,越是想进入,他非常羡慕、渴望进入现代社会和文坛主流。城市对他的轻慢更激起他向别处寻找精神支柱的冲动,而正是在湘西的民间天地中,他发现了迥然有异而又足以与都市价值标准相抗衡的精神支柱。“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他对一切事照例十分认真,似乎太认真了,这认真处某一时就不免成为‘傻头傻脑’”(《<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这样执拗的身份认同,主要正是源于以乡土对抗都市的隐秘心理。从这一心理动因出发,他在创作中着力渲染湘西农村的血性、野蛮,来刺激、冲击城里人生命力的萎缩和人性的伪饰。
1923年,这个在特殊的地理、历史和现实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人,闯荡进了北京。第二年,沈从文开始发表作品,1927年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蜜柑》。1932年,时在青岛大学教书的沈从文利用暑假写出了《从文自传》,这一年他刚过三十岁。这部作品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本身即是优秀的散文,更重要的是它具有超越文学的意义:借助自传的写作,沈从文从过去的经验中重新“发现”了使自我区别于他人的特别因素,通过对纷繁经验的重新组织和叙述,这个自我的形成和特质就变得显豁和明朗起来。《从文自传》沿途追索自己生命的来历,完成自我的确认;而这样一个自我的确立,为已经可以触摸到的未来作好了准备。此前沈从文写作十年,虽然发表了数量庞大的作品,其中也有《柏子》、《萧萧》、《丈夫》等优秀的短篇小说,但就整体而言,他的创作仍处在探索阶段。但《从文自传》的完成,使他达到了另一个境界。确立了自我之后,最能代表个人特色的作品就呼之欲出了。
为了将《边城》置放在沈从文整体的文学背景中加以研读,我们先从他的两篇小说谈起。
《柏子》的故事很简单:年轻的水手,行船了一段时间,终于泊到一处码头,“日里爬桅子唱歌,不知疲倦;到夜来,还依然不知道疲倦”,走过跳板上岸,“目的是河街小楼红红的灯光,灯光下有使柏子心开一朵花的东西存在”,而灯光下的妇人也正翘首以待,于是,“他们把自己沉浸在这欢乐空气中,忘了世界也忘了自己的过去与未来”……沈从文在这里的用笔是恣肆的,恰如故事中人物的粗犷热辣。柏子和妇人不像城里人在表达感情时曲折细腻,“粗卤得同一只小公牛一样”;但是再看下面的对话与念想,你就能在粗犷欢会的背后窥见人性的单纯与真率:
“柏子吸了一口烟,又说,‘我问你,昨日有人来?’
‘来你妈!别人早就等你,我算到日子,我还算到你这尸……’
‘老子若是真在青浪滩上泡坏了,你才乐!’
‘是,我才乐!’妇人说着便稍稍生了气。
柏子是正要妇人生气才欢喜的。”
“妇人的笑,妇人的动,也死死的像蚂蟥一样钉在心上。这就够了。他的所得抵得过一个月的一切劳苦,抵得过船只来去路上的风雨太阳……”
一朝欢娱竟然要等上一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劳苦”与“风雨太阳”,那么这份欢娱的背后未见得不隐伏着忧痛;然而反过来想,正是在这样忧痛隐伏中的爱恋与相思,才更见出真率与淳朴。小说一开篇渲染热闹的劳动与歌唱场面,同水手与妇人的欢爱一样,这正是他们在“劳苦”与“风雨太阳”的桎梏下生命力的蒸腾。
柏子们“忘了世界也忘了自己的过去与未来”、“也不知道可怜自己”,从表面上看可以视作对自我生存方式缺乏反省的麻木;也可以说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加鞭挞的封建残余。然而重要的是沈从文没有就此滑入精神悲剧等待启蒙的模式,他没有高高在上持道德批判与理性启蒙的立场,他了解这种生存方式的委屈与困难,他也看到其中人性的温厚与美善。所以沈从文更能体贴乡土中国日常生活中的款曲委婉。《柏子》中有一处交待:“落着雨,刮着风”,“雨声风声”,“江波吼哮”,“船只纵互相牵连互相依靠,也簸动不止”,然而对于船上的人来说,“这一种情景是常有的。坐船人对此决不奇怪,不欢喜,不厌恶,因为凡是在船上生活,这些平常人的爱憎便不及在心上滋生了”。沈从文在为柏子这样的人物画像时,其实正和他笔下的人物一处生息着,他自己也是“坐船人”,“在船上生活”着。
沈从文在展示“乡下人”精神特征时的寄托,在与《八骏图》这类小说的并置中,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显豁。所谓“八骏”,是指客居青岛大学的达士先生连同他周围的七位教授。小说通过达士先生的视角,揭开七位教授虚假、萎靡、孱弱、阴暗的面貌:看似家庭美满的教授在“蚊帐里挂一幅半****的香烟广告美女画”,自称“老人”的教授在心中晃着“苗条圆熟的女孩子影子”……最妙的是结尾处,达士先生身受海滩上神秘女子的魅惑,向未婚妻撒谎推迟归期,显然达士先生自己也在小说叙事者解剖的范围内。全篇精巧而锐利的讽刺,直指现代文明与城市文化培育出的精神贵族、知识精英,他们被社会与道德紧紧捆绑,自然本性被压制,终于人格分裂。两相比照,如柏子一般在湘西世界的光影声色中自然舒展的人性状态,当然显得活泼、自由、健康而明朗。小说最后写:“自命为医治人类灵魂的医生,的确已害了一点儿很蹊跷的病。这病离开海,不易痊愈的,应当用海来治疗。”海的本质是沈从文素来钟爱的水,它与自然、人性本源相联系,“被阉割过的寺宦观念”,“应当用海来治疗”。在这一意义上,苏雪林的评点贴近沈从文的创作理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轻起来……”。(《沈从文论》)
让我们回到1933年,随着生活的日趋安稳和事业的起步,沈从文逐渐被都市和主流文化所接纳。先前创作中时或出现的芜杂和矫情慢慢滤去,沈从文不仅找到了一份独特的情感天地,更重要的,他拥有了表达这份情感的独特方式,他开始把饱满而丰富的情感压缩到文字后面,用朴素、澄澈的叙事来表达他对湘西生活的复杂态度。于是,《边城》诞生了——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时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夏天则晒晾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裤,可以作为人家所在的旗帜。秋冬来时,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无不朗然入目。黄泥的墙,乌黑的瓦,位置则永远那么妥贴,且与四围环境极其调和,使人迎面得到的印象,非常愉快。一个对于诗歌图画稍有兴味的旅客,在这小河中,蜷伏于一只小船上,作三十天的旅行,必不至于感到厌烦,正因为处处有奇迹,自然的大胆处与精巧处,无一处不使人神往倾心。”
这完全是一个桃源仙境般的世界。山水秀美,风俗淳朴,无论是农民、水手还是妓女,无不重义轻利,守信自约。沈从文描绘的这一民间世界,将藏污纳垢的混浊澄清掉,首先贡献给读者的,是一颗玲珑剔透的美玉,它钟灵毓秀,折射出自然熏陶下的人情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谐和)、人性美(人自身的美好)。接下来是翠翠的出场:
[##]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故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故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
翠翠不是五四以来被人道主义的概念以及现代化的教育体制所培育、规训出来的人物,她完完全全是“自然之子”:“在风日里长养着”,是山水中的活物,与天地浑然一体。“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她的美丽、善良与天真,就是大自然清辉灵性的投射。大自然给予她全部生命,那种丰满、质朴、圆润的风致,本就得自风、日、青山绿水的滋养,而这个生命体本身又是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俨然如一只小兽物”般“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这种与山水融会一体的气质,与自然进行生生不息的回环、交流、映照的本能,使得翠翠成为一种生命的现象。当沈从文在现实中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各种要求已然得到了满足,世俗的功名、美满的婚姻、安稳的生活一一实现,内心却还是存有一个超越世俗的渴求,已经步入了现代文明的常轨,心底深处却渴求着应和那份与自然相协的律动。《边城》的创作是沈从文在追寻心中的一个梦,翠翠就是他的这个梦,梦中分明渗透着《从文自传》里那个在大自然万物百汇、光影声色中活脱跳动的少年精灵的影子。而在读者心目中,翠翠这个形象完全成为典范自然人性、寄托超现实的美好理想的化身,那浑身发散的健康、美丽、庄严,如徐徐清风,沁入被社会、文明的各种成规所压抑的现代人的心脾。
然而这个田园牧歌的世界中,也逐渐显现出不谐和的因素。比如翠翠的故事:码头船总顺顺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同时爱上了翠翠,结果一个身亡,一个出走,翠翠的外祖父也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故世,留下翠翠一人等待那个“也许永远不回来,也许‘明天’回来”的二老。整部小说笼罩着一种无可奈何的命运感,每个人都淳朴、诚实,爱得坚贞,用心良苦,悲剧发生的缘由似乎是一连串的误解和人事的弄巧成拙,作者大概倾向于把根源归咎于无法左右的天意,仿佛古希腊人性悲剧中人与不可抗拒的命运之间的冲突。沈从文的用意,是构筑这样一个田园牧歌的世界来供奉美好而自然的人性,反抗现实秩序对人的压抑,与都市文化的贫弱“失血”形成对比。
1934年在写作《边城》过程中,沈从文因探望病危的母亲离京回乡,非常敏锐地发现以往情景正在流逝:“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长河>题记》)当他用“常”与“变”的眼光去打量湘西世界时,态度的复杂就显现出来了,一方面极力挽留桃源仙境般的神话,另一方面又意识到湘西世界日趋没落无法挽回的历史命运。正如小说末尾那座“与茶峒风水有关系”的白塔在老祖父故世的风雨夜晚轰然圮坍,预示着在现代化不可抵御的展开情境中,田园牧歌神话的必然终结。所以,我们应该注意到沈从文在纯美极境中表达的“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以及潜藏在那种无可挽回的悲剧背后沉静深远的无言追悼。正如汪曾祺讲的:“《边城》所写的那种生活确实存在过,但到《边城》写作时(1933-1934)已经几乎不复存在。《边城》是一个怀旧的作品,一种带着痛惜情绪的怀旧。《边城》是一个温暖的作品,但是后面隐伏着作者的很深的悲剧感。可以说《边城》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边城》的生活是真实的,同时又是理想化了的,这是一种理想化了的现实。为什么要浪漫主义,为什么要理想化?因为想留驻一点美好的,永恒的东西,让它常在,并且常新,以利于后人。”(《又读<边城>》)沈从文正是用小说中的美好世界与现实生活的黑暗丑陋相比照,提醒人们去“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并且给予“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一种勇气同信心”(《<边城>题记》)。
30年代的中国文学进入了无名状态。大一统的时代主题已趋瓦解,文学创作道路出现明显的分途,在坚持启蒙以及一部分更加激进的作家走左翼的道路之外,还有一大批很有才华的作家开创了新的立场和创作道路,他们将视野转向普通的民间社会,但不像启蒙主义无意间会遮蔽民间世界的真相,也不是左翼文学那样以意识形态来图解民众生活,他们探讨民间承受苦难的能力,并且努力把社会底层的生活真相不带有知识分子目的地展示出来,在叙事、语言、题材、观念上都焕然一新。民间立场和民间审美观念的出现,为新文学注入了新鲜血液,改变了原来偏重于知识分子自身题材的“由启蒙到革命”的狭窄性,把文学创作引入了一个更为广阔、自由的“由启蒙到民间”的新天地。比如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就为文学带来了崭新的艺术空间。
民间立场的观照,为解读《边城》这个悲剧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虽然沈从文是在都市中为现代人想象乡土描绘图景,但是每每潜心于自己笔下的民间世界时,那种“自愿作乡下人”的意愿总会自动发生效力。就像小说第二章提到的那样,“河中涨了春水”,“沿河吊脚楼,必有一处两处为水冲去”,而湘西民众“对于所受的损失仿佛无话可说,与在自然的安排下,眼见其他无可挽救的不幸来时相似”;天保的身亡、傩送的出走、老祖父的故世以及翠翠的等待,这一切如果从“一个普通乡下人”的眼光来看,正是“在自然的安排下”,面对“无可挽救的不幸”时的“无话可说”,他们恬淡自守着那古老、质朴而简单的存活法则,原本就像天气刮风下雨,山中草木的春华秋实一般,自然不过,生生死死,轮回不已[1]。如果跳出现代性规划的想象图景,就会发现白塔轰然圮坍,“又重新修好了”,这正是地道的中国乡土式的地久天长。在人类自我生命的节律和大自然节律的应和、共振中,“时间”的意义趋向永恒(特定空间的非时间化、时间的恒定化),从而凸显出一种苍莽辽阔、深邃沉静的无言之美……
1936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从文小说习作选》,《习作选集代序》里谈到《边城》,有这样一段“指责”读者的话:“我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那么,作者在作品背后隐藏的,到底是什么呢?如果从文学世界和创作主体的关系来看,这其实是理解《边城》的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沈从文研究专家张新颖教授有过一段深入的论述,以这段文字来结束本文,最恰切不过了:
“原来这个美丽精致的作品里面,融汇了作者个人‘年青生活心受伤后的痛楚’,‘过去的失业,生活中的压抑、痛苦’。原来《边城》中的悲剧意味可以说是指向沈从文本人的生活痛苦。这其中蕴藏了作者以往的生命经验,是包裹了伤痕的文字,是在困难中的微笑……
“‘微笑’担当了什么?由自然美、人性美和人情美构成的沈从文小说世界的‘微笑’面容,担当了什么?如果不看到这一点,单说沈从文的景物描写如何如何美,人情风俗又如何如何淳朴,就把沈从文小说中的自然和人情看得太简单了。‘微笑’背后不仅有一个人连续性的生活史,而且有一个人借助自然和人性、人情的力量来救助自己、纠正自己、发展自己的顽强的生命意志,靠了这样的力量和生命意志,他没有让因屈辱而生的狭隘的自私、仇恨和报复心生长,也是靠了这样的力量和生命意志,他支撑自己应对现实和绝望,同时也靠这样的力量和生命意志,来成就自己‘微笑’的文学。
“‘微笑’的文学对于作者个人有这样的担当,如果把这种担当从作者个人扩大到更广阔的范围呢?沈从文在《题记》里说到‘民族复兴大业’,并非只是随便说说的大话,也不是理论的预设,他是从个人的生命经验和文学之间的紧密关联出发而引生这种思想的,这种思想与蕴藏在清新朴实的文字后面的‘热情’渗透、交织在一起。”(参见张新颖:《沈从文精读》)
注 释:
[1]《湘行散记》中一篇《1934年1月18日》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在水行途中,一只大船“搁浅在滩头激流里。只见一个水手赤裸着全身向水中跳去,想在水中用肩背之力使船只活动,可是人一下水后,就即刻为激流带走了。在浪声吼哮里尚听到岸上人沿岸追喊着,水中那一个大约也回答着一些遗嘱之类,过一会儿,人便不见了。”这件让沈从文大感“惊心眩目”的事(有点类似《边城》中天保大老的身亡),“从船上人看来,可太平常了”。从中我们不难发现“普通乡下人”和现代知识分子这两种视角的差异。在同一篇的稍后部分,沈从文又有这样的感叹:“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我有点担心,地方一切虽没有甚么变动。我或者变得太多了一点。”两种视角交替的情形,在《边城》中也可见到。沈从文一方面醉心于描绘那个生生死死、千古长流的自由世界,“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但是知识分子的视角又时或浮出,思索着“常”与“变”,对那个“千年不变”的自由世界投去“无言的哀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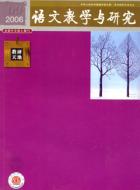
- 新课程下学习方式的五个特点 / 赵同宇 赵 兰
- 文言文译句的思路 / 李 凤
- 关于文言文教学的突围 / 郭新国
- 上好语文引导课 / 陈维贤
- 语文综合性学习的基本途径 / 李方艾
- 语文学习的评价方式应充满人文关怀 / 乐殷南
- 诗歌美育的因素及实施途径 / 唐晓军
- 文言文教学的问题与出路 / 代爱珍
- 合作学习的误区与对策 / 李建芳
- 《荷花淀》的矛盾还原分析 / 童艳华 袁海林
- 《孟子》的辩论艺术探微 / 赵素娟
- 关于《藤野先生》的一处解释 / 李泽文
- 钱锺书论《阿Q正传》发微 / 王明华
- 新课标指导下的说课活动 / 徐永峰
- 语文课外阅读量的细化及阅读模式 / 端木春晓
- 想象赋予阅读的魅力 / 鄢桂芳
- 阅读教学中的默读静思 / 周祖勋
- 阅读小说切莫忽略环境描写 / 张学勤
- 阅读教学中的情感参与 / 汪太福
- 快速把握散文主旨的方法 / 车庆欣
- 解读古典诗词中的“水”意象 / 邵世荣
- 表达方式的审美解读 / 李志军
- 作文课堂与生活空间 / 李东方
- 想象在写作中的运用 / 邱桂萍
- 记叙文写作须讲五美 / 卢 明
- 从古文论中看写作问题 / 王爱波
- 题材处理的几个技巧 / 苏晓徐
- 话题作文的审题·拟题·点题 / 张德勤
- 新课标写作教材设计特点分析 / 赵年秀
- 沈从文《边城》细读 / 金 理
- “客”族词研究 / 王洪涌 刘合柱
- 网络时代教学语言的转变 / 王巧云 汪红梅
- 古代白话小说点校本中的标点问题 / 匡鹏飞
- 生命的言语与言语的生命 / 虞红敏
- 《安塞腰鼓》课堂实录 / 何琼侠
- 《赤壁赋》教学设计 / 张慧玲
- 为语文新课程改革一辩 / 吴平安
- 论语文课堂文化的维度 / 毛承延
- 隐痛:正本清源话创新 / 王庆兰
- 从模拟考试谈高考作文审题 / 郭智军
- 我的作文辅导与江苏高考作文发生巧合 / 徐 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