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建设 2008年第5期
ID: 81112
语文建设 2008年第5期
ID: 81112
重读经典
◇ 袁湛江
●经典是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长期以来决定阅读的书籍,是世世代代的出于不同的理由,以先期的热情和神秘的忠诚阅读的书。——博尔赫斯
●语文教师要引领学生步入经典,首先自己要阅读经典,要与学生努力形成“共生”效应。其次,教师还要重读,反复读,惟其如此,才能真正读懂,才能在教师的重读与学生的初读之间找到切入点,从而继承与发扬民族文化,提升精神境界。
本期我们编发浙江宁波万里国际学校中学袁湛江、邓彤、桂维诚,浙江宁波效实中学郑素芳以及浙江余姚高风中学黄文杰等老师关于经典阅读的一次对话,希望能引起广大语文同人的思考。
袁湛江:经典作品的阅读教学一直是中学语文教学的重点,其实也是难点。今天我们围绕经典作品的阅读教学来讨论,我们选择一个小的切入点:谈谈重读经典这个话题。
郑素芳:先请袁老师讲一讲为什么要选择“重读经典”这个话题。
袁湛江:源于我们对经典作品的基本理解。经典,一定是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可以跨越民族和文化领域的作品。丰富的内涵以及作家的模糊处理赋予其“说不尽”的主题,而且很多经典作品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情景下阅读会带给人们不同的启示和回味。所以对语文教师来说,重读经典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需的。
桂维诚:重读经典是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刻认同,是一个人能够与商业社会保持一定距离而不致完全陷入其中的基本保证。这一方面是个体通过文化进行群体认同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文化借助个体得以实现、延续甚至进一步深化其自身的契机。一种文化如果要绵延不绝地存在下去,少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用心继承与精心发扬,因此重读经典不仅是个体提升精神状态的需要,也是个体进行民族认同的责任所在。关于生死、爱憎、美丑、善恶的题材既是文学作品写不尽的宏大母题,也是人类对自身命运世代深思省察的永恒命题,所以读经典一定会常读常新,魅力无穷。
邓彤:重读、再三读、反复读是走进经典的唯一途径,又是语文教师专业发展的必由之路,还是提升学生语文素养的不二法门。
袁湛江:还有一点考虑,就是中学语文教学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语文教师对经典作品不断地重读就会有不断的发现。我们中学语文教师对许多经典作品的初次阅读并不是做了教师以后,而是在做学生的时候,那么,当我们做了教师以后再来读这些作品,感受会发生很大变化;刚做教师跟做了十年、二十年教师阅读同一经典作品的感受又有不同。我们如何将这些新的发现和感悟变成学生初读经典的一种资源,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大家先集中到一个问题上:在重读经典作品的时候你们有什么感受,最好结合具体作品谈谈。
黄文杰:重读经典,我们意在突破主题先行的观点的束缚,突破教学方式过于技术化的束缚,突破以教代学、以本为本的程式的束缚,还以阅读原态。重读经典,不仅是对经典本身的深入探究,同时也是重构教学策略,使其过程与方法激起学生阅读的兴趣、质疑的热情,培养学生读书的习惯和能力、思维的深度。有这两者为基础,即使是对《祝福》这样的短小经典也能找到常读常新、常教常新的教学快乐,比如有人读出祥林嫂是一个没有春天的女人,有人读出社会的冷漠,有人寻找祥林嫂的微笑,有人回味五处有关钱的描写,等等。
袁湛江:你说的是“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吗?
黄文杰:不一定是“一千个读者”,有时候“一个读者”也会读出“一千个哈姆雷特”。不仅不同的读者读同一部经典作品会产生不同的感受;即使是同一个读者,在不同的心境、不同的阶段也会产生不同的阅读感受。所以我强调“常读常新,常教常新”。
桂维诚:我以前上《祝福》时,曾以传统的主题即“四权”对妇女的迫害来归纳课文,一次课堂上,突然有个学生问:“狼代表什么?如果阿毛不是被狼吃掉,也许祥林嫂的遭遇就不会那么惨。”这个问题引起了大家的热烈讨论。显然这里不能简单地把狼与旧社会挂钩,狼吃人在新社会也可能发生。这就需要我们对经典进行重新解读。
袁湛江:重新解读有什么新的发现呢?
桂维诚:大家通过深入探讨认识到,狼吃了阿毛以及贺老六伤寒复发壮年早逝都是非社会性灾难。在新社会,一个丧夫失子的弱女子会赢得人们的同情和帮助,可以改变悲剧的命运。但是在祥林嫂生活的那个时代,封建礼教猛于虎狼。如果说恶狼和病魔夺去她儿子和丈夫的生命带有某种偶然性,那么祥林嫂最后走向死亡则是必然,她的“逃—撞—捐—问”只是对悲剧命运的徒劳反抗,杀害她的元凶是比虎狼更凶恶的封建礼教和迷信思想。
袁湛江:现在看来,“四权”显然过于概念化和政治化,缺少从人性的角度和高中学生阅读接受基础的角度出发的考虑。但是这种观点在中学语文教学参考书中主导了好长时间,现在40到60岁的人接受的基本都是这种观点,所以没有重读经典的过程,我们的观念就会老化。
桂维诚:跳出“四权”的定论,从小说的典型环境入手,还能发现鲁镇是一个受封建理学思想严密控制、弥漫着浓厚的迷信气氛、对受苦人表现出令人战栗的凉薄与冷漠的封闭式社会。这里有阶级斗争的环境,也有非阶级斗争的环境;有社会因素,也有自然因素。祥林嫂连遭不幸,再受到种种精神酷刑,岂不雪上加霜?联系鲁迅的《灯下漫笔》一文,祥林嫂正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典型,她的复杂性格中既有反封建的一面,又有受封建迷信毒害的一面。通过重新解读,可以读出作者对鲁镇这种凉薄人情的鞭挞,是为了“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袁湛江:这种丰富的思想感情和复杂的人物性格必须经过不断的重读,才能逐渐认清。
黄文杰:我们在重读经典的过程中,往往会发现这种情况:越是深入下去,越会发现主题的多元性和人物的游离感,就像进入了一个深不可测的洞穴,越往里走,岔路越多,问题越多,不确定性也越多。袁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袁湛江:我提一个问题:碰到这种情况,你的感受是无所适从的困惑,还是挑战定论的激情?
黄文杰:两者都有,但是激情更多一些。
袁湛江:困惑我理解,激情我更欣赏。坦率地讲,一个人在阅读经典作品的过程中没有遇到任何障碍、一帆风顺地把握原意,几乎是不可能的,有质疑、有争议、有困惑都是正常现象,但要有挑战的激情和勇气,黄老师刚才所做的关于“洞穴”的比喻我们几乎人人都遇到过。
邓彤:读书,首先需要勇气,要敢于打破经典作品的神秘感。许多伟大的经典其实非常“平易近人”,大多数经典都淳朴得如同生活本身,你能感受生活,你就能欣赏经典——只要你具备最基本的阅读能力。细细阅读经典,其实就是细细品味生活,或者说,是在体验一种你从未经历过的生活,这又有什么可畏惧的呢?用体验生活的方式阅读经典,将会读出无穷的滋味。
袁湛江:在阅读过程中产生歧义往往会影响对作品的基本理解,而重读经典为接近作品的原意提供了可能。刚才桂老师谈到了《祝福》中的祥林嫂,说她“既有反封建的一面,又有受封建迷信毒害的一面”,那么,她被迫嫁给贺老六而“闹婚”这一情节,是表现了她对封建思想的反抗,还是表现了她被封建思想毒害?
黄文杰:这个问题我也注意到了,而且我们学生的争论还很激烈。持“反抗”观点的人说:“祥林嫂虽然是个奴隶,但她在鲁家已经坐稳了奴隶,并且她很满足这种奴隶地位,何况即使是一个奴隶,她也有追求自由的愿望啊,所以有人来打破她这种自以为很满足的生活状态,她自然要反抗了。”持“毒害”观点的学生说:“祥林嫂之所以反抗,归根结底是她心中有一个观念:从一而终。所以她反抗不是对命运的抗争,恰恰是不惜用生命来维护封建礼教,可见被封建礼教毒害之深!”
[##]
袁湛江:你是什么观点?
黄文杰:祥林嫂的可怜不仅因为她的悲惨遭遇——出身卑贱、祥林早死、贺老六病死、儿子惨死,以及如此可怜的境遇非但没有得到社会的关怀,却还要被婆婆绑卖、大伯收屋、鲁镇百姓嘲弄、地主老爷家鄙弃,落得讨饭饿死的结局,还因为无形潜入灵魂的可怕的地狱迷信、贞洁礼教,使得走入困境的祥林嫂陷入活也不是、死也不能的精神绝境。勤劳善良的祥林嫂,不能因为她的勤劳善良在这个社会里获取生存的机会,反而被践踏、吞噬。祥林嫂也并不是一味逆来顺受,她会逃出来反对婆婆虐待,强力反对婆婆绑卖,省吃俭用到极点来捐门槛,用自己的力量来反抗不公平的命运,用自己的力量想得到这个社会的承认,但悲哀的是她这是用贞洁反贞洁、用礼教反礼教的盲目、自发的反抗,这在封闭的鲁镇永远也不可能找到重生之路,祥林嫂只可能绝望而死。我初读的时候认为祥林嫂抗婚是反抗封建礼教,后来在重读的过程中,把祥林嫂还原到文本中,还原到她所处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就从原文中找到了很多不同的信息和依据,另外我又读了鲁迅同期的其他作品来论证我的结论,现在越来越认识到祥林嫂的“自卫式”反抗行动源于她对封建礼教的不自觉的维护,认识到那种心灵防守的脆弱与深刻的悲凉。
袁湛江:所以在深入的阅读过程中不断的发现问题不是件坏事情,它会逼迫我们对作品做更仔细和深入的研读,从走近经典到走进经典。
黄文杰:目前在经典作品的阅读教学中,盛行一种多元解读的说法,袁老师怎么看?
袁湛江:这是对“非此即彼”的一种反动,“非此即彼”强调的是文本解读的一元性,这对那些宏大的复杂的史诗性作品往往不适用,例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有时即使是很短小的作品,如果表现出来的思想感情比较复杂,也会形成读者的多元解读,比如对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历来就存在争论。但莫衷一是,多元泛化,看似中庸,实无主见,不应该成为一种阅读倾向。语文教师既要调动自身的生活积累,又要注意回归到作者的写作背景中去,千万不能用自己今天的阅读感受代替作品的原意。这样经过深入研读,你会从多元解读中解放出来,也就是说,不要放纵自己多元泛化解读。
郑素芳:我想举一个自己重读《论语》的例子来说明对多元解读的理解。《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是《论语》中较完整的一个片段。孔子为什么“与点”一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初读文章,我感觉曾皙的回答“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描绘了一种闲适美好的生活,这种生活让孔子向往,这种描述让他愉悦,因而他赞成曾皙。后来发现参考书上说曾皙描绘的是一种大同社会的生活,这正是孔子所追求的,这似乎印证了我初步阅读的感受。再后来又看到了东汉王充的见解,他认为曾皙所述是古代一种叫“雩祭”的祭祀仪式,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曾皙能对古礼作如此具体生动的描绘,并以此寄托自己的理想,在孔子看来是十分难得的,因而他内心狂喜而情不自禁地赞叹。这样解释似乎有理有据,但总觉得过于理性,没有读出最细微、最真切的东西。有一次听到一堂公开课,主讲老师就是持这种观点的,这堂课始终围绕“礼”来解读整个文本,我觉得太过个人化了。
袁湛江:实际上你对这几种解读都不满意。
郑素芳:是的,所以再次研读原文,结合《论语》等文献对孔子经历和个性的阐述,我悟出了更多的东西。意识到这是一次非常生动的课堂活动,师生的话尽管不多,但却细腻地传达出他们各自的性格特征,以及彼此之间的微妙关系。
袁湛江:请你具体分析一下。
郑素芳:首先看孔子与子路。子路雄心勃勃,表示他能在三年之内治理好一个面临内忧外患的中等规模的国家。孔子听完后一“哂”,这“哂”不是赞扬,而是明显的批评。这一点曾皙感觉到了,课后他追问孔子原因,孔子说是因为子路不够谦让;冉有、公西华也感觉到了,因此他们回答时措辞特别谦卑,尽管他们也志在为政。子路自己也应该感觉得到,但估计不会因为老师的这一“批评”而受到伤害。《论语》中的子路是一个率真、耿直的人,经常因鲁莽而被孔子批评,他也敢批评孔子的“迂腐”,师生关系相当随便;更何况,孔子的批评是善意的。子路志向高远,这和年轻时的孔子多么相像!孔子曾经自信地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而今孔子历尽艰险,在他看来,子路虽然真诚,但多少有些年少轻狂。
再看孔子和冉有、公西华。冉有表示他只能在三年之内使一个小国物质上比较富有,精神的教化则无能为力;公西华表示他愿意学习做一个主持赞礼和司仪的官。孔子听后不置可否,这似乎不符合他老师的身份,但却是彼时孔子真实内心的体现。在孔子看来,冉有、公西华态度谦和,这符合君子的要求。他们志在为政,符合孔子一贯倡导的积极入世的原则。只是此一时彼一时,如今的孔子对为政治国已经不太感兴趣了。因此,面对冉有和公西华的回答,他既不好违心地赞赏,又无法批评否定,只能保持沉默。
最后看孔子和曾皙。曾皙表示他的志向是过一种轻松洒脱、闲适逍遥的生活,这看似散漫的“志向”赢得了孔子的极力赞赏。从孔子的赞赏中,我们可以窥见他丰富的内心世界。孔子是一个社会责任感特别强的人,为了实现“礼治”的愿望,他一生奔波,风餐露宿,饱受白眼;他意志顽强,勇气可嘉,但屡屡受挫,年华的流逝难免使他心灰意冷。从灵魂深处来说,他也许一直渴望过一种闲云野鹤、自由自在的生活,如今这种愿望尤其强烈。曾皙的话深深触动了孔子的心灵,他才是孔子的知音啊!因此孔子不由“喟然”长叹,毫不掩饰他对这个学生的赞赏之情。
袁湛江:几个学生的不同性格及其与孔子之间的微妙关系好像让你有了什么发现?
郑素芳:是的。在这一节“言志”课上,孔子首先是一个老师,因此他反复鼓励学生“各言其志”,以包容的心态接纳学生不同的志向,这是他作为教师的理智,也是职业道德的需要。但他更是作为一个真实的“人”而存在的,他不吝惜赞扬,也不忌讳批评,“言志”的是学生,而他也不是以主持者的身份高高在上,而是在对学生的批评或表扬中表明自己的内心世界,这是一个多么真实而可爱的孔子!也许我这次的解读过于感性,但自觉与文本更近了。我想,作为语文老师,对于经典作品,应该有一些属于自己的阅读感受。
袁湛江:看得出来,你很喜欢这篇文章,重读是下了些工夫的,对孔子与几个学生的不同态度和关系分析得比较透彻,而且参考了一些有价值的文献资料。你在多元解读中作出了明确的选择,或者说形成了自己的见解——孔子是作为一个真实的人存在的,然而,此时此刻他已“心灰意冷”,“从灵魂深处来说,他也许一直渴望过一种闲云野鹤、自由自在的生活,如今这种愿望尤其强烈。”我不知道,这种观点由何而来?
郑素芳:根据我对孔子生平的了解而形成的一种判断和推理。
袁湛江:这种观点未必没有道理,但是,单靠孔子对几个学生的不同态度作出推断显然不够,当你还没有拿出孔子生平中的事实,包括他的有关言论和行动来佐证他此时此刻的“心灰意冷”,这种“也许……”的判断就变得不够可靠。我的意思是在读书的过程中不管你得出什么见解,一定要言之有据。我期待你能找到更充实的材料来证明你的观点。
袁湛江:现在我们来讨论重读经典的最后一个话题:教师在重读经典过程中所得到的收获和启发如何最大限度地在指导学生阅读中发挥作用?邓老师,你以前曾经阐述过一个“素读”的观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觉得,素读教学的指导方法在教师的重读和学生的初读之间会找到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
邓彤:所谓素读,就是朴素地通过文字符号领会其内在意蕴。素读教学就是教师不多用其他资料,不滥用现代媒体技术,只是运用最传统的对话问答方式,引导学生反复阅读课文,对文本做最朴素的解读。素读追求的是一种本色阅读,力求用本色的教学设计,养成真实的阅读能力。有许多迷恋语言的作家创作作品如园艺家一般细致认真,用一种投入的心境去安排一花一草,不允许有一点不和谐的地方,更不允许有丝毫冗赘。精于修辞学的作家必然有自己的语言体系,有自己珍爱的词语,不愿意看到自己的文章中出现杂词赘句。素读就是引导读者进入文、词、句的深层含义中去,品尝其中的韵味。可以说,这种享受是通过其他媒介(例如图片、影像)了解意义的读者所无法得到的。
素读主义者善于找出散布在作品中的关键词,并从中去探寻这些词语在作者语言体系中的特殊含义。从语言最小的单位——词语,到句子,到段落,到作品的节奏,逐一推敲,最后再把它们重新组合到一起,于是一部作品也就重新被结构起来了。这种作者拈花而读者微笑的境界应该是阅读的最高境界了。
袁湛江:我知道邓老师是一个红学家,《红楼梦》是你在经典作品阅读教学领域建立的“根据地”,能不能结合这部作品的阅读指导来谈谈你的素读理论?
邓彤:我曾利用一个暑假将《红楼梦》原著通读四遍,在一本岳麓书社出版的普及本《红楼梦》上密密麻麻地写下许多读书心得;到1993年,我开始正式开设《红楼梦》导读选修课,试图用一年的时间,引导学生认认真真地研读这部经典著作。此后,每教一届学生,我都要与学生一同阅读《红楼梦》,我的研究水平、教学水平都因为研读《红楼梦》得到了长足发展。
袁湛江:教师与学生一起成长。
邓彤:我且以某个段落的研读为例来阐释“素读”理论。《红楼梦》第三回有这样一段文字:
雨村一面打恭,谢不释口,一面又问:“不知令亲大人现居何职?只怕晚生草率,不敢骤然入都干渎。”如海笑道:“若论舍亲,与尊兄犹系同谱,乃荣公之孙。大内兄现袭一等将军,名赦,字恩侯,二内兄名政,字存周,现任工部员外郎,其为人谦恭厚道,大有祖父遗风,非膏粱轻薄仕宦之流,故弟方致书烦托。否则不但有污尊兄之清操,即弟亦不屑为矣。”雨村听了,心下方信了昨日子兴之言,于是又谢了林如海。
这段文字乍看十分普通,但细细品味却韵味无穷。
袁湛江:经典作品的精妙之处,常常在于用普通的文字表达了无穷的韵味。请邓老师品味一二。
邓彤:先看雨村。“雨村一面打恭,谢不释口”——这是贾雨村吗?想当初,甄士隐见雨村贫寒无力进京应考,赠送了“五十两白银,并两套冬衣”,雨村则“收了银衣,不过略谢一语,并不介意,仍是吃酒谈笑”,那时的贾雨村是何等的清高自重!如今,却做出这般感激涕零的姿态。这是什么缘故呢?是雨村原本就是势利眼,对甄士隐的馈赠不以为意对林如海的举荐感激不已呢,还是经过宦海波折之后已经十分看重功名富贵了呢?这里需要品味。“一面又问:‘不知令亲大人现居何职?’”——雨村此问委实奇怪。前一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已经详细介绍了贾府为官状况,此时雨村为何再次询问?这不是他糊涂,恰是他精明过人之处。试想,冷子兴不过是贾府管家之女婿,他对贾府的介绍雨村未必全信,而举荐复职兹事体大,雨村自然须彻底打听清楚方才放心。果然,当林如海介绍完毕,“雨村听了,心下方信了昨日子兴之言”。一句问话泄露内心,由此可知其人心思缜密如此!如此前后照应之处,读者岂能置之不顾?
再看如海。对于贾赦,他只简单介绍官职,不做任何评价;对于贾政,则是称赞有加。这说明了什么?其实,从人之常情来看,不评价其实也是一种评价。贾赦是贾府中的老流氓,作为妹婿,如海虽然不以为然,但却不好议论,于是只有避而不谈;但他对贾政的由衷称道却暴露了他的基本态度和情感倾向。
最后从全书布局角度来看,这一段对话的作用也非同小可,它为后来贾雨村的飞黄腾达奠定了基础,为故事的推进做好了铺垫。
袁湛江:就是这样一段普通的文字,却让我们咀嚼出如许滋味,这样的文本解读不正是语文教学迫切需要的吗?可见,要想找到教师与学生之间阅读的合适切入点,前提条件是教师要有真功夫,所谓真功夫,就是教师面对经典作品要进得来,出得去。有见解才能有方法。要像邓老师那样,建立自己阅读的“根据地”,培养自己粗壮的感性神经和敏锐的语言悟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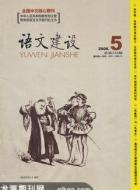
- 高考现代文阅读常见答题误区分析 / 唐海波
- 2008年中考现代文阅读命题预测 / 李仰臣 刘腾辉
- 基于国际性评价项目的语文阅读测试框架初探 / 周 莹
- 中小学语文教育急需汉字字形及属性标准 / 王文勇
- 书法教 / 李宇明
- 说“半糖” / 刘 慧
- “呼叫转移”的新用法 / 俞玮奇
- “凤凰男”与“孔雀女” / 徐 莉
- “赶紧”“赶快”和“赶忙”辨析 / 尹海良
- 漫议“~模” / 林利藩
- 最不实用的最美 / 孙绍振
- 优美的错觉 / 袁 勇
- “书”“疏”“上书”辨析 / 胡元德
- 《氓》主题新解 / 黄全彦
- 韩国中小学“媒体教育”面面观 / 贾 晴
- 归纳·拓展·融通 / 曹志正
- 课堂的精彩是学生的精彩 / 文惠林
- 探索教 / 王泽芳 余日山
- 语文阅读能力的整合策略 / 尹 炎
- “浅文”深教的四种策略 / 胡红艳 雷丽忍
- 重读经典 / 袁湛江
- 朝着中国古诗源头“漫溯” / 刘占泉
- 《离骚》(节选)教学实录 / 夏云陶
- 《〈论语〉十则》教学设计(第一课时) / 吴诗斌
- 《周而不比》教学设计(第一课时) / 叶建峰
- 今天,为什么读《论语》 / 章浙中 周广平
- 小学中年级语文教科书插图研究 / 李祖祥 陈元元
- 论点摘编 / 佚名
- 论语文课程改革的实质 / 潘 涌
- 培养现代语文能力,过好现代语文生活 / 郑 浩 李 节
- 温故知新 / 饶杰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