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教学之友 2015年第8期
ID: 361793
语文教学之友 2015年第8期
ID: 361793
《小狗包弟》研究综述及教学建议
◇ 李路瑶
巴金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追求“真”是他散文最大的特点,语言简约平实,情感丰满真实。其名篇《小狗包弟》更体现了巴金朴实真挚的写作风格。作为教材的经典篇目,研究者和执教者甚多,而较多教学设计存在不完善之处,故笔者从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语言魅力和教学处理等方面分析其研究状况,提出教学建议以供参考。
一、关于《小狗包弟》的思想情感
《小狗包弟》通过一只小狗的命运,讲述了在血腥动荡的十年中一段折磨心灵的经历。巴金用舒缓平实的文笔写沉重的故事,思想情感的多样性和深刻性值得反复研读思考,因而研究者对文章的思想主题进行了多元化解读。汪嘉宾认为小狗包弟的故事渗透着浓重的时代背景,揭示了艺术家和狗之间发生悲剧的必然性,深刻地透视了酿成文革十年浩劫的社会根源。正如《随想录》第二篇《探索集》所示,“探索”“文革”发生的根源,反思文革悲剧是它的主旨;[1]吴飞从故事发生的背景、内容、表达的情感等角度研究发现,文革背景下,巴金为了保全家人,送走了包弟,而妻子萧珊为了减轻对丈夫的压力,甘愿“多受一点精神折磨”,不离不弃。因此吴飞认为文章的主题更多的还有对萧珊的回忆和亏欠,对亡妻的倾诉和怀念;[2]王敬敏则着眼于文中描绘的和谐而充满生机的画面,捕捉到这是巴金对精神家园重建的象征,由此得出文章主旨是对生命的负责,对自我灵魂的救赎,是对病态社会的呐喊,对现实的评判;[3]笔者认可王敬敏深入精神层面的思想情感剖析,巴金晚年多在直面和反思自己,全文充满了赤忱的态度,让读者看到了这位“世纪良心”老人的伟大人格。
巴金曾在《探索集后记》中表示:“我写作是为了战斗、为了揭露、为了控诉、为了对国家、对人民有所贡献,但绝不是为了美化自己”。[4]因此,王志强从真善美角度思考了本文的主题:敢于、严于解剖自己的求真期待,“老吾老”、“幼吾幼”、“泛爱众”的求善渴望,和谐美好家庭生活的求美守望。[5]在笔者看来,深受中国传统“仁爱”思想浸染的巴金,又接受了西方民主思想的博爱情怀,希望用自己深刻理性的反省,唤醒社会对真善美的追求。
多数研究者都是从单角度对文本的情感进行解读,而一篇富有时代印记的文章往往需要读者从多角度层层剥开。曲竟玮从情感、社会和思想三个角度进行更加深入的剖析。从纵向的感性分析中得出情感线索——人非物亦非,表现出感情的折磨、情绪的幻灭,呈现出“精神创伤”的情感主题。从横向的理性分析中,认为“我”和萧珊的苦难经历才是文章的重心所在,文章的社会主题在于通过一只小狗的故事,将以作者夫妻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在动荡年代中艰难不易的命运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全文的结构重心是重复了三次的“您的小狗怎样?”,叩问小狗命运也即叩问“我”的责任,叩问时代的命运,“我”未能尽到人道的责任而那个冷漠时代的中国最悲剧的也是人道的缺乏。这句问话揭示了文章的思想主题——人道主义。[6]
二、关于《小狗包弟》的艺术手法
晚年的巴金从《小狗包弟》开始反思自己、忏悔过去,细细品味《小狗包弟》,可感受到巴金行文运笔之间的独特魅力。
1.叙述手法多样化。本文采用了插叙、倒叙和补叙等多种写作手法,使文章在平缓自然的讲述中有起有伏。具体体现在:一、引子部分讲述了艺术家和狗的故事,交代了写作的缘由;二、由现在写到过去,转入对往事的回忆,中间插叙了日本朋友对包弟的喜爱;三、用倒叙手法交代了包弟的处境和结局:“包弟已经没有了”;四、补叙事情的经过,回到现实中,写当下对小狗包弟的歉意和怀念之情。
2.对比手法鲜明化。文章平静自然的语言下,暗含着人与狗的多次对比:首先,艺术家遭到专攻队的残酷武斗时,人与狗表现的强烈对比——“认识的人”无情冷漠而小狗却亲切忠诚。其次,小狗由“包弟”变成“包袱”,“我”与包弟的鲜明对比——小狗的重情重义与“我”的自私懦弱,背上了更为沉重的精神包袱,这种对比更加 引人深思,也让人感受到文革时期人与人之间的自私冷漠悲凉。
3.修辞艺术真切化。王彩从文本建构角度探寻,认为本文的修辞言说完成了对狗的物性认知向人性化认知的跃进。从动词的使用领会到巴金的修辞预设和修辞意旨:“跑”、“奔”、“叫”、“扑”、“闻”、“舔”、“抚摸”等动词交代无名小狗是一个修辞铺垫——比照性的物象之狗;“作揖”、“讨”、“守”、“厌倦”、“等候”、“高兴”等词语集合,描述性地传达了一种跃进式认知——包弟是一只人性之狗。[7]无独有偶,谭学纯运用修辞义素进行细致分析,从广义修辞学“话语建构—文本建构—人的精神建构”的阐释路径着手,即分析“人”与“狗”互为镜像的修辞叙事,“包弟”向“包袱”转换的修辞情境,“包袱”自身的修辞语义暗转,同位短语“小狗包弟”被人为拆解的修辞化分离,“我”变成“包弟”的修辞推理依据,以及《小狗包弟》道德自责和道德追问主题。[8]这些修辞技巧向读者展现了人性、兽性的颠倒,正是对那个人道丧失的社会极为深刻的鞭挞。
4.结构设置精巧化。全文重生活琐事的描写,但结构上颇有巧妙之处。方来龙深入挖掘了其结构之美,具体分析了以下特点:一、张弛有度:开端描写艺术家被批斗的惨状以及无名小狗被打伤致死的情景,让读者置身于血腥紧张的气氛中,接着描写小狗包弟的可爱乖巧,让读者走入温馨之中,在包弟被送往实验时,读者紧张的情绪又达到高潮。二、线索贯穿:明线——小狗包弟的故事;暗线——“我”对小狗包弟不断变化的情感。这两条线的交织更让读者看到了悲剧中所隐藏的深层次社会原因。[9]
三、关于《小狗包弟》的语言魅力
散文语言讲究叙事描写,比喻含蓄,而巴金笔下描写的现实生活往往是简单而通俗的,他曾评价自己的文章是“不打扮”。
叙议结合:全文前一部分以记叙为主,采用白描手法描写小狗,同时夹杂着抒情议论,“日本种黄毛狗,干干净净”,“作几个揖”,“讨糖果吃”,一只可爱聪明的小狗就跃然于纸上;后一部分以抒情议论为主也夹杂记叙性文字,“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我瞧不起我自己,我不能原谅我自己”,语言带有杂感、随笔的特点。[10]多种表达方式并用使文章在散文特色之外,增强“春秋笔法”的色彩,更现凝练与简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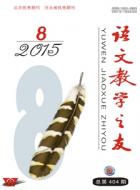
- 高中语文教学中学生审美素养的培养 / 杜润青
- 高中语文课教学目标的设计误区与解决策略 / 穆俊成
- 初语教学中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 / 吴璇
- 语文教改中的几点思考 / 朱云静
- 从点到面:让小组合作更有效 / 林霖
- 放飞诗情 升华认知 / 李敏
- 谈“微课”在中职语文教学中的应用 / 陈晓静
- 谈打造语文高效课堂 / 徐莹
- 追求美感与效率并重的初中语文课堂 / 杨锋
- 《蜀相》教学课例评析 / 韩宝江
- 《小狗包弟》研究综述及教学建议 / 李路瑶
- 《芦花荡》开篇景物不能表现敌人倍感恐怖 / 严若红 丁海军
- 项脊轩 / 江海燕
- 品读《散步》之美 / 陈飞
- 柳妈的善良是把刀 / 高培存
- 谈快速高效涵泳记诵文言文 / 王彦梅
- 今年杜鹃啼又是,非比昨日愁煞人 / 罗彩艳
- “先学后教”在高中文言文教学中的运用和思考 / 王德金
- 语文课堂兴趣激发的方法例析 / 谢跃娟
- 谈语文“预习、讨论、检测、迁移”四环节教学法 / 张克东
- 语文世界中的踽踽独行 / 许夏
- 修改病句之中医诊疗 / 刁可佳
- 高中语文教学中的人文教育实践路径研究 / 孟庆华
- 古诗词阅读应注重“语言张力” / 胥伟
- 非连续性文本阅读情境设计策略 / 宓娟
- 例谈指导高中生自主修改作文的途径 / 杨燕
- 语文味教学法在记叙文写作教学中的应用 / 向晓璐
- 变“本”为“纸”:作文形式的改变提升了训练效率 / 王永洛 王青红
- 借助时评提高议论文写作能力 / 郑仁水
- 基于职业能力视角的中职应用文教学策略 / 王华
- 羊年说“羊”字 / 齐殿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