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教学之友 2007年第7期
ID: 359429
语文教学之友 2007年第7期
ID: 359429
古诗文备课札记
◇ 曹伯高 钱吕明
1.关于李白《将进酒》的两个“君不见”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这是李白诗歌名篇《将进酒》开篇的两个排句。理解起来并无困难,时光易逝、人生易老这八个字即可尽其意。八字尽意,偏偏要用三十四字,妙处何在?
我们知道,自从孔夫子在水边发出“逝者如斯夫”的感慨之后,水即成了时光的隐喻。这可作时光代称的黄河之水,如果只是像小溪一样缓缓流淌,人们自然不会惊叹光阴似箭;即便黄河之水汹涌澎湃,如果能够周而复始,去而复回,人们也无须悲叹光阴不再;现在的问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落差如此巨大,流速如此迅急,裹挟万物,电闪雷奔,一泻千里,势不可挡,让人只能徒唤奈何。但是,“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黄河千古流,依然是黄河,人呢,早晨还是青丝红颜,傍晚已经霜雪满头,都说是人生短促,现在短促的人生只在早晚之间,如何叫人不悲伤?这里的黄河,既是时光的最佳对应物,又是伟大永恒的象征。黄河越是永恒,人生越显短暂;黄河越是拥有无穷的生命活力,人生越是显得渺小脆弱。“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而人生的痛苦又莫过于对生命短促的忧虑,诗人将无情的事实用夸张和对比的手法呈现在人们面前,真是惊心动魄。不仅如此,诗人又连用两个“君不见”,一再呼告,剥夺了人们逃避思考的全部空间,让你没有任何回避的余地。一般的乐府诗只在篇首或句末偶而用之,李白两句连用,构成长句铺排,如挟天风海雨,铺天盖地而来,其艺术感染力之强,风雨惊之,鬼神泣之。
诗人如此经营诗的开头,用意却在劝酒。既劝别人,也劝自己。原来诗人素有“安社稷,济苍生”之志,却因遭谗被迫离开长安,胸中郁积很深,于是借酒兴诗情,抒写政治上不得志的深沉愤懑。“人生得意须尽欢”,“会须一饮三百杯”,“将进酒,杯莫停”,“与尔同销万古愁”,当是饮酒过程中的酒人酒语。在李白如此强大的劝酒攻势面前,有谁能不痛饮乃至狂饮呢?当然,诗仙的思想情感不会如此单一,《将进酒》同样流露出复杂而矛盾的思想情绪,傲视圣贤、蔑视富贵、及时行乐的思想,都借豪迈奔放的诗句宣泄出来。试想,没有鬼斧神工的两个“君不见”,能有如此动人心魄的力量吗?
2.关于“噫吁嚱,危乎高哉!”
李白《蜀道难》袭用乐府旧题,着力描绘蜀道之高峻险要,一唱三叹,音韵铿锵,气势磅礴,豪迈壮观,其开篇一句,破空而来,很值得细细品味。
诗的魅力在于抒情,文学的生命在于创造。就凭《蜀道难》开篇这三个感叹词,李白就是当之无愧的诗歌巨匠。他一不小心崩出来的这三个感叹词,是中国诗歌史上天才的创造。在李白之前的古诗中,有在诗的开篇用感叹词,并且竟然连用三个的吗?没有。为什么?因为从来就没有谁这么写过。“突破”之难,创新之难,难于上青天。再高明的模仿,也不过是模仿,决不会在文学史上留下哪怕是浅浅的印痕。《诗经》和《楚辞》中多用“兮”字,但都是用在句尾或句子中间。汉代梁鸿的《五噫歌》,五句诗句尾皆用“兮”,并且紧跟一感叹意味更强烈的“噫”字,这已经是了不得的创造,开篇即连用三个感叹词,这样的创举,舍李白其谁也?
当然,李白连用三个感叹词,并不是故作惊人之举,自有其非用不可的道理在。试想,猛然看到“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人们的第一感觉是什么?是惊讶,是震撼,自然发而为声,一声惊叹,这样便有了“噫”。如果蜀道只是一般的高峻,有这一声也就够了,问题是,蜀道之难,一处比一处高峻,一处比一处险要,一处比一处峥嵘,一处比一处骇人,人们的惊叹,自然是一声之不足,又有第二声,二声之不足,又有第三声,数声之后,方才回过神来,发出“高呵高呵”的感叹。可见,李白的开篇之笔,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真可谓文学史上的神来之笔。如果直接用“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开头,整首诗就有托不起来的感觉,诗味骤减。品读古诗乃至任何优秀的文学作品,有一点比较文学的眼光,有一点文学史的视野,有一点细细品读的功夫,会读出更多的味道。
3.关于“解鞍少驻初程”
读姜夔的《扬州慢》,人们对“解鞍少驻初程”一句往往很少留意,以为不过是一般的交代而已。这样的解读,实在有点可惜。
作者在词前小序中点出这首词的主旨在黍离之悲,也就是抒发对国家昔盛今衰的痛惜伤感之情,实际是亡国之悲。自然词中须有“昔盛”与“今衰”两个方面的内容,以构成鲜明的对比。词中写“昔盛”的句子,“淮左名都”一句,突出其大都会的地位;“竹西佳处”一句,以点代面,突出扬州城昔日繁华热闹的情景;“春风十里”一句,更是借杜牧的诗句,以复现昔日扬州城十里长街的繁荣图景。那么,介于这几句之间的“解鞍少驻初程”句,在篇幅有限的词中,就不可能只是一般过程的交代,理应是对扬州城往日繁华的渲染。“初程”,此行最初一段路程,说明此行路程不短,而作者是骑马,不是坐车,可见此行并非悠哉游哉,颇有一点赶路的意思。有谁要赶一段长长的路程,却在出发之初停下来,逛一逛风景名胜以一饱眼福的呢?人之常情,这样的情况是极少出现的,除非此地有着非同一般、异乎寻常的吸引力。扬州恰恰是这样一个对少年姜夔来说有着巨大吸引力的地方。一是扬州几百年的繁华,实在令人神往,“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由此可见一斑;二是杜牧的文采风流,也令少年才子不惟景仰,更会产生无穷的想象。是的,他知道扬州城已经两次遭到金兵的洗劫,对扬州的衰败已经有了相当的心理准备,但他绝难想象,天下闻名的扬州城会没有一点繁盛的影子,因而他解下马鞍,走进城去,去追寻在梦中不知出现过多少次的富商辐辏、游人荟萃、丝弦管乐、笑语欢歌的情景。经过战火洗劫的扬州城尚且具有如此惊人的吸引力,扬州昔日的繁荣局面可想而知。但展现在他眼前的,却是荠麦青青、废池乔木、清角吹寒、一座空城,这怎不让杜牧“重到须惊”?怎不让作者感叹“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没有如此强烈的反差,怎能把黍离之悲推向极致,产生惊心动魄的艺术感染力?
4.关于“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
苏轼在他的《石钟山记》中,以自己的目见耳闻,肯定了郦道元关于石钟山得名由来的见解,否定了李勃的意见。苏轼在总结此次考察时,把“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作为石钟山得名由来未能流传下来的原因之一。这里,苏轼完全是以己度人,渔工水师根本就不可能“知”。
首先,作为长期生活在石钟山的寺僧,应是民间懂得石钟山得名由来的权威,连寺僧也只是“使小童持斧,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可见李勃之说深入人心,渔工水师根本就不可能想到石钟山还会有别的得名由来。
其次,从第二段来看,渔工水师根本就不可能在夜晚驾小舟“至绝壁下”,因为“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又有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阴森恐怖,令人心悸,连苏轼自己也感到害怕,“心动欲还”,而当“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时,舟人更是“大恐”,可见,他们是不可能与苏轼有同样的发现的。
再次,渔工水师即使有和苏轼同样的发现,也不会想到这和石钟山得名由来有什么关系,因为渔工水师不可能具备作者那样的历史文化知识。苏轼“徐而察之,则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淡澎湃而为此也。舟回至两山间,将入港口,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有窾坎镗鞳之声。与向之噌吰者相应,如乐作焉”。他的这样一种感受与联想,渔工水师是不可能具备的。至于“噌吰者,周景王之无射也;窾坎镗鞳者,魏庄子之歌钟也”,对渔工水师而言,就更是天方夜谭,因为《国语》《左传》的相关记载,苏轼自然是烂熟于心,渔工水师可能连书的封面也未必见过。
再说,渔工水师虽然不会写文章,但如果他们知道石钟山得名缘由,还是会口耳相传,必不会出现“寺僧使小童持斧”扣石之事,此事只能说明渔工水师根本就不“知”。在这一点上,苏轼完全忽略了渔工水师的知识结构,属于想当然耳。可见,即使是大学问家,如果思虑不够周全,也是会闹笑话的。
(作者单位:兴化中学
扬州高级中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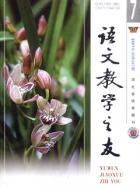
- 回归语文教学原点 / 吴 奇
- 语文教学要为讲解法正名 / 吴章贵
- 新课改背景下中学语法教学的现状调查与思考 / 刘爱霞
- 初三语文,冷落课本不应该 / 黄静华
- 如何维护学生的话语权与读悟权 / 吕 琳
- 例谈不和谐课堂的五种情形 / 张长松
- 语文之本不能缺失 / 黄长红
- 培养“语法感”的八种方法 / 邵统亮
- 把书读“厚” / 隋国英
- 诗词教学无定 / 屈 涛 顾美花
- 阅读教学的重要任务是培育“读者” / 马燕萍
- 自主阅读评价的策略 / 张金平 孙孝军
- 语文新教材:爱你真的不容易 / 张兰芬
- 美如歌声不胜收 / 刘小华
- 吹毛求疵《伤仲永》 / 赵东明
- 鲁庄公形象新探 / 吴 奇
- “郎诚见完与恩”的句式特点之我见 / 杜燕君
- 绚丽的图画 伟大的乐章 / 马玉萍
- 《荷塘月色》写景艺术中的摄影技巧 / 杨新华
- “烛之武”的“之”何解 / 吴美华
- 从《归去来兮辞》看中国文人的归隐情结 / 钟伟建
- 《师说》的比较句式 / 项正文
- 一字未宜忽 语语悟其神 / 田永生
- 《琵琶行》注解商兑 / 蔡桂忠
- “膑脚”“断足”语焉不详 / 凌会杰
- 古诗文备课札记 / 曹伯高 钱吕明
- 新课标背景下作文评价体系探微 / 王 冰
- “真实的作文”是中学写作教学的出路 / 蒋旭霞
- 新课程理念下的作文批改 / 于海生 张艳华
- 文学描写中的“妙喻连珠” / 陈元勋
- 简说巧拟作文标题 / 王凤燕
- 高考作文中的“感情真挚”透视 / 马怀民
- 文学名著列入考试范围的意义和对策 / 曹传秀 张美杰
- 常见的古典诗歌意象解析 / 柯贞云
- 是“主谓句”还是“紧缩复句” / 赵伟波 刘跃平
- 比喻辞格的二极走向 / 徐红旗
- “叫板”新义浅说 / 顾正龙
- “无独有偶”应“多用于贬义” / 席欣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