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大语文论坛 2009年第6期
ID: 135325
中学语文·大语文论坛 2009年第6期
ID: 135325
浓妆淡抹总关情
◇ 魏毅德
【摘 要】读《边城》,每每生出无言的感动。张爱玲说“人生是一袭华美的袍,里面布满虱子”,大约是指在人生的风光、体面背后,其实有许多折磨我们心灵的噬咬的痛苦,而在沈从文这里,人生的悲竟是从人性之善中生出来的,这悲便显得尤其伤感了。是什么样的经历使得作者能挖掘出一段与他所处的时代迥异的人生风景,这段风景中又是什么使我们心生怜惜、感动!作者试图通过大量相关资料,给自己的感动一个详尽的答复。
【关键词】沈从文 《边城》 人性 课堂教学
教《边城》,不是第一次了,讲台下的学生换了几拨,于我而言,则是一次次被吸引和打动的过程,品读文字,看看电影,想想现实,浓浓的情,深深的爱,淡淡的悲……在其优美伤感而又散淡从容的描述背后,总有一些东西让我沉吟许久,生出些许久违了的感动。我也时常想,是什么样的性格、气质以及人生经历使得作者能挖掘出一段与他所处的时代迥异的人生风景,这段风景中又是什么使我们心生怜惜、感动!假期里,我翻阅了许多资料,试图寻找更多的东西,以下便是我的所思所得。
一、排解与弥补之情
《边城》完成于1934年4月19日,关于它的创作动机,作者说:
“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得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
从作者的创作动机看,这是“愚夫俗子”的哀乐,是为“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可见,文章是作者对真情真爱的阐释,这真情真爱,不仅是爱情,而且超越爱情,涉及到人类最广阔的“爱”;尽管这真情真爱发生在如诗如画的湘西,充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返璞归真的牧歌情调,但它却是悲凉的,充满了诗意的悲凉。为何真情真爱却如此悲凉,在“人性美”“人性皆善”的背后却隐伏着悲痛,对此解读的大方之家是很多的,但都与一“情”字是分不开的。也许抛开当时的评论和沈从文应对评论的文字,看看他在其它文字里的流露和情感,更能说明问题。
为了纪念结婚三周年,沈从文于1936年创作了一篇小说《主妇》。它主要写女主人公碧碧和丈夫“他”在结婚三周年纪念日回味婚后生活时的“情绪散步”。新婚时的热闹,婚后由于两人生活习惯全不相同,“欢喜同负气”的琐碎小家庭生活,她便尽力去适应,但她渐渐发现他对她的那点“惊讶”“狂热”,“好象被日常生活在腐蚀,越来越少”。他呢?知道自己“热爱人生富于幻想忽略实际”的性格在家庭生活里形成的毛病,早在预备结婚时就有意识地“转移嗜好”,试图通过收集各种小古玩,“制止个人幻想的发展”,尽可能增加一点家庭幸福。夫妇双方相互调整的努力,往往“力所不及”,再加上“意料以外的情形”的发生,因而在“种下了快乐种子”的同时,“收获了些痛苦果实”。男主人公三年来,情感上经常与那个“意外”作斗争,使他总是想着这样的问题:一个心头上的微风,吹到另外一个人生活里去时,是偶然还是必然?人生的理想,是情感的节制恰到好处,还是情感的放肆无边无涯?生命的取与,是昨天的好,当前的好,还是明天的好?当他“想起一个贴身的她”时,还是觉得应该“贴于实际”,不能老在“幻想”中生活。小说写到结尾处,男主人公仍然没有完全摆脱矛盾:“愿意如她所希望的‘完全属于她’,可是不知道如何一来,就能够完全属于她。”
这篇小说显然是以沈从文结婚前后一段生活为原型,他也经历了像男主人公那样的感情起伏和变迁,从翠翠的这一最成功的人物形象就可看出,历来认为翠翠的形象有三个来源。
一是泸溪县绒线铺的女子。
我写《边城》故事时,弄渡船的外孙女,明慧温柔的品性,就从那绒线铺小女孩印象得来。(《湘行散记·老伴》)
一个是在青岛崂山看到的女孩子。
故事上的人物,一面从一年前在青岛崂山北九水看到的一个乡村女子,取得生活的必然……(《水云》)
另一个来源就是太太张兆和。
一面就用身边新妇作范本,取得性格上的朴素式样。(《水云》)
但从其余的作品与文字来看,远不止这三个,还有许多类似的湘西少女以及后来邂逅的“偶然”(因为有些女孩子是偶然相逢,所以沈从文后来在回忆文章中把这样偶然出现的异性,均以“偶然”相称)纷至沓来;还有那个在芷江县使他一见钟情的马姓朋友的姊姊,虽说结果受骗上当,但初恋之情毕竟深深刻印在心坎上;还有那个糖坊的女儿,因为爱她,日后竟养成了爱吃糖的习惯;还有青岛海边所遇到的那个使他产生一刹而逝的微妙感觉的黄衣女郎;还有北平掀起他情感波澜的一个又一个“偶然”……
怎样解决这个令人烦恼的冲突?沈从文也曾像《主妇》中的“他”一样,试图将精力转移到收集许多容易破碎的古陶旧瓷上面,以稳定平衡那奔放的生命,那起了波澜的心灵,然而,这还是消灭不了因结识“偶然”而产生的种种幻想,即使幸福的婚姻也不能中和它,消解它。
“换言之,即完美爱情生活并不能调整我的生命,还要用一种温柔的笔调来写爱情,写那种和我目前生活完全相反,然而与我过去情感又十分相近的牧歌,方可望使生命得到平衡。”
他想通过创作,编造传奇性白日梦,让其宣泄和升华。他要将这些“偶然”性格中种种富于人性美的素朴式样,铸到小说主人公身上,让整个故事充满了“善”,但又因一些不凑巧,使素朴的善终而演化为悲剧的结局。
故事线索逐渐清晰了,人物轮廓逐渐明朗了,开笔的条件均已成熟,于是,在五月端阳前后的斜风细雨以及六月中夏雨欲来时闷人的热,和闷热中的寂寞,展开了翠翠和她的亲人、爱人之间的悲欢离合。沈从文毫不讳言,只有如此构思,才能缓解他心中的“情结”,他说:
“这一来,我的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在这个不幸故事上,才得到了排泄与弥补。”
故事写到最后,他原拟让翠翠在人群中更经历些酸辛,但作为第一个读者的家中亲人不同意,所以他采取了较缓和的结局:“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让翠翠用“等下去”的办法打发日子去了。
于是,沈从文的深情便在《边城》里得到了排解与弥补,困扰了他几十年的情,几十年浮在空中的“幻想”,在《边城》中有了“生活的实际”。
二、乡土风情
作者写《边城》时,已经在好几地方生活过,也走过许多地方,但仍忘不了他的故乡——凤凰县。1932年的中篇小说《凤子》中曾经描述过:
……试将那个用粗糙而坚实巨大石头砌成的圆城作为中心,向四方异开,围绕了这边疆僻地孤城,约有五百左右的碉堡,二百左右的营汛。……
地方东南四十里接近大河,一道河流肥活了平衍的两岸,多米,多橘柚。西北二十里后,即已渐入高原,近抵苗乡,万山重叠。……
以后,凡介绍到自己故乡时,沈从文又反复称引上述文字,因为“这虽然只是一个轮廓,但那地方一切情景,却浮凸起来,仿佛可用手去摸触”。由此可以看出沈从文对故乡的熟悉程度,在《边城》里也随处可见,如文章的开头: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
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小溪流下去,绕山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的大河。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则只一里路就到了茶峒城边。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小溪既为川湘来往孔道,水常有涨落,限于财力不能搭桥,就安排了一只方头渡船。这渡船一次连人带马,约可以载二十位搭客过河,人数多时则反复来去。渡船头竖了一枝小小竹竿,挂着一个可以活动的铁环,溪岸两端水槽牵了一段废缆,有人过渡时,把铁环挂在废缆上,船上人就引手攀缘那条缆索,慢慢的牵船过对岸去。船将拢岸了,管理这渡船的,一面口中嚷着“慢点慢点”,自己霍的跃上了岸,拉着铁环,于是人货牛马全上了岸,翻过小山不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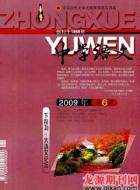
- 把学生学习的权利还给学生 / 赵维政 徐庆美
- 中学生语文的学习现状与思考 / 张 英
- 和青年教师谈课程改革 / 徐绍兰 张 华
- 在语文教学中提高文学素质 / 苏承伟
- 别让德育目标成为语文教学的空白 / 朱安荣
- 转变教师角色,创新语文课堂教学 / 何良辉
- 语文学习需要哪些良好习惯? / 单新萍
- 为有枝头“暗香”来 / 毛 丽
- 语法一片天 / 赵梅花
- 浅谈新课标下学生阅读“嗜好”的培养 / 魏陈荣
- 对语文教学行为正当有效的几个追求 / 陈仲刘
- 备好情 / 王志杰
- 如何让学生在语文课中兴趣盎然 / 李海霞
- 浅谈新课程背景下语文教学中的情感因素 / 龚海平
- 用培育观指导中学语文训练 / 方梦龙
- 如何引导学生发现问题 / 邰雨春
- 论语文教学中口语交际能力的培养 / 周廷彪
- 新课标下的语文课堂教学艺术摭谈 / 磨玉荣
- 新课程高中语文教学中的思维训练 / 胡建伟
- 自主探究教学必须注重的“六性” / 马 坚
- 教学设计应注意的四方面问题 / 邢作庆
- 立足文 / 张又斌
- 语文的发现学习与接受学习 / 谢秋晓
- 语文教学如何选择恰当的切入点 / 李林雨
- 真正美人方有一陋处 / 铁 娇
- 新课程中学生角色转变的探索 / 李凤兰
- 师生心灵沟通的方法策略 / 黄绪环
- 语文教学后记的内容与作用 / 张吉彬 胡喜顺
- 呼唤语文教学的文本回归 / 夏新国
- 此时无声胜有声 / 樊 琳
- 作文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联想能力 / 曾小萍
- 课堂教学中多媒体技术应用的错位及应对策略 / 严永庆
- 撑起心灵的一片蓝天 / 涂 萍
- 让学生习作焕发灵动之美 / 王万忠 刘 建
- 作业小天 / 李翔云
- 在比较阅读中看文学的传承 / 钱玉花
- 如何使作文意蕴深厚 / 刘 聪
- 阅读教学需要教师的开放心态 / 钱 珏
- 古代诗歌鉴赏的四维能力训练方法 / 李冬梅
- 为作文穿上靓丽的新衣裳 / 郭 军
- 关注阅读教学中学生个性发展 / 施丽光
- 凭借东风上青云 / 徐秀丽
- 教材深度开发与作文有效教学的途径 / 熊 辉
- 朗读教学与语感培养 / 范小芬
- 问世间情为何物 / 李桂华
- 咬定青山不放松,学以致用 / 葛文艺
- 新诗如何教出“新”意 / 余丽芳
- 论王家卫电影的后现代文化特征 / 赵海艳
- 例谈新材料作文审题 / 李石清
- 妙语生花,飞扬你的课堂 / 练瑜珍
- 让作文之水长清 / 彭光容
- 例证法的运用 / 赵建春
- 成长,就在每一堂课中 / 袁 彬
- 敞开思想的襟怀写作 / 孙周通
- 关于作文“静的妙处”的升格指导 / 张增杰
- 于细节中见形象 / 金海英
- 呼唤真情作文的回归 / 张平治
- 语文综合性活动教案 / 池新东 沈秋菊
- 阅读“枝头”表达“花” / 贾锋全
- 温度教学 / 李海珠
- 《声声慢》教学设计 / 黎 峰
- 弘扬祖国传统文化要从汉字抓起 / 李泉荣 李 菁
- 浓妆淡抹总关情 / 魏毅德
- 巧用红线串珍珠 / 王少娜 高崇阳
- 纯美的诗体小说——《荷花淀》 / 陈学雯
- “众人拾柴火焰高” / 赵明云
- “石头”的秘密 / 余小娟
- 于丹的成功与博士的悲哀 / 张宪哲
- 大智如愚的刘姥姥 / 于宏伟
- 新课标下语文高考备考 / 胡 杰
- 《采薇》的主题仅是思乡厌战吗? / 朱 平 姜 贺
- 《乌泥湖年谱》中的人物类型分析 / 程海燕
- 谈高三语文复习的全局意识 / 叶润峰
- 白璧微瑕 / 赵东梅
- 高考语文失误原因分类谈 / 徐 超
- 漫话“三” / 冯国亮
- 打造高考作文的“骨架美” / 周松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