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 2006年第6期
ID: 85865
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 2006年第6期
ID: 85865
屈原与荆楚文化传统
◇ 申华岑
屈原是我们中华民族可称之为“民族魂”的第一人,他执着的爱国主义精神、疾恶如仇的批判意识、坚持理想、宁死不屈的斗争意志,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进步作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国文学史上凡是有成就的作家,无不受到屈原的影响。借痛惜逝者以自悼的贾谊,以抑郁不平之气倾注于《吊屈原赋》中,在汉初“文景之治”的盛世即深谋远虑,时发忧世之言;司马迁含冤受刑之后,以“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激励自己,含辱忍诟14年,终成千古大篇,鲁迅赞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李白一生傲岸,不向权贵折腰,却深深折服于屈原:“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江上吟》);杜甫不仅继承了屈原忧国爱民的精神,他的诗歌更是努力以屈原为范,“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戏为六绝句》);陆游、辛弃疾则是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宋代的承流继响者;时至明清,吊骚、感骚、拟骚,可谓蔚然成风;五四时期的文化先驱们,将屈原的爱国主义情怀自觉地转化为国家兴亡的使命,鲁迅以“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屈原式诗句,作为自己为祖国为民族而奋斗的宣言书;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在名剧《屈原》中,把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表现得气势磅礴,淋漓尽致,在广大中华同胞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诚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盛赞的那样“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也许缘于上述的原因,屈原自沉清流的爱国壮举更多是停留在政治层面上的诠释,屈原昭示后人的典范人格中的民族文化底蕴,却因此被忽略淡化了,从而使屈原高高地站在神坛之上。事实上,一个最伟大的人格离不开民族文化的滋养,也只有他最充分的体现了民族文化精神,才可称之为一个民族的灵魂。班固谓:“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他注意到了地理环境对民族性格的影响关系。本文试从屈原的性格形成和荆楚地域文化关系上,解读屈原怀石自沉、以死殉国的伟大人格之地域文化因素。
一、楚人的艰难创业史和执著进取、九死不悔的民族精神
楚,古国名,是我国先秦时代最有悠久历史的古老国家之一,楚贵族为芈姓,始祖鬻熊,源于中原的祝融部落。他们在夏商时期往南方迁徙,一直到周代初年,鬻熊重孙熊绎被周成王封于 “楚蛮”之地,楚人才得以安身,然仅有方圆百里。环楚各国占尽了良田沃土,楚人被蜷缩在山地与平原之间,崇山峻岭,荆棘丛生,地僻民贫,其地理自然条件比中原地区具有更大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文献记载的“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则是早期楚君疲于奔命的生动写照。《左传》记载楚灵王时右尹子革的话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赴草莽。”筚路蓝缕的苦志,正是荆楚文化兴起的原动力。《晋书》载:“?冒以筚路蓝缕,用张楚国。”熊绎时代约为公元前一千年,从熊绎到?冒,前后约二百多年,筚路蓝缕的精神一直贯穿其间;从熊绎到灵王,前后约四百多年,楚国的臣民依然缅怀筚路蓝缕的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支撑下,楚国由一个古老氏族的百里小国,发展为强盛的奴隶制王国,又发展为广大的封建制王国。它疆域广袤,整个南中国到处有楚国军队的军旗飘扬,其最远所至,东到大海,北达黄河,南据洞庭苍梧,向西抵达滇池;它声威日彰,跻身春秋五霸,名列战国七雄;它光辉广被,成为南国文化的集中代表。究其因,楚人的血液中有熊绎、若敖、?冒筚路蓝缕、拓拔草莽的韧性精神的因子,使楚人具有励精图治、发奋自强、执着进取、顽强勇敢、坚忍不拔的基本精神。楚民族的这种气质和性格,在屈原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
屈原生活在战国后期诸侯各国争斗最为激烈的时代。诸国之中,秦、楚、齐的实力最为强大,当时“纵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战国策·楚策一》)的政治格局,对楚国来说,既是严峻危急的,又是一个实现北定中原统一中国的良好机遇。屈原从宗族感情和政治家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出发,主张内修法度,联齐抗秦,然而屈原出色的政治才能,遭到以上官大夫、靳尚、子兰之流为首的亲秦派的嫉恨;所提出的“举贤授能,循绳墨不颇”的政治措施又侵害了贵族大臣的利益,为保护集团私利,他们从中百般阻挠、千方破坏;怀王、襄王又都昏聩不明,听信谗言,疏远和放逐屈原。就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政治环境下,屈原仍不放弃他的“美政”理想而苦苦追求:“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这正是他坚定地追寻理想、九死不悔精神的表白。览阅楚人历史,不难发现持有这种精神的个体,并非屈原一人。卞和不惜两次刖足献玉的执著精神是楚人韧性刚毅的写真。这个故事最早见于《韩非子·和氏》篇,韩非是战国后期人,楚人和氏当为春秋初年人氏或出生于西周末年至春秋初年。博闻强记的屈原一定知道卞和其人其事,赤诚为国之心与执著献宝之举相得益彰,可见,这是楚人的民族根性所至。
古来史家往往把楚民族这一刚勇执著进取的性格气质和荆楚的“荆”字联系在一起。“荆”就是这种基本精神的代名词。扬雄就说:“包楚与荆,风飘以悍,气锐以刚,有道后服,无道先强。”《晋书》曰:“荆,强也。言其气燥强。亦曰警也,言南蛮数为寇叛,其人有道后服,无道先强,常警备也。”可见楚人性格基本精神中的“悍、强、刚、劲”是历来都公认的。
二、爱国情怀与国殇精神
爱国主义作为民族的最高情感深埋在楚人的民族性格和民族传统这一片沃腴的土壤里,尤其是在民族危亡、事关国家荣辱的抉择面前,楚人从君臣到百姓,无不表现出以国家利益荣辱为重,轻个人生死得失的大胸襟、大气魄。
楚之臣大都视国家的荣誉,高于个人的生死。如有覆军之败,往往自尽以谢国人。虽贵为公子王孙,位至令尹、司马,也很少偷生。楚康王时,令尹襄为吴师所败,引军自还,自尽于途中,临终之际嘱咐子庚一定要修筑郢城。
楚之君也很以社稷为重,较为平庸以至昏聩的楚君,也不敢做丧权辱国之事。楚共王有鄢陵之败,临终前要求大夫在他死后加上“灵”或“厉”的恶谥。暴虐的楚灵王听到政变发生的消息,惶然不知所从,右尹子革建议他逃亡别国,他拒绝并说这样只会自找没趣,竟只身走向郢都中途自缢。昏庸如楚怀王,遭秦国软禁,宁客死他乡也不肯以捐弃国土为代价换取一己自由。仅凭这一点,他赢得了几代楚人的怀念,以致秦末起义楚人拥立的楚王仍称怀王。在爱国的天平上,楚人表现出了惊人的贵贱平等。既使是国君,一旦刚愎自用,不听谏诤而致战争失利,臣下也可加以惩罚。《左传》庄公十九年:“十九年春,楚子御之(指御巴人伐楚之师)大败于津。还,鬻拳(楚主管城门者)弗纳,遂伐黄。败黄师与?陵。还,及三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诸夕室。亦自杀也,而葬于经皇。”只有君臣都置根于对社稷江山的钟爱挚恋土壤中,才会有如此的悲壮之举。
楚之民的爱国事迹更是一篇篇可歌可泣、动地惊天的书写不尽的诗章。不妨择其一例,在秦楚的最后决战中,公元前278年春,秦将白起率最强悍的兵力攻陷楚都郢城,他们万没有想到他得到的是一座空城。在这场巨变中,楚人有逃亡和战死的,却没有一个投敌献媚的,受伤被俘的两名士兵也选择了火堆和嚼断舌根不肯泄露楚钟鼎鬲樽的埋藏地点。楚人留下了不朽的精神: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在楚民族的文化土壤里生长起来的屈原,亲闻、亲见、亲历了这桩桩件件。他的楚辞“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便是适应楚民族这种爱国思想和民族精神的需要,与其说屈原作楚辞以抒爱国情怀,不如说是楚辞体现、张扬了屈原和楚人强烈的民族意识。
[##]
《橘颂》以橘为象征表现了这位时代歌手高尚的人格和眷恋乡土热爱祖国的情感。“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是何等坚定执著;诗人在流放途中听到秦将白起攻破郢都而写的《哀郢》,对祖国的一腔苦恋无尽悼怀,最终化作“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的生死相守。《离骚》更是多方面多角度地倾诉了祖国之恋。“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个人的生死安危都置之度外而寸心只念江山社稷。他痛斥把祖国引向危亡绝境的贵族群小蝇营狗苟:“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他向往太阳的光明,因为浓烈的政治感情和深沉的爱国情怀,一如太阳火热光明,在那里才能实现他的理想。然而“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之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远游的自在终不能使他忘怀于祖国,这感情是何等缠绵缱绻,心境是何等忧苦哀伤。仅此四句便可成为千古怀国之绝唱,《离骚》主题意义正在此。忠君爱国是屈原人格的中轴,他以诗人的童心描画楚国的未来,以恋人的热忱拥抱父母之邦,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革楚国的政治,让自己的美政理想,把楚国导向光明和强盛。但是现实衰败,国运凌夷,圆凿方枘,他的生命只能在沅湘之间游弋蹉跎。面对理想的泯灭,屈原没有选择出走,宁可“从彭咸之所居”而自沉清流。这是一个思与行的大者与强者,献给祖国的最后一次心跳,也是一个普通的楚人以一种最普通而又最悲壮的方式,唱给祖国的情歌。读屈原的作品,最使人激动不已的不是那奇幻谲诡的想象和伟岸新奇的文词,而是诗人那浩然于天地间的一片爱国赤忱。其事之真,楚人楚事;其情之美,楚声楚调,这是形成楚辞民族精神的最基本的一个特色。而这种特色不是文学家的天才创造,而是荆楚之人的一种民族魂——国殇精神。屈原在《国殇》里讴歌:“出不入兮往不返,平原忽兮路超远。带长铗兮挟秦弓,首虽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屈原自沉清流便是国殇精神的履践。
以荆楚精神为内在晶核的荆楚文化,是一种有特质的地域性文化。地域性的文化总得从地域性的江山之助及其相应的社会关系中去找寻文化生成的内在依据。本文的分析力图体现这样的意图。所揭示的荆楚文化蕴涵的基本精神,不仅充溢着荆楚人民的生命热忱,同样也流淌着整个华夏民族的一泓生命意识。正是这种博大的生命精神,组成了卓异光华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她又以文化遗传的基因、民族热血的形式传留和奔涌于今日的中华儿女的血脉里。
单位:河南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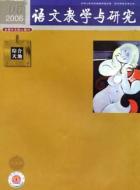
- 校苑竞 / 钟克云 生昀慕
- 叩问心魂 / 刘道生
- 聂海胜来到咱五中 / 刘道德
- 《孔乙己》中笑的艺术 / 许建辉
- 例谈现当代诗歌的鉴赏 / 安 迪
- 古诗词中“流水”意象的意蕴 / 曾春文
- 浅析鲁迅作品的语言特色 / 葛忠明
- 《秋颂》对生命永恒的感悟 / 王锡明 吴瑞雪
- 散文意境漫说 / 苏 虹
- 陋室·丝竹·琴 / 赵剑华
- 浅谈教育恐怖 / 杜新峰
- 中国皇帝称谓知多少 / 孙荣峡
- 新课标对青年教师的要求 / 周 波
- 人文教育中语文教师之我见 / 梁晓枫
- 如何做好新时代的教师 / 吴 宝
- 教师自我心灵调适与现代教育 / 杨 永
- 语文课应有语文味 / 靳晓慧
- 屈原与荆楚文化传统 / 申华岑
- 庄子生命观念解析 / 黄 萍
- 材料作文拟题漫谈 / 李建军
- 高考议论文写作技巧 / 邵宝平
- 综合性学习中的教师角色 / 吕晨铃 兰海燕
- 语文教学中的素质教育略谈 / 张云焕
- 《逍遥游》中一处标点质疑 / 姜志芳
- 新型师生关系谈 / 邓齐平 谭友芝
- 学生自评自改作文的意义 / 杨中明
- 语文早读思维浅探 / 任伟栋
- 论《语文课程标准》的人文性 / 于友栋
- 语文教学与爱情观教育 / 袁 泉
- 教师在“生生对话”中的角色定位 / 舒琼琳
- 呼应错杂的“丫叉句法” / 任根娥
- 这样的“借题发挥”要不得 / 杨守才
- 《报任安书》的悲壮情怀 / 孙怀永
- 《归去来兮辞》的儒道合一 / 郑 忠
- 试析《故乡》中的“我” / 康志林
- 《项脊轩志》“悲”“喜”谈 / 付 煜
- 三处“下棋”该怎么理解 / 白中生
- 巧构妙思的《琵琶行》 / 孙斌华
- 《巴尔扎克葬词》难句试解 / 许瑞祥
- 《西洲曲》在《荷塘月色》中的媒介意义 / 刘绪君
- 《在海边》教学案例 / 邓明箐
- 《黄鹂》说课设计 / 宋建军
- 古诗词中的倒喻例谈 / 刘党桦 李金明
- 论音节j / 胡明晓
- 浅谈量词的修辞功能 / 闪明琴
- 略谈语文课的引入艺术 / 余建雄
- 让诵读成为课堂亮丽的风景 / 沈丽娅
- 如何在课堂上进行文学鉴赏 / 梁 燕
- 创设情 / 付彩霞
- 语文课堂教师点评的误区及原因 / 李国云
- 链接训练是课堂教学的重要手段 / 张家鑫
- 浅谈课堂教学的互动艺术 / 于中波
- 语文课堂激趣例谈 / 唐诗东
- 教师在课堂上应善于倾听 / 高凤琴
- 对课堂教学中“讲”的再认识 / 丁卫军
- 让艺术走进语文课堂 / 胡维汉 曹雪梅
- 话题作文创新的两个层面 / 周多权
- 感受生活与文章写作 / 肖 平
- 中学生作文创新意识的培养 / 梁 平
- 高中生作文如何创新 / 周 杰 徐 升
- 作文批改中的激励机制 / 黄真斌 陈兆进
- 作文选材“三要” / 王 平
- 如何实现作文教学的飞跃 / 沈春萍
- 作文批改要师生互动 / 郭安贵 潘正清
- 作文教学与学生健康人格的培养 / 周远明
- 论史书的“尚实”与“虚构” / 王福山 王文才
- 新课标视野下的鲁迅小说教学 / 张家胜
- 课外阅读的引导艺术 / 金复耕
- 文本与对话 / 王 英
- 在阅读教学中引导学生思考 / 谢 琼
- 浏览方法四种 / 杜先宁
- 中学生课外阅读的价值取向 / 许安保 贾丽青
- 如何提高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 / 高雪梅
- 文言文教学三法 / 杨 君
- 在语文教学中渗透思想教育 / 马伟平
- 如何记课后记钟脆玲 / 钟脆鸣
- 语文教学要以读促写 / 冷翠红
- 大学语文表演法略谈 / 李东方
- 教学中如何开启学生思维 / 陆瑞林
- 词汇积累方法三种 / 任永红
- 让学生思想长出来 / 马晓英
- 挖掘文本中的人文思想 / 曹旭亚
- 教学中如何开展语文活动 / 刘彩青
- 文本教学中的作者介绍 / 梁修红
- 初中语文教学应渗透美育 / 王帮军
- 如何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 刘小利
- 在训练中提高学生素质 / 黄 勇
- 语文活动课的关键在“动” / 张晓莲
- 让网络走进语文教学 / 应培玲
- 语文教学中的人格建构 / 李爱玲
- 语文教学与心理健康教育 / 刘锦芳
- 如何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 / 钱晓灵
- 在探究中学习新课程 / 陈碧玉
- 语文个性化作业的指导与设计 / 白国雄
- 人本主义心理学与语文教学改革 / 饶红涛
- 构建新的语文学习方式 / 许书明
- 文学理论教学改革方向刍论 / 池永文
- 田园童话 / 艾 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