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08年第1期
ID: 82787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08年第1期
ID: 82787
文学写作与艺术虚构
◇ 叶 乔
王安忆,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复旦大学教授。小说代表作有《雨,沙沙沙》、《小鲍庄》、《荒山之恋》、《神圣祭坛》、《乌托邦诗篇》、《69届初中生》、《米尼》、《纪实与虚构》、《长恨歌》等。先后获过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
问者:王安忆老师,您曾在纽约大学东亚系作过一次题为《虚构与非虚构》的演讲,在演讲中,您特别强调了虚构对于文学写作的重要性。今天,我想请您对广大的中学语文教师谈谈虚构与文学写作的有关问题。
答者:好的,我可以谈谈什么是虚构。在说清虚构之前,我先说说什么是非虚构。非虚构实际上就是真实地发生的事实。比如上海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在淮海路最热闹的路段上曾经立起一个雕像,是铜雕。这个雕像很可爱,一个女孩子在打电话。它是一个非常具象的雕像,女孩子姿态很美,而且她是在一个非常热闹繁华的街头打电话,熙来攘往的人群从它身边走过,很是亲切。这个雕像,大家都非常喜欢,可是有一个晚上它不翼而飞,不见了。不见了以后,当然要破案,出动了警察。我非常关心它的下落,我在想,谁会要这个雕像呢?会不会是一个艺术家,把它搬到自己的画室里去了;甚至于我还想,会不会忽然有一个电话亭也在一夜之间不翼而飞,被这个艺术家搬到了他的画室,成为一个组合。可是事情没有这么发生,过了一年以后,破案有了结果。原来它是被几个农民工搬走了,用焊割的方法拆下来搬走了,当成铜材去卖,并且很残酷的,把它的头割下来了,因为他们必须把它切成一段段才好销赃。我看了新闻之后,终于知道了这个少女的下落,感到非常扫兴。看起来,艺术还是要到艺术里去找。生活不会给你提供艺术,生活提供的只能是这么一个扫兴的结果,一个不完整的故事。
上面这个故事就是非虚构。生活中确实在发生着的事情,波澜不惊,但它确实是在进行。可它进行的步骤,几乎很难看到痕迹,很难引起我们的注意。这就是我们现实的状态,就是非虚构。非虚构的东西是这样一个自然的状态,它发生的时间特别漫长,特别无序,我们也许没有福分看到结局。或者看到结局却看不到过程中的意义,我们只能攫取它的一个片断,我们的一生只在一个周期的一小段上。现在,我就试图回答一下,什么是虚构?虚构就是在一个漫长的、无秩序的时间里,要攫取一段,这一段正好是完整的。当然不可能“正好是完整的”,所以“攫取”这个词应该换成“创造”,就是你,一个生活在局部里的人,狂妄到要去创造一个完整的周期。
问者:那么,请问王安忆老师,虚构与非虚构的主要区别在哪里呢?
答者:虚构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形式。刚才我说的这个故事,它是缺乏形式的。因为没有形式,所以它呈现出没有结尾,没有过程,总之是不完整的自然形态,虚构却是有形式的,这个形式就是从它被讲述的方式上得来的。我举一个例子,苏童写有一个小说,名字叫《西瓜船》。写的是某一个水乡小镇,水网密布,有很多河道,在河道上面常常停靠着一些进行农业贸易的船,卖瓜、卖鱼什么的,岸上的居民就向船上的农人做一些买卖。这一日,一个卖西瓜的青年,撑了一船西瓜来到这里,就像通常发生的那样,他和来买瓜的一个青年发生了纠纷,两个人都是血气方刚,容易冲动,就打起来了。岸上的这一位呢,手里拿着家伙,船上的这一位就被他捅死了。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但是这样的故事依然是常见的。然后派出所来处理。死的那个办理后事,活的那个则判刑入狱,激烈的场面过去之后,小镇又回复到平静的日常生活。事情好像慢慢的就这样过去了,如果小说到这儿就结束的话,那么就是非虚构。可苏童接下来开始虚构了。过了若干天以后,这个镇上来了一个女人,一个乡下女人。这个乡下女人是来找她儿子的西瓜船。她找的过程是这样的:她挨家挨户去问询,我儿子的西瓜船在哪里?人们这才想起那死去的青年的西瓜船。在那一场混乱中,西瓜船不知道去了哪里!于是人们开始帮着女人去找船。找到居委会,找到派出所,有人提供线索,又有人推荐知情者,越来越多的人聚在一起,陪同女人寻找西瓜船,最后顺着河流越走越远,终于找到尽头,那里有一个小小的废旧的工厂,在那工厂的小码头上看到了这条搁浅的船。西瓜已经没有了,船也弄得很破很脏,大家合力把这个西瓜船拖了出来,小镇居民送女人上了船,看着这个乡下女人摇着橹走远了。苏童写小说往往是这样的,前面你不知道他是什么用意,直到最后的这一瞬间,前面的铺排一下子呈现意义了。这时候你会觉得,这一个女人,分明就是摇着她儿子的摇篮,但是一个空摇篮,回去了,而这些站在岸上目送她的人,则是代表这个小城向她表示忏悔。这就是形式,从意义里生发出的形式,又反过来阐述意义,有了它,普遍性的日常生活才成为审美。非虚构的东西,它有一种现成性,它已经发生了,人们基本是顺从它的安排,几乎是无条件地接受它,承认它,对它的意义要求不太高。于是,它便放弃了创造形式的劳动,也无法产生后来的意义。当我们进入了它的自然形态的逻辑,渐渐地,不知不觉中,我们其实从审美的领域又潜回到日常生活的普遍性。
问者:我还想问王安忆老师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虚构?或者说,文学写作为什么离不开虚构?
答者:我想用一句简单的话来回答你,我觉得,非虚构是告诉我们生活是什么样的,而虚构则是告诉我们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我觉得现代人的要知道“生活是什么样的”热情,是有很大力量推动的。其中纪录片是一个很大推动的。将生活如此肖真地写下来,就像我前面所说的,对事实无条件的信任,它已经发生了,它就是合理的,我们完全可以抱驯从的态度,而事实上“生活是什么样的”,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在上海最早的纪录片中,有一部很著名的纪录片叫《毛毛告状》,它说的是上海发生的一个故事。这类故事人们从报纸上看到很多,传言中也听到很多,唯有这一个是用影像的方式。它讲湖南农村的一个小姑娘,到上海谋生计,和一个社会底层的、腿有残疾的、无业的、单身的上海青年同居了,又因为种种琐事两人关系发生变故,就崩了。女孩子回到乡下以后,却生下了他们的孩子,这个孩子叫毛毛。她抱着毛毛又一次跑到上海,就要找这个青年,要他认孩子。青年很愤怒,认为女孩是栽赃他,因为他不相信自己有生育能力,他也不相信女孩的忠贞,他是一个自卑的人,他咬定女孩是瞎说。这种故事是常见的城市故事,是家长里短的闲篇,可是人们第一次在屏幕上看到当事人的形象。这个女孩子很倔强,长得很瘦小,大热天抱着她的胖胖的婴儿在烈日底下奔波。这个青年呢,腿有残疾,长的样子呢也还端正。理直气壮的争吵,耍赖,说一些非常绝情的话。一切都变得那么生动和具体。这个女孩子很厉害,把他告上法庭,女孩子在法庭上的表现很有性格,全然不是传统表现中的温顺隐忍的乡村女性,她一点不退让,说这个孩子就是你的,然后做亲子鉴定。当亲子鉴定的结果出来以后,孩子果然是男方的,于是判决男方承担抚养费,接着出现了一个场面。青年一直沉默着,女孩抱着孩子一直哭,非常委屈。这时候制作片子的导演,一个中年妇女,来到男青年跟前跟他说了一句话,她没有说,你服不服?或者你还有什么可说的,而是说,做爸爸了,高兴么?非常体贴的一句话。真是人情百态,全在眼前。这部电视片故事分上下集在两个晚上播放,可说是万人空巷。就这样,大家看到了生活当中如此真实的一个场面,出奇制胜之处在于这是真实发生的,就在我们身边,是你我他中间的一对男女,它彻底地写实,比现实主义创作更加现实主义,它一下子把所有人都征服了。所以说,“生活是什么样的”确实也是一个好问题,尽管是现实的存在,但其中确有很多隐秘是人们并不了解的,我们很有必要去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而事情的发生有时候超乎了我们的想象力。这确实突破了我们的很多概念,这也是非虚构的价值所在,生活总是不断产生新课题,需要我们不断地去认识。可它终究只是生活的一个复制,不能提供一个更高级的、更加振作的生活情景。我还是想正面地描绘一下“生活应该什么样的”,换一种说法就是,我们做虚构的人所以要去做的目的是什么?我这里举《断背山》的例子。我看了《断背山》电影以后,觉得蛮失望的,因为我是先看的小说。看了小说以后,觉得这个小说真的写得非常非常的好。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看到这样不真实的小说,这些年来,我所看到的小说都太真实。它是很不真实的,我为什么说它不真实?它是写两个男子之间的情感,但是它一点都不想回答一个问题,同性恋是什么?小说一点儿都没有这个企图去回答这个现实的问题。你看她怎么描写这两个男子之间的情感,他们的情感发生在一个天气非常恶劣、地理环境也非常恶劣蛮荒的背景之下,他们两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总是让我们注意到那些非常笨重的皮靴,又厚又硬的牛仔布的裤子,布料,皮带上的铜扣,暗夜里马口铁的闪光。特别重,特别重。然后他们俩分别好多年以后重逢,他们拥抱亲吻,那么多的唾液,身体或者衣服摩擦的粗重的声音,他们两人在小屋子里做爱,房间里发出马粪的气味,精液的气味,烟草和烈酒的气味,都是很有重力感的东西。它也写到了其中一个牛仔和妻子的做爱,用了这样的词汇,稀软的意思,肌肤像水一样稀软。实际上小说一点都不想告诉人们同性恋是怎么回事,它只是想告诉人们一个很重的,含量很大很大的情感,这种超体量的感情必须由两个物质感特别强的生物来承担。这就是“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而电影太甜美了。两个演员那么俊俏,是典型的酒吧里的Gay,电影中断背山的风景是如此的明媚,两个人在山上奔跑则很轻盈,它又把它拉回到一个同性恋的话题上,而小说给你的不是一个同性恋的话题,根本和性别没有关系。它要创造一种特别有体量的爱情。这个有体量的爱情就需要两个人都是重量级的,从身体到情感,都要很强劲,然后是不可解决的压力,全社会都对你们说不可以,绝对不可以!不是今天,必须在1960年代,同性恋会被人,甚至自己的亲人,活活打死。所以我觉得小说是在创造一种含量特别重的爱情。这个爱情让我再推回去看的话,它还出现在一部作品里,就是《呼啸山庄》。《呼啸山庄》里的那一对男女之间发生的并不是爱情,自然的力量是那么强,它必须选择最强悍的生命来担任它的对抗。这就是对爱情的最高想象,爱情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想象。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去虚构的原因。
[##]
问者:您在美国讲学时,曾经提到沈从文和老舍的写作不同,似乎认为沈从文的境界更高,而老舍相比起来,更像是普通人的生活。按照您的说法,老舍的写作的确是在告诉我们生活是什么样的,而沈从文是告诉我们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俩的写作确实是非常不一样的。
答者:我是觉得,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写的真是好。我常常觉得,资产阶级是一个对艺术很损害的阶层,它们创造了过于丰富的物质生活,而使精神价值贬抑,但是它们对艺术有一个贡献,就是批判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主义,它把“生活是什么样的”挖掘的很深。回到《骆驼祥子》,它不是在说祥子如何受盘剥,遭受不公正的命运,而是在讲一个劳动者是如何走向堕落的,这个社会是如何毁灭一个健康的灵魂。我记得很清楚,当时的一个老导演谈拍摄《骆驼祥子》,演祥子的演员叫张丰毅,当时还是电影学院的学生,导演叫凌子风,他就叫“祥子”拉着洋车在北影的那个摄影棚里跑,他说你一定要跑出喜气洋洋来,很骄傲的,你那么骠,你那么有力气,而且劳动是多么快乐,你能挣钱,还能租到一部洋车,一定要跑出喜气洋洋的样子。这真是让我觉得批判现实主义的深刻,它让你看到生活表面之下是真相,真相下面还有真相,它是很有力量的。我小时候生活的环境,是由奶妈、保姆、婆婆妈妈组成的,她们有她们的文艺生活,多是说故事。她们热衷的不外乎杨乃武和小白菜,梁山伯与祝英台,在这些故事里面却有一个新文艺的故事,就是祥林嫂。她们很喜欢讲祥林嫂的故事。我从小听她们讲祥林嫂的故事,我听到的是一个非常不幸的寡妇,嫁了两个男人,将来到了阴间会被锯成两半,分给两个男人一人一半,于是她就到庙里面去捐门槛,别人却还是不能够原谅她,觉得她不干净,一个阴惨的故事。等到我自己读鲁迅的小说的时候,我大吃一惊,原来其中有那么强烈的启蒙意识,对祥林嫂是那么的不满意,不满意她的不觉悟。这就是批判现实主义,它把生活的真相一层层的揭示给我们看,看到了底处。但这个主义的局限性也是在这儿,它只破不立,最后没有创造出另外一个世界。我觉得艺术就是要有另外的空间,在那里很多不真实的东西都变成真实的了。
问者:文学写作要求虚构,是不是就是要用虚构来进行创造,创造一个与现实生活不同的世界,以此来告诉我们“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
答者:是的,我们要虚构要创造的那个东西是我们满意的,但又不是真实的,但又要用真实生活的逻辑去创造它。不过这很难做到,只有特别有生气、元气充沛的作家才能做到。我非常看好的一个作家叫迟子建。她写了一个小说叫《野炊图》。故事是这样的,在林场里有三个告状户,这三位各有各的冤情,很倔强,很执着,不屈不挠地告状。其中有一个女人,她的女儿在酒店做服务员的时候被一个官员奸污了,但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只有一条内裤,不足以证明事实,就不能惩办那官员。眼看这个女儿越来越抑郁,生活没有希望,这个母亲能做什么呢?就是掖着这条内裤到处去告状,成了告状户。还有一个告状户,是一个立过很多功的残疾人,可是他没有得到应有的养老和医疗,非常的愤怒,也是非常坚决的告状户。他的告状方式就是把他所有的奖章都别在一件旧军衣上面,穿上去告状。还有一个年轻人,他的故事小说里没有做正面描述,我们看见的是一个特别沉默的人,显然积蓄着不平的怒火。只要林场来了上一级或者再上一级的干部,他们就一定要到现场去陈诉他们的冤情。这一天,林场里来了一个省里的干部视察。领导们就很发愁,这三个人一定又要去告状,这很难看,很丢脸,而他们是不能不管不顾的。于是想了一个办法,先把省里来人的消息封锁了,然后交办给一个年轻人,一个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说,你今天负责带他们三个人上山野炊去,带上酒,吃的,开上越野车,好好招待这三个人,要把他们留在山上。年轻人就照办了,他挨个儿接他们上车,说你们受那么多委屈,我要安抚你们,然后上山了。他们三个人完全不知道为什么忽然间如此这般热情,但是风光那么迷人,酒也很醉人,小伙子那么亲切,三个人很开心,都喝醉了,东倒西歪在地上。你忽然就觉得他们这三个人就像折了翅膀的天使一样,而小伙子就是上天选定来安抚他们的手——小伙子照顾着他们,帮这个整整衣衫,帮那个摆摆身子,老年人尿了裤子,他就把尿湿的地方扯出来,好对着太阳晒干,他对他们生出了怜惜之心。当他照顾到这个女人的时候,出了一点事故,这女人已经被她丈夫冷落很久了,因为是她给女儿安排的酒店工作,出了这样的事,丈夫自然迁怒到老婆身上,这是一个非常健壮的妇女。当年轻人走到女人身边的时候,绊倒在女人身上,然后他就把女人给睡了。事后他心里很难过,觉得侵犯了女人,可是女人一直香甜地睡着。等终于睡醒了,天也晚了,他一个个把他们送回家,最后是送女人。他一直在想要不要向这个妇女做道歉,说对不起,是我喝多了。但万万没有想到,是这女人先开了口,下车的时候,她说,我喝多了。这个故事写得非常奇妙,这个男孩子觉得是他侵犯了她,结果是他安慰了她,大自然让他赠送了一个多么奇异的安慰啊!这三个受委屈的人,终于在这个野炊会上,从一个懵懂的小伙子那里得到了一些安慰。我就觉得这个作品利用的是现实生活里的条件,但是它用这些现实条件勾画的是一个我几乎可以称之为童话的东西。它告诉了我们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
问者:王安忆老师,您说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和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两者的关系怎么处理?
答者:我觉得我们可以将现实进行重新梳理和编码,相信大自然总是会选择某一类人和事来承担某种特殊的使命,让我们相信不可能是可能发生的,也许就在某一个犄角里。现代的民主社会一个要命的事情就是,把什么都平均分配了,英雄也平均分配了,所以我们就找不到英雄,眼前都是芸芸众生。可是,也许其中就隐藏着某种变相,或者变成一个精神病者,流浪者。找不到工作的人,不合群的人……我们怎么去找昔日神话中的人物呢?大概只能遍地搜集了,聚沙成塔了。北京有个作家叫刘庆邦,他写过很多短篇小说,非常好。他有个小说名叫《血劲》,写一个矿工,他的老婆对他非常粗暴,很冷淡。为什么呢?原来这个老婆还是个中学生的时候,当她看到报纸上有一篇文章说,矿工娶不到老婆,她就非常激动,主动跑到矿区去,说我要嫁给矿工。领导当然很高兴,这是可以大做宣传的,中学毕业生都愿意嫁给我们矿工,可以证明矿工的价值。领导给女学生推荐了两个人选,都是先进工作者。第一个人选,是一个沉默的人,就是那种批判现实主义者,能洞察生活的真相。所以他不愿意娶女学生做老婆;第二个则欣然接受。然后矿里面给他们举办了隆重的婚礼,非常高兴!喜气洋洋。可是时间一长,这个女孩子就不高兴了,矿上允诺给她找工作一拖再拖,因为矿里没有多少女工做的工作;她还发现矿工真是没有什么前途的人,生活相当艰苦;这一个男人呢,又很窝囊。矿区的生活,平淡又无聊,慢慢的她就和镇上一个卖狗肉的人相好了,从此就对她丈夫很不客气,不让他碰她,绝对不让碰。于是在他们井下,就生出这样一种消遣,就是问这个丈夫,昨天晚上成了么,他呢,总是表现得很英雄,好累呀,折腾了一夜,然后大家再把他揭穿了。在取笑他的时候,矿工们也在发泄对他的不满,那么差劲,那么窝囊,这样的一个老婆还不揍她。他们说你不是丢你自己的脸,而是丢我们全体兄弟的脸,我们的脸都让你丢尽了。这个可怜的丈夫就说,你们等着吧,我一定要杀了他们。矿工们就激他,你杀呀。他说我刀都磨好了。可是他当然下不了手,他不是那种有狠劲的人。他的媳妇越来越放肆,公然地走进卖狗肉的铺子里去看她的相好。这时候当年那第一个挑选给女学生的沉默的矿工,他跑到狗肉摊子里去,对这一对狗男女说,你们收敛一点。向他们发出警告,他们不理会,依然我行我素。之后不久便发生了血案,这对男女被人捅死在床上。案情是很清楚的,因为现场留下了很多线索,很快就排查出结果了。于是公安局来抓人了,警察走在矿井下的巷道,那个丈夫忽然跳了出来,大喊大叫道,人是我杀的,你们来抓我。这时候矿工们一下子把矿灯都打亮了,照着他,他就在矿灯的光区里又蹦又跳,叫喊着人就是我杀的。这一个场面相当震撼,我觉得这就是英雄的变相。他自己下不了手,他怕血,他不能杀人,可他终于翻身了!我的意思是说,在这里,小说至少是稍微地背叛一些生活的一般的合理性,普遍的合理性。我希望能稍微的背叛一点点,不要太不背叛了。
叶乔,复旦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编校:晓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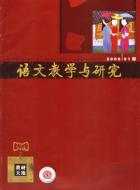
- 读老屋 / 郝永茂
- 爱上长乐的未央 / 孔星华
- 读北岛诗二首 / 陈仲义
- 浅析古典诗词中的声音意象 / 曹德宏 徐建华
- 一种新的语文教学法 / 陈海亮 陈旦阳
- 传统文化应植根于语文教学中 / 刘 玲
- 对联在语文教学中的意义 / 孙 宁
- 非智力因素对语文学习的影响 / 韦柳年
- 文学作品中的距离之美 / 周 华
- 让学生从独立思维中走进新课程 / 张 梦
- 语文课要让学生怦怦心动 / 狄奇静
- 语文教学的设问艺术 / 王玉强
- 农村学校语文学习的怪现象 / 李建芳
- 多媒体在语文教学中的负作用 / 徐 刚
- 试论语文教育现代化的流弊 / 杨道麟
- 对话式教学中教师的有效行为策略 / 尤焕婷
- 成语与名人 / 黄海宾 胡国平
- 巧记文言释义的新方法 / 徐晓玲
- 消极修辞教学问题刍议 / 廖玉萍
- 高考议论文写作怎样快速开头 / 王尔军
- 由高考满分作文标题看作文拟题技巧 / 郝涌平
- 高考诗歌鉴赏中问与答模式探究 / 杜传家
- 走出辨析并修改病句的复习理念误区 / 万仲永
- 新课程背景下的语文考试命题 / 王绍平
- 《木兰诗》的个性化阅读教学 / 徐向莉
- 《卫风·氓》的抒情线索 / 雷光辉
- 《琵琶行》中的臣妾心理分析 / 杨长荣
- 《故乡》中的两个循环节 / 陆建良
- 一堂复习公开课的教学实录 / 成旭梅
- 《珍珠鸟》课堂教学方案 / 王桂芝
- 抓住细节鉴赏小说 / 韩永梅
- 诵读或有声的读后感 / 罗 曼
- 寓言对话式阅读的意义和策略 / 沈中尧
- 农村中学作文教学路在何方 / 邵长新
- 体验式作文的类型与途径 / 陈吉良
- 开放性作文的探索与实践 / 杨会清
- 试论作文教学三感 / 蒋兴娟
-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与诗歌教学有效性初探 / 朱 琳
- 小日记和大作文 / 郑 毅
- 语文教学的趣度与深度 / 周章轼
- 语文教育中可以有点儿野性味 / 李洪义
- 语文课堂小结要凸显精神力量 / 曹 陵
- 整合是语文教学创新的炼金术 / 胡云信
- 文学写作与艺术虚构 / 叶 乔
- 析薪贵在破 / 陶有刚
- 鲁迅精神对语文新课程的滋养 / 毕于阳
- 论语文课堂的文化向度 / 毛承延
